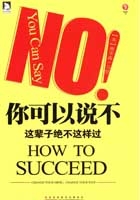傍晚时分,府里进进出出的人多了起来,定是年遐龄父子到访。
我悄悄溜至前厅,躲在屏风后面,偷偷从缝隙里张望,对年秋月充满了好奇,不知道四阿哥和她的初次见面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只见厅里坐了六个人,四阿哥和那拉氏坐了首席,然后依顺序应该是年遐龄,年希尧,年羹尧和年秋月。年羹尧此时看起来不过三十岁年纪,五官清秀,面容白皙,举手投足居然一股文人雅士之风,无法将他与杀人不眨眼的枭雄将领联系在一起;而年秋月则始终低垂眼眉,容貌看得不甚仔细,但体态婀娜,肤凝如脂,应不失为一绝代佳人。
几位寒暄数句,年遐龄忽道:“听闻四爷最近在打听名犬之事,下官偶得一京哈,不知可中四爷的意?”
说着从人抱了一只小京哈进来,一身雪白的毛,居然像极了小落。我欣喜异常,忘形地跳起来,只听身后“当啷啷”数响,我撞翻了丫鬟红绣端上来的茶杯,“什么事?”四阿哥严厉的呵斥吓得红绣簌簌发抖,脸蛋涨得绯红。四阿哥和那拉氏治家一向严厉,在客人面前出了这样的篓子,红绣事后自然没好果子吃,看来只有我挺身而出了。
我拍拍红绣的肩膀以示安慰,定定神从屏风后迈出:“爷,是奴婢不小心打碎了杯子,请爷和福晋恕罪。”
四阿哥见是我,怒气顿消,吩咐红绣重又上茶,便笑着指着那只小京哈问我:“这只狗怎么样?”
我喜上眉梢,使劲点着头,四阿哥见我高兴亦露出满意的笑容,传了绿儿来,让把狗抱进去,我欢天喜地也跟着往里走,却听四阿哥道:“你别走,就待在这里。”我只好站在他身后随侍。不过却可以仔细端详年秋月了,她不是那种让人惊艳的女子,可眉目如画,面若桃花,偶一抬头,眉宇间流动的风情煞是撩人,只是这貌似不经意的秋波所指方向全然冲着一人——我的四爷。
我知道自己脸上此时必是乌云密布,虽然心里十分清楚历史不可改变,但要我亲眼目睹自己所爱之人另娶他人,却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四阿哥谈笑间总不忘回头看看我,却猛然发现我面露不悦,他莫名其妙之余不知所措,年家四人见他神色有异,也不知何故,不敢再言语,场面一度冷下来。那拉氏不愧大家风范,见势不对,马上救场,“听闻秋月妹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年大人真是教导有方啊!不知可否请妹妹献艺一曲,也让我这不争气的姐姐雅一回?”
四阿哥这才恢复神色,面色自若起来,其他人也舒心一笑,气氛重又活跃。年秋月弹奏了一曲琵琶,曲调活泼雅致,颇有小家碧玉之风,赢得在场一片掌声。年秋月起身莺莺谦虚数句,可脸上的得意神色却跟语言毫不相配,眼角的余光还不时饱含羞怯仿佛不经意般扫过四阿哥英俊的脸。我不由轻轻冷哼一声。四阿哥敏感地嗅到空气里异样的气息,回头一笑,有意逗我:“怎么样?把你比下去了吧?”我撅嘴不乐意搭理。
年秋月见状忽道:“原来姐姐也善音律,不知可否请姐姐赐教一曲,让秋月开开眼界。”
我神态淡然道:“奴婢不过是一小丫鬟,哪里懂什么音律?怎敢跟豪门千金相提并论。”
年府四人还真将我当成了丫鬟,只听年遐龄道:“四爷府中果然藏龙卧虎,一小小丫鬟竟也是风雅之人啊!”
四阿哥却沿袭了数千年封建文化的传统,将谦虚这一美德推崇备至,听他的语气就让我气不打一处来,“她哪里懂什么音律啊?不过是自己瞎玩玩。丫头,既让你弹就弹首,别在年大人面前丢丑了。”
怎么说我的古筝在现代也是通过专业过级考核的,就将我贬得一无是处?我压抑心中的愤懑,凝眉飞指,《十面埋伏》的铿锵之音便从我指尖喷薄而发,不知是否怒火中烧的缘故,我将它演绎出前所未有的气势磅礴,自己都被琴音中充斥的杀气腾腾之势所震惊。弦凝指停处,金戈铁马之音绕梁未尽,众人惊讶赞叹之神色显露无遗,竟然皆忘了喝彩。直至我退回四阿哥身后,年羹尧才意犹未尽叹道:“如此气势恢宏之曲居然出自一小女子之手,真让人难以置信啊!”
四阿哥脸上的怡然自得总算让我找到一丝安慰,我可又给他长脸了,只是这个虚伪的家伙仍一味谦虚,“哪里哪里,耍玩之艺,不值一提。”
哼,如果我今天的发挥还不值一提,那么年秋月你侬我侬的庸俗小调简直就是不入流!年秋月的脸此刻像熟透的柿子,既无趣又难堪,看我的眼神也多了些内容,似乎我又给自己竖了一个敌人。
晚膳过后,年秋月便留在了贝勒府为仆,四阿哥将其安排在那拉氏身边,年府四人均流露出失望的眼神,尤其年秋月,隐隐闪过一点泪光,原来他们都以为四阿哥会让她随侍自己,可惜妾有意郎无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