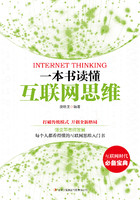菜辛在他的美学名著《拉奥孔》中,论述了画与诗在表现对象上的差别。他说:物体(同时并列)及其感性特征是绘画所特有的对象;动作(先后承续)是诗所特有的对象。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不论是诗还是画,不论是写动态的动作,还是画静态的物体,它们都必须表现人的生活,人的思想感情。离开了这一点,那所谓“动作”、“物体”,都毫无意义,都不是艺术的对象。我国古代的美学家也十分重视这一点,他们在讲到艺术中的情与景的关系时,总是强调以情为主,认为艺术根本是在于表现人的情志。例如,清初的李渔说:情景“二字亦分主客,情为主,景是客,说景即是说情。非借物遣怀,即将人喻物,有全篇不露秋毫情意,而实句句是情,字字关情者”。我国古代美学家还常常讲,在艺术中,往往意不在言中,言在此而意在彼,意在言外,意在画外,等等。这些话的确道出了艺术的重要特点,含意很深。其中一个意思,可以用来说明那些描写自然事物的艺术品,如山水诗、花鸟画等,即:表面上看,作者所写的所画的是山,是水,是花,是鸟,但表现的都不是山水花鸟本身,而是人的生活,人的思想感情,即意在山水花鸟之外,言在此而意在彼。
就艺术把自己的对象界定在人类社会生活以及和人类社会生活有关的事物的范围之内这一点而言,说文学是人学,说艺术的对象是人,是很有道理的。艺术家切不可见物不见人,忘记了艺术对象的这个特点,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写那些见物不见人的作品。
艺术对象是本质规律的生活现象
哲学既然是把世界的总体、总和作为自己的对象,当然在哲学对象之中也包含着人类社会生活。那么,当哲学把自己的视线专门集中于人类社会生活时,是否这时的哲学对象与艺术对象完全一样呢?
可以明确地讲:作为哲学对象的人类社会生活,与作为艺术对象的人类社会生活,不一样。区别在哪里呢?简单地说,哲学对象是生活现象的本质规律,而艺术对象则是本质规律的生活现象。
纷纭复杂的人类社会生活,不管怎样的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实际上都包括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形态,一方面是它的一般的必然的本质规律。前者的特点是具体可感、丰富多变、不稳定性,后者的特点是抽象(看不见也摸不着)、相对单一性和稳固性。前者总是表现为特殊性、个性,后者却是普遍性、共性。二者处于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之中,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双方互为对方的存在条件。但是二者并非没有区别,个性并不等于共性,个别不等于一般,现象不等于本质,偶然不等于必然。当哲学面对着人类社会生活时,它的着眼点不是个性,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形态,而是个性之中的共性,是包含在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形态之中的一般的必然的本质规律——这正是哲学的对象;而当艺术面对人类社会生活时,它的着眼点不是共性,不是一般的必然的本质规律,而是包含着、体现着共性的个性,是包含着、体现着一般必然本质规律的个别偶然现象形态——这正是艺术的对象。让我们举例加以说明。当哲学家和艺术家都面对着生活中的地主这样的人物时,作为哲学家,他所感兴趣的不是每一个地主的个性特点,而是表现在这些不同的地主身上的共同的普遍性的东西,即一切地主之作为地主的压迫农民、剥削农民的必然本质。艺术家则不同,他所最感兴趣的是那一般必然本质规律在每一个具体的地主身上有怎样特殊的表现,是这个地主与那个地主各自不同的个性,各自不同的个别偶然的现象形态。作为艺术对象的地主,必须是这个地主或那个地主,而决不能是一般的地主。艺术家只能写带有自己个性特点的、带有自己特殊的甚至是偶然性的生活经历的、因而以自己特殊的现象形态出现的地主,譬如,或者是现实生活中的南霸天,或者是现实生活中的黄世仁、庄阎王……个别性、偶然性、特殊性,是艺术对象的显著特点。经过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当由艺术对象转化成为艺术形象时,只要是成功的,也都必须保持着个别性、偶然性、特殊性。例如,电影《叶塞尼亚》的人物和故事具有个别性、偶然性、特殊性,电影《绝唱》的人物和故事具有个别性、偶然性、特殊性,话剧《雷雨》的人物和故事同样具有个别性、偶然性、特殊性。取消了个别性、偶然性、特殊性,就取消了现实中的艺术对象,取消了艺术中的艺术形象,也就取消了艺术本身。
在艺术家的工作中,当然决不排斥一般、必然、本质。但是,艺术家注意的绝非用概念表述的一般、必然、本质,而是一般、必然、本质会有怎样的个别、偶然、现象的各种特殊形态的表现,从而,如恩格斯所说,作出“鲜明的个性描写”,使他所写的人物,“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顺便说一句,因为艺术家并不排斥一般、必然、本质,不排斥共性,而是着重表现那一般、必然、本质在不同人物和事物身上的各种特殊的个别、偶然、现象的具体形态,着重表现那共性的各种特殊的甚至奇异的个性形态,于是从艺术家所写的各种艺术形象身上,可以认识到包含在其中的一般、必然、本质,认识到其中的共性、普遍性,这就是艺术的认识作用。但是,艺术形象的个别性、偶然性、特殊性,如生活现象本身那样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使艺术与哲学不同,不仅具有认识作用,同时还具有美感教育作用。这后一种作用,更是艺术的特性的表现,艺术正是以它具体可感、生动鲜明的美的形象,“感人”、“化人”、“移人”,陶冶人的情性,改造人的灵魂,激发人的意志,给人以美的享受,以精神愉悦。如果失去了这些,也就丧失了艺术之为艺术的性质。而艺术的上述特点,也正是与艺术对象的特点密切相关的。
对于艺术对象与哲学对象的这个区别,对于它们各自的特点,许多哲学家、美学家。艺术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曾经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论述,只是这些论述很少为人们特别注意罢了。
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以十分赞同的口气摘引了一大段《欧洲通报》上一篇评论《资本论》的文章中的话,其中正好说明了哲学对象的特点:“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马克思在摘引了这段话之后称赞说:“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上述这段话,既谈了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同时也说明了作为哲学家马克思是把一定社会现象的必然、本质、规律,作为自己探索、研究和把握的目标,也即作为哲学的对象。
更清楚地说明哲学对象与艺术对象的不同特点的,是列宁在给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中的一段话。我们不妨把列宁这段完整的话引在下边,虽然长些,但更便于说清问题:
“对一本通俗的小册子来说,把小市民——知识分子——农民(似乎是我信里的第6点或第5点)的没有爱情的、卑俗的婚姻同无产阶级的有爱情的、公证的婚姻(如果您一定要加的话,还可加上一句:甚至片刻的情欲和暧昧关系,可能是低级的,也可能是高尚的)加以对比;岂不是更好吗?而您所谈到的并不是阶级典型的对比,而是某种当然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但是问题难道在于偶然事件吗?如果您要把婚姻中的低级的接吻和片刻的暧昧关系中的纯洁的接吻这种偶然事件、个别情况作为您的主题,那末这个主题应当放在小说里去发挥(因为在小说里全部的关键在于个别的环节,在于分析这些典型的性格和心理)。难道在小册子里可以这样做吗?”
很显然,作为理论性的小册子(从哲学的理论的角度),列宁要求阿尔曼德面对的是现象的本质,即“阶级典型的对比”(这里的“典型”一词,是指阶级的普遍性、必然性、本质规律性的意思),而不是“某种当然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列宁认为,个别偶然现象虽不是哲学的对象,却理所当然地、名正言顺地应该是艺术的对象。他指出,那种“偶然事件、个别情况”“应当放在小说里去发挥”。列宁在这里强调:“在小说里(在一切艺术中都如此)全部的关键在于个别的环节,在于分析这些典型的性格和心理”。他在“个别的”和“性格”下边特别加了重点号。这就表明列宁特别强调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形态是艺术的对象。
下边我们再看看艺术家们在谈到有关艺术的对象问题时,是怎么说的。
被恩格斯称为文艺宙斯的歌德认为:“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歌德又说:“诗人应该抓住特殊,如果其中有些健康的因素,他就会从这特殊中表现出一般”。歌德谈的都是艺术对象的特点,强调艺术的对象是体现着一般的特殊事物,也就是我们上边所说艺术对象是现实生活的个别偶然的现象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给予高度评价的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前言》中曾经这样说:“偶然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这话的意思,也包含着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体现着必然本质的偶然现象是小说(艺术)的对象。
我国现代著名的导演艺术家焦菊隐,把上述巴尔扎克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他认为:寻找偶然来表现必然,这就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艺术就应该去寻找那表现必然的偶然,以它为对象。
说艺术对象是本质规律的生活现象,一方面是说,艺术虽然绝不能直接地干巴巴地赤裸裸地写必然本质,而是写偶然现象;但它所写的偶然现象中,却应该包含着必然本质,即:本质的现象,必然的偶然。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艺术典型。一般地说,艺术不能把那些“纯粹”偶然的东西,“纯粹”现象的东西(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作为自己的对象,或者说,至少不是主要对象。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个别、偶然、现象是无限生动、丰富、多样的,至少它们比一般、必然、本质要生动、丰富、多样得多。所以,任何本质绝不能全部包括着现象,任何必然绝不能全部包含着偶然,任何一般也不能穷尽个别。当艺术描写现实生活的个别、偶然、现象时,也就把比一般、必然、本质更生动、更丰富、更多样的东西写出来了,而这其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某些非本质的现象,非必然的偶然,这应该是被允许的。当然这不是艺术中的主要部分。如果要求艺术中的一切都是“本质、必然”,那就会使艺术形象变得象“本质、必然”本身那样干巴、抽象,失去生命的血色,失去了它应有的生动性、丰富性、多样性。
艺术对象的重点是精神生活现象
包罗万象的人类生活现象,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生活现象,一种是精神生活现象。前者包括人类的一切物质感性实践活动,例如,我们常常说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三大实践活动,也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等一切物质生活。后者则包括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例如人们的认识活动,人们的感情活动,人们的意志活动,以及人们的希望、愿望、理想,人们的审美活动,人们的道德行为等等。人们的物质生活现象与精神生活现象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二者又是有区别的。总的说,物质生活现象是精神生活现象的基础,精神生活现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物质生活现象的派生物,是它的反映。然而,若将精神生活现象看成是第二等的、无足轻重的,却是完全错误的。精神生活现象有极其活跃的能动性,对物质生活现象起巨大的反作用;而且,精神活动、意识活动,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是他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人的精神活动、意识活动、心理活动的总的特征,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性格”。艺术,虽不把人们的物质生活现象排斥在自己的对象范围之外,但却是以人们的精神生活现象作为重点对象。一句话,艺术最主要的就是要表现人们的精神生活现象,就是要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而刻画性格,则成为绝大多数艺术种类的最基本的工作。
我们说艺术的对象主要是人们的精神生活现象,艺术最主要的是展示人的精神世界——艺术对象这一特点的确定,是以艺术史上的无数事实作为根据的。那些重表现的艺术种类(例如音乐、舞蹈、抒情诗以及其他抒情性艺术等等)显然主要是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音乐的表现对象主要就是一定时代一定阶级一定民族的人们特定的情绪、情感、思想……他们的精神生活、内心世界。贝多芬的交响乐、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我国著名的广东音乐、“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等等,一切成功的音乐作品,都是通过声音,表现人们一定的情绪、情感、思想、理想、愿望,并且又直接诉诸听众的情绪、情感、思想、愿望,诉诸听众的内心世界。我国古典美学,早就指出了音乐的这一特点。《荀子·乐论》中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乐记》中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舞蹈,它也是一种抒情的艺术,它是人们的一定精神生活的表现。当人们感情激动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蹈动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的自然表情动作的放大。总之,舞蹈,主要是以它特定的审美动作来表现人们的某种生活理想、思想和感情。至于抒情诗的直抒胸臆的特点,更为大家所熟知,不必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