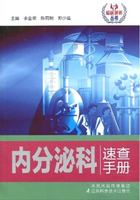在艺术创作中,如果仅仅具备艺术家的主观因素——创作主体的各种条件和资质,即使是非常优秀的条件和资质,那是任凭什么艺术品都产生不了的。虽然美学史上曾经有许多人鼓吹艺术完全是艺术家主观心灵的创造,与客观世界无涉;然而正像人不吃饭会饿死一样,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客观现实作为食粮,同样不能维持其生命。日本的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一书中说:“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他认为文艺的根源是作家的无意识心理,而创作的过程不过是由作家的无意识心理→心象→理知感觉→作品(被象征化的表现)。另一个日本作家、属于白桦派的有岛武郎认为艺术根源于爱,他说:“生艺术的胎是爱。除此以外,再没有生艺术的胎了。有人以为‘真’生艺术。然而真所生的是真理。说真理即是艺术,是不行的。真得了生命而动的时候,真即变而成爱。这爱之所生的,乃是艺术。”厨川白村和有岛武郎都认为艺术根源于主观。但是,不管是厨川的所谓“绝对自由的心境”,还是有岛的“爱”,如果离开了现实生活的大地,是一刻也不能存在的。最起码,人只有活着才能具有某种“心境”,才能“爱”;然而要活着就得吃饭,就得过一定的物质生活,就得与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总之,离不开客观的社会现实。这样,人的主观“心境”和“爱”就另外还有根源,这就是现实。而艺术,其最终根源就不能是艺术家的“无意识心理”或“爱”,而是现实。现在,我们就从艺术创作的客观方面——即艺术的对象来考察艺术的特性。
艺术有自己独立的特殊对象
有些学者对于艺术是否有自己特殊的对象,还持怀疑态度。艺术对象问题确实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个问题,以往的美学权威们论述得最少,从他们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的。譬如,马克思对于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不同方式,谈得很明确;但是却似乎没有直接的明确的谈到过艺术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对象。别林斯基更是干脆否认艺术有自己的对象,他说:“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就是说,哲学和艺术,对象完全相同,只是再现对象的方式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但是,经典作家没有谈的,并非后辈晚生不能进行探讨;而美学权威的话,也并不一定就是真理。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苏联就有人对别林斯基的上述论点提出疑义,明确提出艺术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对象。不久,我国也有人响应,强调“文学是人学”,但是,这种论点几乎是立即被扣上“修正主义”、“人性论”的帽子,遭到大规模地无情批判。今天看来,他们的论点虽然仍有许多可以商榷之处,有的或者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加以补充、修改,使之完善;但总的说,他们关于艺术对象的意见,有很多积极因素,很有启发意义。目前我所看到的数量不多的探讨艺术对象问题的文章,基本上是沿着他们的那条路子走下来的。
现在,是到了深入探讨艺术对象问题的时候了!
在我们上边所引述的别林斯基那段话的前面和后面,他还说过这样的话:“人们看到,艺术和科学不是同一件东西,却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特定内容时所用的方法。”“政治经济学家被统计材料武装着,诉诸读者或听众底理智,证明社会中某一阶级底状况,由于某一种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诗人被生动而鲜明的现实描绘武装着,诉诸读者的想象,在真实的图画里显示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由于某一种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可是他们都是说服,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结论,另一个用图画而已。”别林斯基的这些话曾经在许多文章和教科书中被广泛地引用,是人们很熟悉的。但是,我们听到的大都是人们对这些话的肯定和赞扬,却很少听到有人指出这些话的片面性,特别是很少有人详细说明这些话之所以带有片面性的理由。
上述别林斯基那些话,说艺术和科学的对象“都是同一件事”,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其理由,我们可以从逻辑的和历史的两个方面,分别加以说明。
从逻辑方面说,我们首先可以对别林斯基上述的话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既然承认艺术和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在“处理”现实内容时所采取的形式、所用的方法不同,那么,这不同的形式之中所表现的内容难道会没有差别吗?这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思维方式所面对着的对象难道会完全一样,“都是同一件事”吗?关于事物的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别林斯基曾经说过一段十分精采的话:“如果形式是内容的表现,它必和内容紧密地联系着,你要想把它从内容分出来,那就意味消灭了内容;反过来也一样:你要想把内容从形式分出来,那就等于消灭了形式。”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事物的内容应该有与自己相适应的特定的形式,事物的形式也应该有与自己相适应的特定的内容。内容不同,作为它们的反映的各自的形式,也必不相同。艺术和哲学这两种社会意识形式的不同,正是反映着它们各自所表现的现实内容不同。不同的形式是由不同的内容所决定的。别林斯基说“它们(艺术和哲学)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是与他自己的那段关于内容与形式密切联系着的话,自相矛盾的,是不正确的。决定艺术这种特定意识形式的“现实”与决定哲学这种特定意识形式的“现实”,似乎可以笼统地都被称为“现实”,然而,细细分析起来,其实很不一样,至少可以说它们分别是那总的现实的不同侧面、不同范围、不同属性。这不同侧面、不同范围、不同属性,也就是艺术和哲学各自不同的对象。
别林斯基还说:哲学是用“逻辑结论”“诉诸读者或听众的理智”;而艺术则是用“真实的图画”“诉诸读者的想象”。同时,他认为:诉诸“理智”和诉诸“想象”的是完全相同的同一个对象。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因为,客观对象的特点与人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方法和方式按常理说是相适应的。一个对象主要作用于人的想象,另一个对象则主要作用于人的理智,其所以如此,正是说明这两个对象各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譬如说,作用于人的想象的那个对象,其感性的形象性的特点更为突出,而作用于人的理智的那个对象,其理性的抽象性的特点更为突出。同理,客观现实中那些理性的抽象性的特点,更为哲学家所注意;而客观现实中那些感性的形象性特点,则更为艺术家所注意。前者常常作为哲学的对象(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哲学对象的一种性质),后者常常作为艺术的对象(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艺术对象的一种性质)。
但是,能够最有力地证明艺术对象与哲学对象二者不同,证明别林斯基上述思想的片面性的,不是逻辑,而是历史,即客观事实和实践。
从历史方面说,艺术对象之不同于哲学对象及其他科学的对象,乃是客观存在着的历史事实。在人类漫长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人的意识也不断发展着,人的主观认识能力——他的感受力和思维力、他的掌握世界的能力、方式和方法(这些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也不断地丰富着发展着。与此同时,客观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意识的对象也不断发展着丰富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受与耳朵不同,而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马克思的这些话,强调了存在着与人的各种不同的本质力量相对应、相适应的不同的对象。主体的丰富和发展是与对象的丰富和发展在客观实践中同时进行、同时获得的。马克思在这里说明不同的主观能力存在不同的对象时,主要举了不同的感觉能力的例子,如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但马克思的话是有普遍意义的。不仅不同的感觉能力(如人的视觉和听觉)各有不同的对象,而且不同的思维能力(如理论思维和艺术思维)同样各有不同的对象。总之,人的每一种掌握世界的独特的方式,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独特的对象。如果说在原始时代,由于人的主观能力不发达、“人的本质力量”的贫弱,其艺术的掌握世界的能力与理论的掌握世界的能力等还是混沌一体的,因而相应的在外在世界中艺术对象和科学对象(哲学对象)也是分不清的;那么,随着客观实践的不断发展,人的主观能力大大丰富了,人的本质力量大大发展了,人的艺术的掌握世界的能力和理论的掌握世界的能力以及其它种类的掌握世界的能力,被逐渐区别开来、独立出来了,因此,相应的,外在世界的不同侧面、不同属性、不同范围被开发、被认识、被掌握,也就自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对象,如艺术对象,哲学对象,以及其他许多具体科学的对象。
那么,艺术对象与其他对象(如哲学对象)相比,具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艺术对象的范围应该如何界定呢?
艺术对象的范围
有一种观点,认为艺术是把现实的统一整体作为自己的对象,而“科学家恰恰相反,他却在分析现象,可以说是‘解剖’现象,按照各个部分来研究”。这种说法只是具有部分道理,严格讲并不科学。因为,其一,虽然艺术与伦理学、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具体科学相比较,它的对象显出一定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但是,这种综合性和整体性只是相对而言。其实,任何艺术都不可能全部把现实的统一整体综合地反映出来,而只是反映其一部分、某些侧面、某些属性。其二,与哲学相比,与其说艺术对象是现实的综合整体,不如说哲学对象更是现实的综合整体。哲学总是企图把整体世界在自己的思维中复制出来,它要高高地站在这个世界之上,鸟瞰这个世界的全貌,然后就这个世界的最根本的问题,向人们作出回答,因而,它的对象范围比艺术大得多。
现实世界是无限广阔、无限丰富的,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始无终,而哲学所面对着的,就是这整个现实世界的总体、总和——宇宙间凡是与人相关的一切都在哲学的视野之内,即这个世界的与人相关的一切事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事物的一切方面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都在哲学的视野之内,哲学就是以这包罗万象的综合的整体世界为自己的对象。
与哲学对象比较,艺术对象是狭窄得多了。艺术所面对的不是整体的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属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那一部分,包括那些虽不直接就是人类社会生活、但和人类社会生活有关的现象。大部分艺术作品,是直接描写人类社会生活的;有的艺术作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直接以人类生活为描写对象,但实际上却仍然是表现人类社会生活的,表现人的生活情趣、思想感情、理想和幻想、兴趣和爱好。除了人类社会生活以及与人类社会生活直接有关的现象之外,艺术从不奢望现实世界中的其他东西。不错,艺本也常常描写自然界。但是,艺术却绝非廉价地、无缘无故地把自然界作为自己的对象。只有如马克思所说“自然是人的身体”、自然界的事物与人类生活有着密切的本质联系时,艺术才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它。譬如,艺术中常常写太阳、月亮、星星,常常写山脉、河流、风雨、雷电,常常写动物、植物,会说话的鸟,有感情的花,但是这一切作为艺术的对象,或是以物喻人,或是借物抒情,或是托物起兴,总之,只是为了表现人类生活;不然,它们在艺术中便没有任何价值、任何意义。就连那些所谓“纯粹”的山水诗、风景画、花鸟画,所写所画也绝非纯粹的自然物,而是寄托着、渗透着人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审美感受、理想、愿望,而且也只有这样,那些自然物才能成为艺术的对象。如八大山人的鹰、郑板桥的竹、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很明显地都是寄托着人的思想情趣。早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一首《画竹歌》中,就明确地指出绘画的这个特点。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画家肖蜕赠给白居易一幅墨竹画,诗人作《画竹歌》答之。诗中指出:画的是竹,而表现的却是人的思想感情。诗曰;“人画竹身肥臃肿,肖画茎瘦节节竦;人画竹梢死羸垂,肖画枝活叶叶动。不根而生从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野塘水边碕岸侧,森森两丛十五茎。婵娟不失筠粉态,肖飒尽得风烟情。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请看,这画中不是处处渗透着人的思想感情吗?重写意、重表现的中国山水画、花鸟画是如此,即使重写实、重再现的西洋风景画也是如此。例如列维坦的风景画,那森林,那河流,难道不是明显地表现着画家的某种审美趣味、某种思想感情吗?
即使同一个自然物,在哲学家眼里(即作为哲学对象)与在艺术家眼里(即作为艺术对象),也是很不一样的。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天上的星星在诗人海涅眼里和在哲学家黑格尔眼里具有多么不同的意义。海涅回忆说:“一个星光灿烂的良夜,我们两个并肩站在窗前,我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人……心醉神迷地谈到星星,把它们称为圣者的居处。老师(指黑格尔)喃喃自语道:‘星星,唔!哼!星星不过是天上一个发亮的疮疤’,我叫喊起来;‘看在上帝面上,天上就没有任何福地,可以在死后报答德行吗?’但是,他瞪大无神的眼睛盯着我,尖刻地说道:‘那么,您还想为了照料过生病的母亲,没有毒死自己的兄弟,希望得到一笔赏金罗?’”在海涅那里,星星是圣者的居处,是福地,是人死后可以报答德行的地方,总之星星与人类生活密切联系者,因而是艺术(诗)的对象;而星星在黑格尔眼里,却不过是天上一个发亮的疮疤——即以它作为自然物的本来性质呈现着,因而只是哲学和科学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