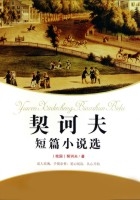前几年,许谋清以他带有浓厚恋乡感情的乡土小说引起文学界和读者的关注。有关这些作品的研究、论文也有过一些。这些作品是许谋清小说创作的开始,也是他走向成功的开始。说来也怪,许谋清没有使自已陷入常人的习惯,顺着业已显出成功的趋势,在原有的轨道上再做新的努力,却把目光和力量转移开来,在一片新的土地上进行开掘。当然,许谋清的乡土小说并非浅尝辄止,但要说他这些小说就已写尽了自己的恋乡情结,已构成了特异突出的文学现象,似乎还不能使人气壮语畅。故此,对许谋清小说创作中出现的这次转移,现今还不必给予结论性的判断。我现在要讨论的是他小说创作中的另一种形态。
放下乡土小说的写作之后,许谋清自1988年10月在《北京文学》上拉开了“海土”小说系列创作的序幕。迄今,我已阅读过这个系列中的11篇作品。“海土”的题记中说古传:女娲氏用泥土造人。《海土》系列里的人物,是用闽南赤红的泥土,和了海水捏成的。大海在喧闹,他们被海水浸湿的心,首先躁动不安了……”这题记使我们便于了解作家的创作构想,也为我们走进“海土”系列小说打开了便捷的途径。与此前的那些乡土小说比较起来,许谋清的笔还未离开闽南这块赤土。但是,由于视角的变化与兴趣的转移,“海土”小说已不再是把浓浓的恋乡情怀化入到对乡俗世态的描绘之中唤起人的某些惆怅温热心情的样子了;“海土”着眼的是现今的故乡,是今天被大海的喧闹搅动起来的生活和人的行为与心态。在这个系列小说作品中,许谋清着重的不仅仅是描绘、对异地风情的发现与品味,同时还更自觉地把某种观察、辨识的目光投放到写作过程中。因之,这些小说不仅描写着动中的闽南生活现实,也同时把对这种生活的思考化入作品提示给读者。“海土”隐蔽了许谋清对故土的凝重感情,却以在故乡的感受与观察为基土,把故乡动中的困惑和希望内含其中,使之感情更见真挚、深沉,也更富于现实性的价值。
“海土”系列小说的共同母题是喧闹的海潮在现实人生中掀起的躁动行为和心态,以及因这种躁动的出现而生出的欣喜与痛苦、死亡和新生。许谋清在一个极大的背景和重大主题上构筑自己的小说,可他落笔却常常在看似细小轻微的事件人物上面。他的小说没有那种平稳周全的架构和情节,但却总能使人在看似无意识的、乃至是细琐的叙说中感受到时代的大背景,透彻到生活人物的肌里深处。当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而来的时候,闽南这块沿海赤土地在闭锁了多年之后重新与这种大潮呼吸相应了,接通了这里多年前曾有过的那种潮汐带来的变动。多年侨居在外的人们归来故里,省亲投资。故里的人显示给他们的除去真挚的亲情之外还有突出的贫穷。生活地域不同、生活状况相异然而却是同一根系的子孙们如今走到一起,彼此的感受极为强烈。海外吹来的劲风扇起了生活在本土上的人们的欲望。结果,人们的生活行为就像脱离了常轨的车子急剧地动荡和行驶着。金钱刺激了人们的热情,“越没文化,胆子越大”,胆子越大,发得越大越迅速。在开放的旗号下,人们都在为自己、为自己的村庄乡镇县区能迅速地发起来奔忙着。像《醉官》里的那位畏酒又不能不去连续陪归侨喝酒以取得资金的县长,《圆》里那位叫黑狗的乡长把本乡的发展寄予番(外国)客对于修厕所的投资上所做的努力情形以及有了钱修厕所后又生出许多争执是非的情形,真令人对这里的现实有别样的感触。源于这种急剧的动荡和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的道德水准,人们的行为规范,人们的心态,人们的喜悲情绪等等,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与变化。“海土”以其细腻深入的笔触写活了这种冲突变化的现实和各样的现实人生,也透彻地描绘着其中的困惑与期冀。
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巨大社会生活变化,使人们以往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不能适应。在这里,一种新样式的衣服刚上身几天,却已过时;这家刚刚花费几万元建起的新屋,不久就又被他人用十几万、几十万元筑起的更漂亮的新屋所排挤;连盗贼也不再死守陈规,迅速地跟随着不断变化的环境对象改变着自己行窃的手段。面对这纷纭的世界,人们的心态各异,行为各异,从而演化出一幅动荡的闽南现实图景。
《土枪牛虱子吴先生》看似写一个乡间的苦恋故事,可剥开这个苦恋故事的外皮,我们见到的却是比这些人物感情更深层、更凝重、更富有社会性的东西。三个男人早年共同爱上了一个女人,后来因一女只能嫁一男他们离开各奔生活。多年之后,当生活出现了大变化的时候,那个女人却在不应该死的时候死去了。她的死使三个男人又走到一起。他们三人聚在酒桌前,各自追思着对她的深深怀念和痛失之情。他们觉得:“得换一种活法,过去过的,那不是日子!谁都对自己的过去不满起来。”土枪承认自己坏,心黑。可他今天毕竟发起来了。因此,他想我要是跟水在户(那个女人)结婚,完完全全可以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水在户不像他现今的老婆这样粗陋,没有教养。另外,他有本事又有钱,水在户也不至于因几个钱去偏僻的地方,以致误了诊治而死亡。牛风子也对自己的老婆不满意,不仅人长得没个形,“也没一样拿得起来,没一点点主意”。心想,若是自己与水在户成婚,也“不会是这样的人”,整天吃苦受累,还发不起来。过去的恋情虽是多年前的事,可他“瞒着老婆偷偷藏着一张水在户的照片”,如今看着,眼眶全都憋红了。至于吴先生,早先窃喜水在户和自己结了婚,今天却为多年来未能使水在户过上好一点的日子而痛苦;更为自己未有能力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最后让妻子奔到山区来,竟使她亡命于盲肠炎这种自己足可以手到病除的小病上悔恨不已。三个男人对水在户的爱刻骨铭心,着实令人感动。然而,他们并非全都知道,换个活法决非轻而易举。土枪有钱,水在户未必就乐意嫁给他;牛虱子胆小贪心,自然不能取得水在户的喜欢;吴先生最有出息,有文化且吃着公家粮,从人与环境习俗来看,水在户当时选择吴先生不是个错误。可恰恰是,吴先生在解决家人经济生活及水在户工作调动上的无力,决定性地导致了她的死亡。因之,“换一种活法”实在不是因有一个愿望即可实现的。它既取决于生活的大背景、大环境,同时也取决于个人自身的因素。土枪、牛虱子、吴先生,他们既无力躲开生活的大环境而存在,更没有彻底摆脱自身因素的制约。所以,水在户的死看似偶然的事情,实际却是生的某种必然性决定的。三个男人各自都在水在户的死亡面前做着各种各样的假设,以为换一种结合方式,生活和人的命运就会是另一种情形。这种因爱生出的心思自然是美好的,但它却是虚幻的,是一种超脱社会和自身因素的假设。“土枪还是土枪。牛虱子还是牛虱子。吴先生还是吴先生。”他们并未因水在户的死亡而摆脱自己,真正找到一种新的活法。小说正是在这一点上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让人们意识到改变自身内在品性的重要和不易,并意识到人决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地存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