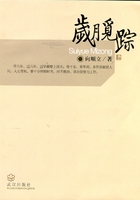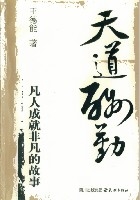裙制之精粗,惟视折纹之多寡。折多则行走自如,无缠身碍足之患,折少则往来局促,有拘挛桎梏之形;折多则湘纹易动,无风亦似飘飖,折少则胶柱难移,有态亦同木强。故衣服之料,他或可省,裙幅必不可省。古云:“裙拖八幅湘江水。”幅既有八,则折纹之不少可知。予谓八幅之裙,宜于家常;人前美观,尚须十幅。盖裙幅之增,所费无几,况增其幅,必减其丝。惟细縠轻绡可以八幅十幅,厚重则为滞物,与幅减而折少者同矣。即使稍增其值,亦与他费不同。妇人之异于男子,全在下体。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其所以为室者,只在几希之间耳。掩藏秘器,爱护家珍,全在罗裙几幅,可不丰其料而美其制,以贻采葑采菲者诮乎?近日吴门所尚“百裥裙”,可谓尽美。予谓此裙宜配盛服,又不宜于家常,惜物力也。较旧制稍增,较新制略减,人前十幅,家居八幅,则得丰俭之宜矣。吴门新式,又有所谓“月华裙”者,一裥之中,五色俱备,犹皎月之现光华也,予独怪而不取。人工物料,十倍常裙,暴殄天物,不待言矣,而又不甚美观。盖下体之服,宜淡不宜浓,宜纯不宜杂。予尝读旧诗,见“飘飏血色裙拖地”、“红裙妒杀石榴花”等句,颇笑前人之笨。若果如是,则亦艳妆村妇而已矣,乌足动雅人韵士之心哉?惟近制“弹墨裙”,颇饶别致,然犹未获我心,嗣当别出新裁,以正同调。思而未制,不敢轻以误人也。
【评】
关于服装美,李渔提出了许多相当精彩的思想,如“贵洁”、“贵雅”、“贵与貌相宜”,而在制作的时候要“相体裁衣”,等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套衣服如果弄得脏兮兮的,再好也不美;如果只是华丽,甚至花里胡哨而不雅致,那也很难说得上美;特别是,如果与他(她)的面色、体态不相称、不相宜,那更谈不上美。为什么一套衣服若让好几个人来穿,有的人穿上好看,而有的人穿上则不好看呢?李渔说,这是因为“面色与衣色有相称不相称之别”。“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各人必须找到自己的“与貌相宜”的衣服。说到这里,我想再顺便提一下,李渔只谈到衣服与面色的关系,而没有具体论及衣服与体型的关系。这是个遗憾。之所以如此,还是前面曾说过的那个原因:中国的民族传统不重视人体美,很少从解剖学的角度研究人体,也很少注意到人体的线条美。只是在后面谈到“鸾绦”即束腰之带时,李渔才提起“妇人之腰,宜细不宜粗,一束以带,则粗者细,而细者倍觉其细矣”,间接地涉及人的体型、线条问题;然而,所谈也不是裁剪和缝制衣服时要考虑形体美和线条美,而只是说用束衣带的方法显出身段的形体美和线条美。
但是,无论如何,李渔的服装理论中还是提出了衣服要“与貌相宜”和“相体裁衣”的观点,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什么叫做“与貌相宜”?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可以有几个方面的意思。
一是与人的面色相宜。不同的人,面色黑白不同,皮肤粗细各异,所以就不能穿同样颜色、同样质料的衣服。这一点李渔有比较自觉的意识。
一是与人的体型相宜。上面说到李渔对此关注不够。今天的服装设计师特别注意人的体型特点,譬如个子的高矮,身材的胖瘦,肩膀的宽窄,脖子的长短,臀部的大小,上身长下身短或是下身长上身短,腰粗或是腰细,胸部是否丰满,等等,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设计、裁剪和缝制合身的衣服。
一是与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素养、内在气质、社会角色等等相宜。李渔对此也有所涉及,他提到衣服与“少长男妇”即性别、年龄的关系,与“智愈贤不肖”即文化素养和内在气质的关系,等等。
一是与一定社会的时代风尚和文化氛围之下人的精神特点相宜。例如魏晋时部分文人蔑视礼法,他们的衣服常常是宽衫大袖、褒衣博带;唐朝社会相对开放,女子的“半臂”袖长齐肘,身长及腰,领口宽大,袒露上胸,表现了对精神羁绊的冲击和对美的大胆追求;宋代建国,控制较严,颁布服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有陵躐”,人们衣着相对严谨;等等。
做到“与貌相宜”的关键在于“相体裁衣”。“相体裁衣”或称“量体裁衣”、“称体裁衣”,这个思想大概最早见于《南齐书·张融传》:“(太祖)手诏赐融衣曰:‘今送一通故衣,意谓虽故乃胜新也,是吾所着,已令裁剪称卿之体’。”太祖皇帝把自己穿过的一通故衣赐予大臣张融,并事先按照张融的身材重新裁剪,以与其体相称。李渔认为,“相体裁衣之法,变化多端,不应胶柱而论”,大体说,面色白的,衣色可深可浅;面色黑的,宜深不宜浅,浅则愈形其黑矣;皮肤细的,衣服可精可粗,皮肤糙的,则宜粗不亦精,精则愈形其糙矣。这里的论述,缺点仍然在于只谈面色不谈体型,总使人觉得没有完全搔到痒处。
李渔谈服装美,还有几点值得称道:
他注意到衣服的审美与实用的关系。当谈到女子的裙子的时候,一方面他强调裙子“行走自如,无缠身碍足之患”的实用性;另方面他又强调裙子“湘纹易动,无风亦似飘摇”的审美性,应该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他特别注意衣服的色彩美。在谈“青色之妙”时,他提出要运用色彩的组合原理和心理效应来创造服装美。例如,可以通过色彩的对比来创造美的效果:面色白的,穿青色衣服,愈显得白;年少的穿它,愈显年少。可以通过色彩的融合或调和来掩饰丑或削弱丑的强度:面色黑的人穿青色衣服则不觉其黑,年纪老的穿青色衣服也不觉其老。可以通过色彩的心理学原理来创造衣服的审美效果:青色是最富大众性和平民化的颜色,正是青色给人的这种心理感受,可以转换成服装美学上青色衣服的如下审美效应--贫贱者衣之,是为贫贱之本等,富贵者衣之,又觉脱去繁华之习但存雅素之风,亦未尝失其富贵之本来。
他还特别注意到衣服色彩的流变。李渔描述了从明万历末到清康熙初五六十年间衣服色彩变化的情况:先是由银红桃红变为大红,月白变为蓝;过些年,则由大红变为紫,蓝变为石青;再过些年,石青与紫已经非常少见,男女老少都穿青色的衣服了。李渔的这段描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我们研究古代服装色彩流变的重要参考资料。
李渔的这些思想,曾得到林语堂先生的称赞,他在《生活的艺术》中引述李渔关于衣衫的一大段文字,说:“吾们又在他的谈论妇女‘衣衫’一节中,获睹他的慧心的观察。”
《鞋袜》原文并评:中国古代女子穿高底鞋
鞋袜【原文】
男子所着之履,俗名为鞋,女子亦名为鞋。男子饰足之衣,俗名为袜,女子独易其名曰“褶”,其实褶即袜也。古云“凌波小袜”,其名最雅,不识后人何故易之?袜色尚白,尚浅红;鞋色尚深红,今复尚青,可谓制之尽美者矣。鞋用高底,使小者愈小,瘦者越瘦,可谓制之尽美又尽善者矣。然足之大者,往往以此藏拙。埋没作者一段初心,是止供丑妇效颦,非为佳人助力。近有矫其弊者,窄小金莲,皆用平底,使与伪造者有别。殊不知此制一设,则人人向高底乞灵,高底之为物也,遂成百世不祧之祀,有之则大者亦小,无之则小者亦大。尝有三寸无底之足,与四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处,反觉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则指尖向下,而秃者疑尖,无底则玉笋朝天,而尖者似秃故也。吾谓高底不宜尽去,只在减损其料而已。足之大者,利于厚而不利于薄,薄则本体现矣;利于大而不利于小,小则痛而不能行矣。我以极薄极小者形之,则似鹤立鸡群,不求异而自异。世岂有高底如钱,不扭捏而能行之大脚乎?
古人取义命名,纤毫不爽,如前所云,以“蟠龙”名髻,“乌云”为发之类是也。独于妇人之足,取义命名,皆与实事相反。何也?足者,形之最小者也;莲者,花之最大者也;而名妇人之足者,必曰“金莲”,名最小之足者,则曰“三寸金莲”。使妇人之足,果如莲瓣之为形,则其阔而大也,尚可言乎?极小极窄之莲瓣,岂止三寸而已乎?此“金莲”之义之不可解也。从来名妇人之鞋者,必曰“凤头”。世人顾名思义,遂以金银制凤,缀于鞋尖以实之。试思凤之为物,止能小于大鹏;方之众鸟,不几洋洋乎大观也哉?以之名鞋,虽曰赞美之词,实类讥讽之迹。如曰“凤头”二字,但肖其形,凤之头锐而身大,是以得名;然则众鸟之头,尽有锐于凤者,何故不以命名,而独有取于凤?且凤较他鸟,其首独昂,妇人趾尖,妙在低而能伏,使如凤凰之昂首,其形尚可观乎?此“凤头”之义之不可解者也。若是,则古人之命名取义,果何所见而云然?岂终不可解乎?曰:有说焉。妇人裹足之制,非由前古,盖后来添设之事也。其命名之初,妇人之足亦犹男子之足,使其果如莲瓣之稍尖,凤头之稍锐,亦可谓古之小脚。无其制而能约小其形,较之今人,殆有过焉者矣。吾谓“凤头”、“金莲”等字相传已久,其名未可遽易,然止可呼其名,万勿肖其实;如肖其实,则极不美观,而为前人所误矣。不宁惟是,凤为羽虫之长,与龙比肩,乃帝王饰衣饰器之物也,以之饰足,无乃大亵名器乎?尝见妇人绣袜,每作龙凤之形,皆昧理僭分之大者,不可不为拈破。近日女子鞋头,不缀凤而缀珠,可称善变。珠出水底,宜在凌波袜下,且似粟之珠,价不甚昂,缀一粒于鞋尖,满足俱呈宝色。使登歌舞之氍毹,则为走盘之珠;使作阳台之云雨,则为掌上之珠。然作始者见不及此,亦犹衣色之变青,不知其然而然,所谓暗合道妙者也。予友余子澹心,向着《鞋袜辨》一篇,考缠足之从来,核妇履之原制,精而且确,足与此说相发明,附载于后。
附:
妇人鞋袜辨(余怀)
古妇人之足,与男子无异。《周礼》有屦人,掌王及后之服屦,为赤舄、黑舄、赤繶、黄繶、青絇、素履、葛屦,辨外内命夫命妇之功屦、命屦、散屦。可见男女之履,同一形制,非如后世女子之弓弯细纤,以小为贵也。考之缠足,起于南唐李后主。后主有宫嫔窅娘,纤丽善舞,乃命作金莲,高六尺,饰以珍宝,絅带缨络,中作品色瑞莲,令窅娘以帛缠足,屈上作新月状,着素袜,行舞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多效之,此缠足所自始也。唐以前未开此风,故词客诗人,歌咏美人好女,容态之殊丽,颜色之天姣,以至面妆首饰、衣褶裙裾之华靡,鬓发、眉目,唇齿、腰肢、手腕之婀娜秀洁,无不津津乎其言之,而无一语及足之纤小者。即如古乐府之《双行缠》云:“新罗绣白胫,足趺如春妍。”曹子建云:“践远游之文履”,李太白诗云:“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韩致光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杜牧之诗云:“钿尺裁量减四分”,汉《杂事秘辛》云:“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夫六寸八寸,素白丰妍,可见唐以前妇人之足,无屈上作新月状者也。即东昏潘妃,作金莲花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金莲花”,非谓足为金莲也。崔豹《古今注》:“东晋有凤头重台之履”,不专言妇人也。宋元丰以前,缠足者尚少,自元至今,将四百年,矫揉造作亦泰甚矣。古妇人皆着袜。杨太真死之日,马嵬媪得锦袎袜一只,过客一玩百钱。李太白诗云:“溪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袜一名“膝裤”。宋高宗闻秦桧死,喜曰:“今后免膝裤中插匕首矣。”则袜也,膝裤也,乃男女之通称,原无分别。但古有底,今无底耳。古有底之袜,不必着鞋,皆可行地;今无底之袜,非着鞋,则寸步不能行矣。张平子云:“罗袜凌蹑足容与。”曹子建云:“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李后主词云:“划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古今鞋袜之制,其不同如此。至于高底之制,前古未闻,于今独绝。吴下妇人,有以异香为底,围以精绫者;有凿花玲珑,囊以香麝,行步霏霏,印香在地者。此则服妖,(笠翁曰:“服妖”二字着眼,以此垂戒,非示劝也。)宋元以来,诗人所未及,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赋“香奁”、咏“玉台”者。
袜色与鞋色相反,袜宜极浅,鞋宜极深,欲其相形而始露也。今之女子,袜皆尚白,鞋用深红深青,可谓尽制。然家家若是,亦忌雷同。予欲更翻置色,深其袜而浅其鞋,则脚之小者更露。盖鞋之为色,不当与地色相同。地色者,泥土砖石之色是也。泥土砖石其为色也多深,浅者立于其上,则界限分明,不为地色所掩。如地青而鞋亦青,地绿而鞋亦绿,则无所见其短长矣。脚之大者则应反此,宜视地色以为色,则藏拙之法,不独使高底居功矣。鄙见若此,请以质之金屋主人,转询阿娇,定其是否。
【评】
从“鞋袜”款,我无意间获得了一个重要知识,即中国古代女子(至少一部分女子)是穿高底鞋的,这与西方女子穿高跟鞋相仿。过去我一直以为当下流行的女孩子或年青女人穿高跟鞋或高底鞋是从外国传来的,我们的老祖宗从无此物;现在我发现,最晚在李渔那个时代之前(前到什么时候说不准,大概不会在五代女子开始缠足之前),中国女子已经穿高底鞋(我猜想那高底鞋的跟也有点高,与高跟鞋相近)了。中国古代女子之穿高底鞋与西方女子之穿高跟鞋,从形式上看有点相似,但,我想她们的初衷大约是很不一样的。按照西方的传统,女子特别讲究形体美、线条美,她们的胸部和臀部都要有一种美的曲线突现出来,而一穿高跟鞋,自然就容易出这种效果。这是她们的高跟鞋的审美作用。而按照中国五代女子开始缠足之后的传统,小脚是一种美,而且愈小愈美。不但缠之使小,而且要用其他手段制造脚小的效果,于是高底鞋派上用场了:“鞋用高底,使小者愈小,瘦者愈瘦,可谓制之尽美又尽善者矣”;有了高底“大者亦小”,没有高底“小者亦大”。这是中国古代女子高底鞋的审美作用。我想,为了突现脚之小,若那高底鞋之跟也略高,效果会更显着一些。这也是前面我为什么猜想古代女子高底鞋之跟也有点高的原因。
但是,我早已表明我的态度:缠足是对女子的摧残;欣赏女子的小脚,是一种扭曲的、变态(病态)的审美心理。因而,我绝不认为古代女子穿高底鞋会有什么美。同样,如果现代女子穿高跟鞋有害健康的话,我认为女人付出这样的代价制造美的效果是不值得的。
《习技第四·小序》原文并评:男子中心主义
习技第四·小序【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