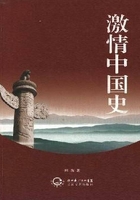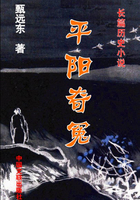凡作传奇,不宜频用方言,令人不解。近日填词家,见花面登场悉作姑苏口吻,遂以此为成律,每作净丑之白,即用方言,不知此等声音,止能通于吴越,过此以往,则听者茫然。传奇天下之书,岂仅为吴越而设?至于他处方言,虽云入曲者少,亦视填词者所生之地。如汤若士生于江右,即当规避江右之方言,粲花主人吴石渠生于阳羡,即当规避阳羡之方言。盖生此一方,未免为一方所囿。有明是方言,而我不知其为方言,及入他境,对人言之而人不解,始知其为方言者。诸如此类,易地皆然。欲作传奇,不可不存桑弧蓬矢之志。
【评】
《少用方言》与前面的《字分南北》应结合起来阅读,都是谈戏曲中方言使用问题。
使用方言,的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李渔当年不主张使用方言,是为了戏曲能够让不同地区的观众都听得懂。然而方言有时也可以成为塑造形象的有效手段,在现代戏剧、相声、小品中尤其如此。例如大家所熟悉的牛群等人说的相声,就用江苏方言塑造了一个公款吃喝的“科长”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黄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中的东北方言也收到很好的审美效果。所以,使用方言的功过是非须具体辨析,不可一概而论。
我最感兴趣的是李渔在这一节无意中触及了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他是从对《孟子》中“褐”字如何释义悟出这个道理来的。李渔认为连博学如朱熹者,对“褐”字也未能甚解,原因何在?在于朱熹生活在南方而不了解北方的生活。李渔游历西北,见“土着之民,人人衣褐”,才知道《孟子》“自反而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中“褐”之真义。原来,当地土着,以此一物而总“衫裳襦裤”,“日则披之当服,夜则拥以为衾”,是以“宽博”。由此,李渔幡然大悟:“太史公着书,必游名山大川,其斯之谓欤!”
创作无绝窍,生活是基础。大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当然,有了生活并不一定就能创作出好作品来;但是没有生活肯定不会有好作品产生。
《时防漏孔》评:焦循之辩
时防漏孔【原文】
一部传奇之宾白,自始自终,奚啻千言万语。多言多失,保无前是后非,有呼不应,自相矛盾之病乎?如《玉簪记》之陈妙常,道姑也,非尼僧也,其白云“姑娘在禅堂打坐”,其曲云“从今孽债染缁衣”,“禅堂”、“缁衣”皆尼僧字面,而用入道家,有是理乎?诸如此类者,不能枚举。总之,文字短少者易为检点,长大者难于照顾。吾于古今文字中,取其最长最大,而寻不出纤毫渗漏者,惟《水浒传》一书。设以他人为此,几同笊篱贮水,珠箔遮风,出者多而进者少,岂止三十六个漏孔而已哉!
【评】
智者千虑,亦难免有失。对李渔《时防漏孔》款所批评的《玉簪记》中陈妙常本道姑而用“尼僧字面”,清乾嘉间着名学者焦循(1763~1820)在《剧说》卷二中提出了不同意见:“陈为尼,而《玉簪》作道姑,盖以尼为剪发,于当场为不雅,本元人郑采作道姑耳。乃其曲‘从今孽债染缁衣’,又云‘姑娘在禅堂打坐’,则隐寓其为尼也。笠翁视之非是。”焦循所说很有道理。这与德国学者莱辛《拉奥孔》中所说绘画、雕刻为避免视觉上过于刺激而把拉奥孔被巨蛇缠杀画面做缓和处理一个道理。莱辛认为,“表达物体美是绘画的使命”,美(此处着重讲视觉上的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而在文学中则可以处理得更为激烈。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江巨荣、卢寿荣校注本《闲情偶寄》第73页将此注出,很好。今作说明,兹不掠美。
《科诨第五》原文并评:戏曲科诨和笑
科诨第五·小序【原文】
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钧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泥人作揖、土佛谈经矣。予尝以此告优人,谓戏文好处,全在下半本。只消三两个瞌睡,便隔断一部神情,瞌睡醒时,上文下文已不接续,即使抖起精神再看,只好断章取义,作零出观。若是,则科诨非科诨,乃看戏之人参汤也。养精益神,使人不倦,全在于此,可作小道观乎?
戒淫亵【原文】
戏文中花面插科,动及淫邪之事,有房中道不出口之话,公然道之戏场者。无论雅人塞耳,正士低头,惟恐恶声之污听,且防男女同观,共闻亵语,未必不开窥窃之门,郑声宜放,正为此也。不知科诨之设,止为发笑,人间戏语尽多,何必专谈欲事?即谈欲事,亦有“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之法,何必以口代笔,画出一幅春意图,始为善谈欲事者哉?人问:善谈欲事,当用何法,请言一二以概之。予曰:如说口头俗语,人尽知之者,则说半句,留半句,或说一句,留一句,令人自思。则欲事不挂齿颊,而与说出相同,此一法也。如讲最亵之话虑人触耳者,则借他事喻之,言虽在此,意实在彼,人尽了然,则欲事未入耳中,实与听见无异,此又一法也。得此二法,则无处不可类推矣。
忌俗恶【原文】
科诨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不俗则类腐儒之谈,太俗即非文人之笔。吾于近剧中,取其俗而不俗者,《还魂》而外,则有《粲花五种》,皆文人最妙之笔也。《粲花五种》之长,不仅在此,才锋笔藻,可继《还魂》,其稍逊一筹者,则在气与力之间耳。《还魂》气长,《粲花》稍促;《还魂》力足,《粲花》略亏。虽然,汤若士之《四梦》,求其气长力足者,惟《远魂》一种,其余三剧则与《粲花》并肩。使粲花主人及今犹在,奋其全力,另制一种新词,则词坛赤帜,岂仅为若士一人所攫哉?所恨予生也晚,不及与二老同时。他日追及泉台,定有一番倾倒,必不作妒而欲杀之状,向阎罗天子掉舌,排挤后来人也。
重关系【原文】
科诨二字,不止为花面而设,通场脚色皆不可少。生旦有生旦之科诨,外末有外末之科诨,净丑之科诨则其分内事也。然为净丑之科诨易,为生旦外末之科诨难。雅中带俗,又于俗中见雅;活处寓板,即于板处证活。此等虽难,犹是词客优为之事。所难者,要有关系。关系维何?曰: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使忠孝节义之心,得此愈显。如老莱子之舞斑衣,简雍之说淫具,东方朔之笑彭祖面长,此皆古人中之善于插科打诨者也。作传奇者,苟能取法于此,是科诨非科诨,乃引人入道之方便法门耳。
贵自然【原文】
科诨虽不可少,然非有意为之。如必欲于某折之中,插入某科诨一段,或预设某科诨一段,插入某折之中,则是觅妓追欢,寻人卖笑,其为笑也不真,其为乐也亦甚苦矣。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斯为科诨之妙境耳。如前所云简雍说淫具,东方朔笑彭祖,即取二事论之。蜀先主时,天旱禁酒,有吏向一人家索出酿酒之具,论者欲置之法。雍与先主游,见男女各行道上,雍谓先主曰:“彼欲行淫,请缚之。”先主曰:“何以知其行淫?”雍曰:“各有其具,与欲酿未酿者同,是以知之。”先主大笑,而释蓄酿具者。汉武帝时,有善相者,谓人中长一寸,寿当百岁。东方朔大笑,有司奏以不敬。帝责之,朔曰:“臣非笑陛下,乃笑彭祖耳。人中一寸则百岁,彭祖岁八百,其人中不几八寸乎?人中八寸,则面几长一丈矣,是以笑之。”此二事,可谓绝妙之诙谐,戏场有此,岂非绝妙之科诨?然当时必亲见男女同行,因而说及淫具;必亲听人中一寸寿当百岁之说,始及彭祖面长,是以可笑,是以能悟人主。如其未见未闻,突然引此为喻,则怒之不暇,笑从何来?笑既不得,悟从何有?此即贵自然、不贵勉强之明证也。吾看演《南西厢》,见法聪口中所说科诨,迂奇诞妄,不知何处生来,真令人欲逃欲呕,而观者听者绝无厌倦之色,岂文章一道,俗则争取,雅则共弃乎?
【评】
戏曲中插科打诨并非“小道”,也非易事。李渔把它比作“看戏之人参汤”,乃取其“养精益神”之意。这个比喻虽不甚确切,却很有味道。
科诨是什么?表面看来,就是逗乐、调笑;但是,往内里想想,其中有深意存焉。人生有悲有喜,有哭有笑。悲和哭固然是免不了的,喜和笑也是不可缺少的。试想,如果一个人不会笑、不懂得笑,那将何等悲哀、何等乏味?现在姑娘们找对象,就常常喜欢找那种有幽默感的。因此,会笑乃是人生的一种财富。戏剧的功能之一就是娱乐性;娱乐,就不能没有笑。戏曲中的笑(包括某部戏中的插科打诨,也包括整部喜剧),说到底也是基于人的本性。但是,观众笑什么?为什么笑?如何引他们发笑(总不能像相声里所说的,观众本不想笑,硬是去咯吱他让他发笑吧)?这里面大有学问。笑有不同种类、不同性质、不同内涵。譬如有纯生理的笑,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的笑、用手咯吱使人发笑等等即属此类;但人的大多数笑都有社会的、文化的意义。有无意识、下意识的笑,但大多数笑是有意识的。有肯定性的、赞许的笑,但有相当多的笑是否定性的、像刀子一样尖利的。有的笑是爱,有的笑是恨。有的笑是笑自己,有的笑是笑别人。有的自以为是笑别人,实际上是笑自己,果戈里《钦差大臣》演到最后,演员指着满场笑着的观众说:“你们是在笑自己!”笑的样子也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微笑、大笑、狂笑、傻笑、抿着嘴笑、咧开口笑、低着头笑、仰着脸笑、捧腹而笑、击掌而笑、嘻嘻而笑、吃吃而笑、强笑、苦笑、讪笑、淫笑、冷笑、阴笑、奸笑、蠢笑、天真的笑、羞涩的笑、会心的笑、得意的笑、放肆的笑、无聊的笑、刻薄的笑、挖苦的笑、忧郁的笑、开心的笑、皮笑肉不笑、含着眼泪笑、低三下四的笑、无可奈何的笑、连讽带刺的嘲笑、歇斯底里的疯笑……那么,戏曲中的笑是什么样的笑?我想,这种笑就其种类、性质、内涵和形态来说,应该是比较宽泛的;现实中自然状态的一切笑都可以作为它的原料。但是,它有一个最低限,那就是经过戏曲家的艺术创造,它必须是具有审美意味的、对人类无害有益的。这是戏曲中笑的起跑线。从这里起跑,戏曲家有着无限广阔的创造天地,可以是低级的滑稽,可以是高级的幽默,可以是正剧里偶尔出现的笑谑(插科打诨),可以是整部精彩的喜剧……当然,不管是什么情况,观众期盼着的都是艺术精品,是戏曲作家和演员的“绝活”。
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科诨第五》的四款中所探讨的就是这个范围里的部分问题。前两款,“戒淫亵”和“忌俗恶”,是从反面对科诨提出的要求,要避免低级下流和庸俗不堪--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是需要注意的,有的戏,喜欢用些“赃话”和“赃事”(不堪入目的动作)来引人发笑,实在是应该禁戒的恶习。后两款,“重关系”和“贵自然”,是从正面对科诨提出的要求,要提倡寓意深刻和自然天成,“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他所举“简雍之说淫具”和“东方朔之笑彭祖面长”,雅俗共赏,非常有趣,的确是令人捧腹的好例子。
《格局第六》评:中西戏剧“格局”之比较
格局第六·小序【原文】
传奇格局,有一定而不可移者,有可仍可改,听人自为政者。开场用末,冲场用生;开场数语,包括通篇,冲场一出,蕴酿全部,此一定不可移者。开手宜静不宜喧,终场忌冷不忌热,生旦合为夫妇,外与老旦非充父母即作翁姑,此常格也。然遇情事变更,势难仍旧,不得不通融兑换而用之,诸如此类,皆其可仍可改,听人为政者也。近日传奇,一味趋新,无论可变者变,即断断当仍者,亦加改窜,以示新奇。予谓文字之新奇,在中藏,不在外貌,在精液,不在渣滓,犹之诗赋古文以及时艺,其中人才辈出,一人胜似一人,一作奇于一作,然止别其词华,未闻异其资格。有以古风之局而为近律者乎?有以时艺之体而作古文者乎?绳墨不改,斧斤自若,而工师之奇巧出焉。行文之道,亦若是焉。
家门【原文】
开场数语,谓之“家门”。虽云为字不多,然非结构已完、胸有成竹者,不能措手。即使规模已定,犹虑做到其间,势有阻挠,不得顺流而下,未免小有更张,是以此折最难下笔。如机锋锐利,一往而前,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则从此折做起;不则姑缺首篇,以俟终场补入。犹塑佛者不即开光,画龙者点睛有待,非故迟之,欲俟全像告成,其身向左则目宜左视,其身向右则目宜右观,俯仰低徊,皆从身转,非可预为计也。此是词家讨便宜法,开手即以告人,使后来作者未经捉笔,先省一番无益之劳,知笠翁为此道功臣,凡其所言,皆真切可行之事,非大言欺世者比也。
未说家门,先有一上场小曲,如《西江月》、《蝶恋花》之类,总无成格,听人拈取。此曲向来不切本题,止是劝人对酒忘忧、逢场作戏诸套语。予谓词曲中开场一折,即古文之冒头,时文之破题,务使开门见山,不当借帽覆顶。即将本传中立言大意,包括成文,与后所说家门一词相为表里。前是暗说,后是明说,暗说似破题,明说似承题,如此立格,始为有根有据之文。场中阅卷,看至第二三行而始觉其好者,即是可取可弃之文;开卷之初,能将试官眼睛一把拿住,不放转移,始为必售之技。(王左车云:先生之文,篇篇若是;先生之书,部部若是。所谓现身说法者也。)吾愿才人举笔,尽作是观,不止填词而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