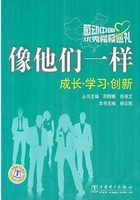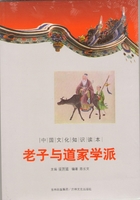《语求肖似》评:李渔谈艺术想象
语求肖似【原文】
文字之最豪宕,最风雅,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过填词一种。若无此种,几于闷杀才人,困死豪杰。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觉富贵荣华,其受用不过如此,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非若他种文字,欲作寓言,必须远引曲譬,蕴藉包含,十分牢骚,还须留住六七分,八斗才学,止可使出二三升,稍欠和平,略施纵送,即谓失风人之旨,犯佻达之嫌,求为家弦户诵者难矣。填词一家,则惟恐其蓄而不言,言之不尽。是则是矣,须知畅所欲言亦非易事。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无论立心端正者,我当设身处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当舍经从权,暂为邪辟之思。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浒传》之叙事,吴道子之写生,斯称此道中之绝技。果能若此,即欲不传,其可得乎?
【评】
这是一篇谈艺术想象的妙文。妙在哪里?妙在李渔不但能把艺术家进行创造性想象时“为所欲为”、“畅所欲言”的自由驰骋的状态描绘得活灵活现;而且,还特别妙在李渔揭示出艺术家进行想象时必须具有自觉控制的意识,所谓“设身处地”,代人“立心”。艺术想象,看似无拘无束、绝对自由,“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刘勰),好象艺术家在想象时完全处于一种失去理智的不清醒的疯狂的无意识状态;实则“自由”并非“绝对”,“疯狂”却又“清醒”,“无意识”中有“理智”在,即刘勰所谓“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艺术想象是“醉”与“醒”的统一,是“有意识”与“无意识”的融合。艺术想象好像作家放到空中的一只风筝,人们看到那风筝伴着蓝天白云,自由自在、随意飘弋;但是,在放那只“风筝”时,始终有一根线攥在作家手里,那“线”,就是自觉的“意识”和“理智”。艺术想象有点像“打醉拳”,亦醉亦醒,半醉半醒,醒中有醉,醉中有醒,表面醉、内里醒。全醉,会失了拳的套数,打的不是“拳”;全醒,会失掉醉拳的灵气,醉意中“打”出来的风采和臆想不到的效果丢失殆尽。李渔既看到“醉”的一面,所谓“梦往神游”;也看到“醒”的一面,即作家对“梦往神游”的有意识控制。他认为作家必须清醒地为人物“立心”:“立心端正者”,要“代生端正之想”;“立心邪辟者,我亦当舍经从权,暂为邪辟之思”。这段话使我想起俄国大作家高尔基关于艺术想象的有关论述。高尔基在《论文学技巧》一文中比较科学家与文学家之不同时说:“科学工作者研究公羊时,用不着想象自己也是一头公羊,但是文学家则不然,他虽慷慨,却必须想象自己是个吝啬鬼,他虽毫无私心,却必须觉得自己是个贪婪的守财奴,他虽意志薄弱,但却必须令人信服地描写出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你看,这两位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在谈到艺术想象时,几乎连用语都一样,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然而,李渔却早高尔基近三百年。
由此,我惊叹李渔的才智。
《词别繁减》评:意则期多,字惟求少
词别繁减【原文】
传奇中宾白之繁,实自予始。海内知我者与罪我者半。知我者曰:从来宾白作说话观,随口出之即是,笠翁宾白当文章做,字字俱费推敲。从来宾白只要纸上分明,不顾口中顺逆,常有观刻本极其透彻,奏之场上便觉糊涂者,岂一人之耳目,有聪明聋聩之分乎?因作者只顾挥毫,并未设身处地,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心口相维,询其好说不好说,中听不中听,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笠翁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罪我者曰:填词既曰“填词”,即当以词为主;宾白既名“宾白”,明言白乃其宾,奈何反主作客,而犯树大于根之弊乎?笠翁曰:始作俑者,实实为予,责之诚是也。但其敢于若是,与其不得不若是者,则均有说焉。请先白其不得不若是者。前人宾白之少,非有一定当少之成格。盖彼只以填词自任,留余地以待优人,谓引商刻羽我为政,饰听美观彼为政,我以约略数言,示之以意,彼自能增益成文。如今世之演《琵琶》、《西厢》、《荆》、《刘》、《拜》、《杀》等曲,曲则仍之,其间宾白、科诨等事,有几处合于原本,以寥寥数言塞责者乎?且作新与演旧有别。《琵琶》、《西厢》、《荆》、《刘》、《拜》、《杀》等曲,家弦户诵已久,童叟男妇皆能备悉情由,即使一句宾白不道,止唱曲文,观者亦能默会,是其宾白繁减可不问也。至于新演一剧,其间情事,观者茫然;词曲一道,止能传声,不能传情。欲观者悉其颠末,洞其幽微,单靠宾白一着。予非不图省力,亦留余地以待优人。但优人之中,智愚不等,能保其增益成文者悉如作者之意,毫无赘疣蛇足于其间乎?与其留余地以待增,不若留余地以待减,减之不当,犹存作者深心之半,犹病不服药之得中医也。此予不得不若是之故也。至其敢于若是者,则谓千古文章,总无定格,有创始之人,即有守成不变之人;有守成不变之人,即有大仍其意,小变其形,自成一家而不顾天下非笑之人。古来文字之正变为奇,奇翻为正者,不知凡几,吾不具论,止以多寡增益之数论之。《左传》、《国语》,纪事之书也,每一事不过数行,每一语不过数字,初时未病其少;迨班固之作《汉书》,司马迁之为《史记》,亦纪事之书也,遂益数行为数十百行,数字为数十百字,岂有病其过多,而废《史记》、《汉书》于不读者乎?此言少之可变为多也。诗之为道,当日但有古风,古风之体,多则数十百句,少亦十数句,初时亦未病其多;迨近体一出,则约数十百句为八句;绝句一出,又敛八句为四句,岂有病其渐少,而选诗之家止载古风,删近体绝句于不录者乎?此言多之可变为少也。总之,文字短长,视其人之笔性。笔性遒劲者,不能强之使长;笔性纵肆者,不能缩之使短。文患不能长,又患其可以不长而必欲使之长。如其能长而又使人不可删逸,则虽为宾白中之古风《史》《汉》,亦何患哉?予则乌能当此,但为糠秕之导,以俟后来居上之人。
予之宾白,虽有微长,然初作之时,竿头未进,常有当俭不俭,因留余幅以俟剪裁,遂不觉流为散漫者。自今观之,皆吴下阿蒙手笔也。如其天假以年,得于所传十种之外,别有新词,则能保为犬夜鸡晨,鸣乎其所当鸣,默乎其所不得不默者矣。
【评】
“词别繁简”和后面的“文贵洁净”,这两款前后照应,谈宾白如何做到“繁”、“简”得当;其中道理也适用于整个戏曲和一切文章的写作。我又一次惊服李渔的高明!他的许多观点拿到今天也是十分精彩的。
何为“繁”,何为“简”?这不能简单地以文字多少而论。李渔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多而不觉其多者,多即是洁;少而尚病其多者,少亦近芜。”譬如,由“诗三百”一般四言数句之“简”,到“楚辞”,特别是屈原《离骚》一般六言、七言,数十句、数百句之“繁”;由《左传》、《国语》每事数行、每语数字之“简”,到《史记》、《汉书》一事数百行,洋洋千言、万言之“繁”,人们既不感到前者太“少”,也并不觉得后者太“多”,这就是它们写得都很“洁净”、精粹,话说得得当,恰到好处,没有多余的东西。如果以为话说得愈多愈好,文章写得愈长愈好,“唱沙作米”、“强凫变鹤”,杂芜散漫,废话连篇,如现在某些电视连续剧那样,一集的内容硬拉为两集、三集,一部连续剧非要数十集、上百集才完,那真是读者和观众的灾难!
必须学会以“意则期多,字惟求少”的标准删改文章。李渔说:“每作一段,即自删一段,万不可删者始存,稍有可删者即去。”“凡作传奇,当于开笔之初,以至脱稿之后,隔日一删,逾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鲁迅和许多外国大作家也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鲁迅主张把一切多余的字、词、句都毫不可惜地删去,并且尽量不用形容词;宁肯把小说压缩为速写,绝不肯把速写拉成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应该毫不惋惜地删去一切含糊、冗长、不恰当的地方”;“紧凑常常能使叙述显得更精彩。如果读者听到的是废话,他对它就不会注意了”。契诃夫说:“写作的技巧,其实并不是写作的技巧,而是……删掉写得不好的地方的技巧。”“把每篇小说都改写五次,缩短它。”“写得有才华就是写得短。”
修改和删节的结果,就是使得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都用得是地方,即李渔所谓“犬夜鸡晨,鸣乎其所当鸣,默乎其所不得不默”。有时候,说不如不说,多说不如少说。列夫·托尔斯泰说:“与其说得过分,不如说得不全。”语言的锤炼工夫是一个很苦的过程。福楼拜谈到他写作的情况时这样说:“转折的地方,只有八行……却费了我三天。”“已经快一个月了,我在寻找那恰当的四五句话。”中国古代诗人为了锤炼语言也费尽心机:“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贾岛),“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李频),“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卢延让),“日日为诗苦,谁论春与秋”(归仁和尚)。还有那个为写诗而呕心沥血的李贺。《新唐书·李贺传》中说,李贺每天一早骑一瘦马出门,一路吟哦,得句便写在纸条上投入囊中,暮归,再补足成一首首诗。他母亲十分心疼,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
字分南北【原文】
北曲有北音之字,南曲有南音之字,如南音自呼为“我”,呼人为“你”,北音呼人为“您”,自呼为“俺”为“咱”之类是也。世人但知曲内宜分,乌知白随曲转,不应两截。此一折之曲为南,则此一折之白悉用南音之字;此一折之曲为北,则此一折之白悉用北音之字。时人传奇多有混用者,即能间施于净丑,不知加严于生旦;此能分用于男子,不知区别于妇人。以北字近于粗豪,易入刚劲之口,南音悉多娇媚,便施窈窕之人。殊不知声音驳杂,俗语呼为“两头蛮”,说话且然,况登场演剧乎?此论为全套南曲、全套北曲者言之,南北相间,如《新水令》、《步步娇》之类,则在所不拘。
文贵洁净【原文】
白不厌多之说,前论极详,而此复言洁净。洁净者,简省之别名也。洁则忌多,减始能净,二说不无相悖乎?曰:不然。多而不觉其多者,多即是洁;少而尚病其多者,少亦近芜。予所谓多,谓不可删逸之多,非唱沙作米、强凫变鹤之多也。作宾白者,意则期多,字惟求少,爱虽难割,嗜亦宜专。每作一段,即自删一段,万不可删者始存,稍有可削者即去。此言逐出初填之际,全稿未脱之先,所谓慎之于始也。然我辈作文,常有人以为非,而自认作是者;又有初信为是,而后悔其非者。文章出自己手,无一非佳;诗赋论其初成,无语不妙。迨易日经时之后,取而观之,则妍媸好丑之间,非特人能辨别,我亦自解雌黄矣。此论虽说填词,实各种诗文之通病,古今才士之恒情也。凡作传奇,当于开笔之初,以至脱稿之后,隔日一删,逾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无瑕瑜互见之失矣。此说予能言之不能行之者,则人与我中分其咎。予终岁饥驱,杜门日少,每有所作,率多草草成篇,章名急就,非不欲删,非不欲改,无可删可改之时也。每成一剧,才落毫端,即为坊人攫去,下半犹未脱稿,上半业已灾梨;非止灾梨,彼伶工之捷足者,又复灾其肺肠,灾其唇舌,遂使一成不改,终为痼疾难医。(声伯云:文章至此,可称无翼而飞。“曲子相公”之不能收拾,即若是也。快哉!文人古今有几?)予非不务洁净,天实使之,谓之何哉!
《意取尖新》评:说“尖新”
意取尖新【原文】
纤巧二字,行文之大忌也,处处皆然,而独不戒于传奇一种。传奇之为道也,愈纤愈密,愈巧愈精。词人忌在老实,老实二字,即纤巧之仇家敌国也。然纤巧二字,为文人鄙贱已久,言之似不中听,易以尖新二字,则似变瑕成瑜。其实尖新即是纤巧,犹之暮四朝三,未尝稍异。同一话也,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意懒心灰,有如听所不必听。白有尖新之文,文有尖新之句,句有尖新之字,则列之案头,不观则已,观则欲罢不能;奏之场上,不听则已,听则求归不得。尤物足以移人,尖新二字,即文中之尤物也。
【评】
戏剧作家应该注意遣词造句时选取“尖新”字眼儿。“尖新”,是李渔在论宾白时提出的要求,其实它何尝不适宜于唱词?李渔所谓“尖新”,是对“老实”而言。他说:“同一语也,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意懒心灰,有如听所不必听。白有尖新之文,文有尖新之句,句有尖新之字,则列之案头,不观则已,观则欲罢不能;奏之场上,不听则已,听则求归不得。尤物足以移人,尖新二字即文中之尤物也。”显然,所谓“尖新”者,一方面是指语言要新鲜而不陈腐,另方面是指语言要生动活泼,富有表现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李渔之“尖新”,含有王骥德之“溜亮”、“轻俊”、“新采”、“芳润”等意思在内,趣味十足,令人眉扬目展。好的戏剧,其语言都应该是“机趣”、“尖新”的。例如老舍《茶馆》第二幕中一段台词:唐铁嘴对王利发说:“我已经不抽大烟了!”王利发对此很惊讶:“真的?你可要发财了!”接下去唐铁嘴的台词可谓“尖新”、“机趣”:“我改抽‘白面’啦。你看,哈德门烟又长又松,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侯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再如,关肃霜主演的京剧《铁弓缘》,许多台词也很有机趣,可称尖新。剧中老太太回答那个官宦恶少求婚时说:“蚊子叮了泥菩萨--你认错人了!”这是一句歇后语,用在这里十分贴切,令观众开怀、捧腹。
《少用方言》评:使用方言,贵在得当
少用方言【原文】
填词中方言之多,莫过于《西厢》一种,其余今词古曲,在在有之。(王宓草云:石破天惊,轰雷四起。)非止词曲,即《四书》之中,《孟子》一书亦有方言,天下不知而予独知之,予读《孟子》五十余年不知,而今知之,请先毕其说。儿时读“自反而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观朱注云:“褐,贱者之服;宽博,宽大之衣。”心甚惑之。因生南方,南方衣褐者寡,间有服者,强半富贵之家,名虽褐而实则绒也。因讯蒙师,谓褐乃贵人之衣,胡云贱者之服?既云贱衣,则当从约,短一尺,省一尺购办之资,少一寸,免一寸缝纫之力,胡不窄小其制而反宽大其形,是何以故?师默然不答。再询,则顾左右而言他。具此狐疑,数十年未解。及近游秦塞,见其土着之民,人人衣褐,无论丝罗罕觏,即见一二衣布者,亦类空谷足音。因地寒不毛,止以牧养自活,织牛羊之毛以为衣,又皆粗而不密,其形似毯,诚哉其为贱者之服,非若南方贵人之衣也!又见其宽则倍身,长复扫地。即而讯之,则曰:“此衣之外,不复有他,衫裳襦裤,总以一物代之,日则披之当服,夜则拥以为衾,非宽不能周遭其身,非长不能尽覆其足。《鲁论》‘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即是类也。”予始幡然大悟曰:“太史公着书,必游名山大川,其斯之谓欤!”盖古来圣贤多生西北,所见皆然,故方言随口而出。朱文公南人也,彼乌知之?(胆大包身,始能发此快论。然有此识,方有此胆,胆亦不易大也。)故但释字义,不求甚解,使千古疑团,至今未破,非予远游绝塞,亲觏其人,乌知斯言之不谬哉?由是观之,《四书》之文犹不可尽法,况《西厢》之为词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