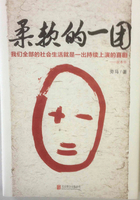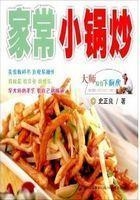其时,县长巳经喝了两杯当地窖藏的老酒,酡红了一张脸,端了酒杯到门口去道,朱大夫好大的面子,迟来当罚喔!
朱风高一扬手,早有随从自车上抬下一只土黄色的泥坛。一层泥一层糙纸一层荷叶地小心揭了覆瓿,顿时一股沁人的酒香四下里明亮地流淌。
人们先是一愣,继之起了一片欢腾!县长随即将酒杯泼了,嚷道,这才是真正的老酒呢!清亮的酒汩汩筛出来,先筛在一把长嘴大锡壶里,再两手高擎,筛在一只又一只的纹边蓝花碗里,刚亮的香气更猛烈了。
看见大家喝得尽兴,朱风高笑了,他翕动着鼻翼,一对猫眼神采四溢。他告诉来客,这坛酒还是他十七年前正式拜师学医时埋下的。随即一挥手,随从又捧出一只造型奇特色泽古旧的六角箱。箱子的五面各有一个锁绊子,启开来,朱风高小心地掣出一件青玉佛手。这件佛手折技带叶,下端附丽一只小佛手,白中带灰,肌理滋润,巧夺天工。
一位缙绅站起来说,佛手多指,指子谐音,指就是子,朱先生是祝罗先生与我太太多子多福呀!
朱风高喃喃道,这是真正的新疆和田玉。当下交给罗雨田。罗雨田感激万分,连连道,这我怎么担待得起呀!这一宴,喝倒了两个人,这就是朱风高与罗雨田。朱风高的红脸与罗雨田的白脸恰成对照。朱朝罗的脸上打了拳,打得鲁莽而又准确,罗的嘴角流出一线血。罗回敬了一拳,绵软无力。两人后来就卧在地上,互相揪着,谁也听不明白地骂着,呕吐着,成了一摊泥。
是夜,陈秀美把一直醉着的罗雨田清洗干净,守在他身边一夜没合眼。她在帮他清洗的时候,发现朱风高那一拳,击断了他一只门牙。这个已经成为她丈夫的卧在她身边的男人,此刻显得如此懦弱,顿时激起她心中一片悲悯之情。
那一夜,她诅骂她曾爱恋过的朱风高。
我承认罗小青的敬业精神比我强。
我对各种宣传百般灵验的东西始终抱有一定程度的怀疑,对桐木拳功也不例外,这障碍了我的一心一意。
小青分析这是我的思维方式的障碍,理性意识太强的人,下意识就排斥感性。传统得医学等等就目前的科技水平,很难参透,它是一种更多地诉诸感性而非理性的东西。所以,小青屡屡提醒我,相信直觉,痴恋感受!
五月,我与小青来到湘赣边境一个叫幕家山的地方。我们准备地这里建一个基地。小青说,这里山清水秀,水好空气好,气场自然也不错尤其是交通还便利,生活方便,一个大集镇就在我们桐木拳功选下的疗养院两三里之内。
实际上,基地基本上是现成的。一个圮废的军营旧址,草木萋萋,却房舍俨然。将这四排平房的门窗修缮一下,配上简单的床褥,就可以投入经营了。
“文革”时听说这里驻扎了一个团。后来,部队迁走了。房子无偿给了地方。地方始终没有将这几排平房派上用场,不知是当地农民不习惯这种教室式的平房,还是嫌它距离热闹的村镇有些路程的缘故。房门不掩,每间屋都是一些牧羊放牛者的栖息地,胡乱堆放禾草、断砖、残木,人溺畜粪,騷臭弥漫。
以前联系,幕家山镇的干部都很随意,他们说,反正我们闲置没用,你们拿去用,正好。房租多点少点,没有大关系的。一旦我们前期准备工作就绪,正式与幕家山签合同,他们就咬文嚼字了。镇长说,这地方风景不错,气候也好,夏天比外头低两三度,他们早就有意向办个疗养院了。副镇长说,县财政局、粮食局、民政局,甚至农业银行都表示过类似的意思。甲方出地,乙方出钱,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言下之意,此前的意向不做数了。
趁便时,我低声与小青耳语道,看来,不让些股份给他们不行。
小青不露声色道,这些人的胃口!外来和尚都是唐僧肉!谈得成就谈,谈不成就只有走上层。
一顿饭下来,我是不能喝,小青尽管饭量小酒囊大,也架不住这群乡镇干部轮番“打箍”。小青几次握着唇,做欲吐状,他们依然不饶,小青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各种名目各种说道陪饮。一圈诸侯们都酒气熏天,东倒西歪了,小青这时搁出早已拟好的合同,说,这是你们先前就看过了,镇长签过字以后,等会叫主任盖个章。说时间,笔已经塞到了解情况镇长手里。
镇长也斜了眼看过一遍说,不急吧,不急,还没吃完酒呢。随手就交给了办公室主任。
吃罢饭,我和小青交换了一下目光,就跟镇长说,签完合同我们就得往回赶了,路上还有活动。
镇长说,你们深圳人也太讲时间就是金钱了。找主任就行,我都交代了的。说完就与我们握别。
随主任到办公室,他却掏出一份他们早拟好的合同。合同上说,幕家山镇以房屋共两千四百平米,场地约一万平米人股,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五十五。派人参与财务管理。
小青勃然色变,道,你们就是几幢破房子投人,还想控股,这不是昏了头吧?
主任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说,罗小姐从深圳来,应该知道,召集最有价值的,就是房地产。
我说,如果你们这片破房子与荒地在深圳,我们愿意给你们百分之九十的股份。
主任狡猾一笑,道,是的,因为不在深圳,所以我们占了百分之五十几,让利很大了。
小青说,看来,找你这个办事员,是办不成事的。主任并不恼道,官大一级压死人,罗小姐应该体谅我这个小小办事员。
于是我们驱车径往县城去。在县里,我们曾与肖县长见过一面,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肖县长说,只要外面带资金进来,搞合法经营,不管经营什么我们都提供便利。
找了一圈,才在一家再生橡胶厂找到肖县长。这家厂子投资一千万,才刚见到效益,就有人状告上去,认为三废污染严重,分管环保的省长助理亲自打电话来问。据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也得到消息,拟过问此事。肖县长心里沉甸甸的,我们来的不是小青灵机一动,她跟本省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关系很好,可以通过他去有关部门解释一下,本厂正在加大力度治理三废,甚至,就可以先发再生橡胶厂积极治理三废的消息。肖县长当即叫小青用他的手机拨电话给副部长。小青先问对方坚持练了桐木拳功没有,叫他贵在坚持。然后谈到本县,谈到一把手在厂里督促治理三废云云。副部长认为这样很好,值得宣传。小青收了线,就赶紧叫肖县长组织一篇文章寄去,副部长出面,发省报没问题的。肖县长回头就叫秘书安排稿子。
小青说,县长整天心忙得脚不沾地,我就是有意请县长练练桐木拳功也无法说出口了。
肖县长说,会的会练的。又问,幕家山去了。小青眉头一蹙,就把镇里的遭遇娓娓说了一遍。肖县长摇摇头道,我们的有些中层干部就是这样,叶公好龙,整天希望龙来呀,龙来呀,一旦来了,又怕龙吃了他的饭,喝了他的酒,挣了他的钱!
小青说,其实,我这疗养院办起来,四面八方,全国各地,五色人等,什么人没有?不定里头就有几个富商看好你这里,愿意投资呢?为什么要竭泽而渔,把我搞得一点积极性没有才好!我们这也是为当地造福来的。
我告诉县长,想请我们去办疗养院的地方很多,就在广东,也有许多嘉山秀山。
肖县长说,说到底,还是一个观念问题!他答应跟幕家山的镇长说一下,叫他为我们一路开绿灯。
见肖县长语气肯定,我和小青这才放下心来。
1942年的蔡里是多事之秋。
春天里发生了一场前所未见的鼠疫。这场瘟疫开始在乡下播弄,骇住了的农民看见一户一户的门庭圮颓,死者横陈道途,便无比张惶地逃向县城。
尽管此前省卫生署得到情报以后,明令各村所务必在卫生检疫部门的来之前,控制村民不得外出,又哪里挡得住发乎内心的恐惧所带来的潮涌一般的逃亡欲。人们甚至顾不得掩埋妻子儿女的尸体,就没头苍蝇似地沿着大路奔跑。有些人跑着跑着,就一头栽在路边的沟渠里,吓得企望捧喝渠水的人没命似的拔脚就跑。
富鑫饭馆的何胖子孙早在闻到风声之前,就聪明地停业休息,与此同时却大肆囤集米面薪炭。然后大门坚扃,拒人于千里之外。
当两眼饿得发绿的灾民大大街小巷鬼魂一样地游走的时候,何胖子暗自庆幸自己的先见之明。
那天,何胖子的女儿正在为每日吃腌腊肉,没有蔬菜吃而发牢骚,何胖子的老婆教训女儿说,有米有肉,你还不知足,你看外头啊,几多人把地里的荠菜、马齿苋都吃光了,你恁不晓得知足!女儿嘟哝道,我想吃荠菜。
忽就见梁间一团灰物扑哧一声掉在桌上。母女俩吓了一跳,定睛看时,原来是一一只老鼠。待得何胖子闻讯走过来,看见桌子正中那只肥硕的老鼠,脸色抖然一变,癒癒巴巴地说,大祸临头了。我没想到……人,进不来,老鼠,会钻进来。
第二天早上,何胖子的女儿就寒战,盖两床被子还牙齿磕磕。到晚上就高烧,热得连一件贴身的汗褂子也兜不住。接着是双腿与胳膊上的酱紫色淤斑,稍一碰就溃烂出血。
何胖子看着鼻息渐弱的女儿,疯也似地跑出去找朱风高。朱风高的家里有一股混合着中草药的烟熏气。何胖子好不容易敲开他家的门,朱医生说,你没看见我门上的招帖么,和你一样,我早就停业了。
何胖子单腿就跪下了,说,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分上,救我女儿一命吧。
朱风高摇头,不是我不救你女儿,实在是我回天无力,你找罗雨方去吧,他是新医,或许有些办法。罗雨方身上是另一股呛人的药水气息。罗医生听了何胖子的哭诉,二话没说,背起药箱就出发他到何宅,看了何胖子女儿一眼就说,人已经没有办法了,准备料理后事吧。说着,已然从药箱里掣出一把乌亮的手推喷筒,四下里喷去,一股乳白的雾水散出来。此事过去多年以后,何胖子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把喷筒给他留下的最初印象,像极了男人胯下的那个物件。何胖子的上下寓所,四处缭绕着呛人的药水气息。在女儿渐渐僵硬的尸体面前,何胖子的老婆涕泗横流。罗雨方警告她不要靠前。何胖子在院墙的枇杷树下,指挥雇工掘地。连棺木也来不及置办,就将女儿勉强塞进一只垛柜里掩埋了。
当罗雨方在坟土四周喷药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苍凉的声音,不要喷了,这种药未必有用。是朱风高。
朱风高从一只皮囊里掏出一种褐色的粉末,手腕一抖,四下里散开,空气中立刻弥漫着辛辣的气息。人人掩鼻,咳嗽不止。一时泪流满面。朱风高说,咳一咳有好处,把病毒都咳出来了。两天后,何胖子的老婆也死了。
但是,何胖子的两个儿子活过来了,当然还有何胖子。何胖子相信,之所以遭大难而不曾满门皆杀,是医生的救治之功。但他不知是西医罗雨方还是中医朱风高之功。他只记得,在后来的日子里,罗雨方与朱风高双双出现在蔡里的大街小巷。他俩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配合默契。一个喷药雾,一个洒药粉。
开始人们还躲避着,害怕这股难离的气息,很快的,只要这股药味传来,就前呼后拥,像接受洗礼一般,承受着药水与药粉的沐浴。
一个半月以后,瘟疫败退,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在蔡里留下二百零八具尸体。年长者七十八岁,小的不足半岁。
这年秋季,蔡里再遭一劫,日本精锐部队的坂垣师团在江洲一线遭到国民党集团军的顽强抵抗,坂垣师团的第三团突破防线以后,突进蔡里。遭遇抵抗之后如入无人之境的日本将士顿时将蔡里作为凶残报复的对象。他们三五成群地闯进商家与民宅,刀劈不足月的婴儿,用铁丝将姑娘与老妪的奶头串在一起,然后将裸体的一群女人赶上大街,并不断用刺刀在她们背上、腿上以及胸前划着,鲜血一路流淌。尖利的哭声如同焚烧后的硝烟,白天黑夜地缭绕在蔡里的上空,久久不散。
直到日本撤退以后,才有国民党军队开进蔡里,然而,巳经是满目疮痍。
那段日子,朱家与罗家医寓安排不下这么多的伤病员。残腿的断臂的割掉了鼻子或者耳朵的,一个姑娘的两个奶头均被割掉,还有一个中年妇女的生殖器被塞满了沙土……惨状令朱罗两人双手颤抖,泪水迷蒙。
无论如何他俩也不能照顾这么多的伤残者,于是商定在东门的集市搭一个临时大诊所,将蔡里的大小郎中都聚集起来,统一诊治,这个意见很快得到蔡里人包括县府官员的一致肯定与拥护。
幕家山疗养基地的建立,据初步估算,需要我们投入五十万左右,这当然不包括进一步的完善,比如搞一个像样的食堂,一个拳功房,以及阅览室等。
小青愁眉紧锁,钱不凑手,到哪去筹措这许多钱哪!我知道佳佳公司经营不善,劳心费力,只能说略有盈余。小青的发展已有往房地产、运输业渗透的意向,经费的确不会太宽松。但是,我坚持认为投入传统医药功法的疗养,回报率高,无甚风险,颇值得另眼相睐。你看一个嵩山少林寺,是多少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当然,我们起步之初,做起来会很困难,如果能贷到一笔款子就好了。
小青说,这个疗养的项目具体就交给你做。我当你的后勤部长。
我说,后勤部长是要保证人、财、物的。她眉毛一挑,要财没有,要人可以保证。我说,我现在连你都没有得到呢,遑论其他。她嗔道,你敢说没得到我?男人哪!我说,灵与肉,二者不可或缺。
她绽齿一笑,道,这就看你的本事了。你说说打算。我说贷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多搞点相关活动吧。小青也觉得是该搞些养身讲座了,不仅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效益或者说广告效益。如今养身保健等市场整顿得紧,如果老没见活动,人家以为“桐木功”蔫掉了。
小青的口才是好的,说起桐木拳功的源流,娓娓道来,煞是动听;再则,她就是桐木拳功的传人;而且,她对传统养身术,也有诸多研究,还在书籍网络里整理了大量资料。
我劝她就像当下一个知名的保健医生那样,主动演讲,秉承的自然是家传。她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抢先道,我看就你上台,保证不比老齐小金差。
她这一说,令我枰然心动。其实,私心窃意,早就觉得老齐小金的那两下子不咋的,吾可取而代之。
我当即表示愿意一显身手。我觉得发轫之作,先不拿深圳开刀为好,淘金之地,鱼龙混杂,本人既非龙,亦非鱼,于是选定了一省之隔的峰城。
峰城原本有我们桐木拳功的辅导站,所以做起来不太费劲。事先当然还得把准备工作做充分了,比如宣传,比如组织有级别的离退休老干部到会,小青在深圳赶制了一千张桐木拳功之功能卡,起始准备印上我的肖像。我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用一个模糊概念为好,她就是说人头像虚化。于是到某杂志社请了一个美编,把我的照片、小金的照片,老齐的照片以及会员老马的照片一起给他参考,综合取舍利用。
结果令人满意,因为功能卡上的人头是博采众“相”之长而成,亦驴亦马,非驴非马,给持卡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事实上,进人桐木拳功以后,我凡报告必听,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天下文章一大抄。我发现,不仅大多数养生拳路功法抄袭古人(古人故矣,不会提出著作权问题),而且,互相因袭的情况也?很严重。时间一长,我都分不出哪是张三哪是李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