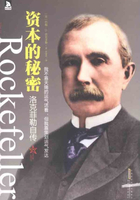少说也值两百块光洋呢,柯议长特意叫我取出来准备义卖的。这么宝贝的东西为什么要卖掉?他也缺钱?她这一问,陈早也觉得是个问题,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心爱物出来义卖呢?按说,一次捐两百块钱,对柯家来说,不会伤筋动骨的。
他捉摸道,搞义卖是参议局组织的,他当然要带个好头。她说,那怎么办?我们出去小半会了,有谁进来过呢?以前丢过东西没有?
她摇头,这里耗子多,还上床呢!却没少过东西。外人来不来你这屋。不来,她说,除了你。没有外人,那就应该是戏班子里的人了。她一愣道,我们戏班子里也从没有少过东西呀!是不是你在路上丢了?或者根本忘了带下山?
陈早阴下脸道,不可能,进你这屋前,我还摸了一下,硬骨似的。
她说,我们这里,谁识得了这块现是个宝物?他盯着她问,想想,这段时间,谁最可能到这屋里来?她想了想道,要说,只有二刀了。
就是他,陈早愤愤道,他对我本来就有气,他不偷去卖,把它扔到江里去,我又怎么找?
她说,二刀老家歙县,就是出砚石的地方,他怎会稀罕一块砚呢。
是了!正因为他老家是产歙砚的地方,他才知道古砚的价值,他才会偷……
剑香不悦道,你怎么看人家恁坏呢?陈早怒道,砚就是在你这被偷的,你还讲我看人坏!剑香坐下道,我看二刀哥不会做小偷。陈早一拍包,甩门而去。剑香追出来叫,你等等……他已经很快消失在浓浓夜色里。
四野静下来,江涛的喧哗越发切近了,声声迫人。剑香双泪如涌,刚进屋,二刀就跟进来了,说,谁欺负了你呢,哭得这样伤心?
剑香不理他,管自哭了一阵,心里舒服了些。二刀就一直立在那里,在微弱的烛光中影绰绰的,若真若幻。
剑香抬起头问,二刀哥,我只问你一句话,刚才我不在的那阵,你进来过没有?
他瓮声瓮气道,没有。那你见谁来了没有?没有。怎么了?她摇头,不复再问。
这一夜,她都没睡实;武大头一夜未归。
淑英再次见到剑香的时候,剑香正迎着江风在堤侧晾晒衣裳。那是挑戏箱的麻绳连接而成的一根长线,穿着衣袖或裤腿晾晒的红绿衣裳在风中劲舞。
剑香踮起脚伸长臂膀在拍打,她的身子弯成一道弧,在灰亮的天宇衬托下,很见韵致。
淑英不由得就呆看了片刻。近前来,她站在阴处,收了太阳伞,侍立在侧的男佣吴金接了。她亲热地叫了一声,剑香!剑香回头,一愣道,太太!你来了,快回屋坐坐。淑英说,刚从江提上过来,头都犯晕。剑香说,太太一年四季住在山上,应该是欢喜山的。淑英撑开伞要拢她。剑香端着木盆快走两步道,太太用,我们是日头里晒惯了的。
淑英说,这里属大湖疫区,有血吸虫,也就是大肚子病,不能赤脚的。
剑香就表示原本并不知道,这下再不敢赤脚了。她老家也有疫区,她看见过大肚子病的痛苦。
淑英一身夏装,装点不多,依然透出迫人的富贵气,进得寒碜的布景包裹的居所,剑香更觉不知如何叫她落座。最后把戏箱收拾干净,垫起一个蒲包请太太坐。淑英问,夜晚热不热?
剑香球磨着她所为何来,答道,不热,靠江边呢。淑英捏着床上的被褥说,该热了,还盖得住被子!说着,已经叫吴金抖开随身带来的一个小包楸,里面是一条线毯。她叫剑香在床上铺开,但见线毯上伏两只猫,一公一母,白猫跃动,黑猫恋随。
淑英说是送她的。
剑香就叫道,我怎敢受用这么精致的毯子!心里却一阵欢喜。淑英淡淡说,好吃好睡好演戏。剑香折起毯子说,谢太太。你爹爹还没消息?
剑香告诉她,安徽来人,说在安庆街上看见他的影子,叫他,他没回头,也不知道是不是看走了眼。跟家里联系,家里没见他回呢。
淑英说,那块端砚,是柯议长的心爱物。刘二刀一直没有承认他偷了,你看,是不是有别的什么线索?
提起端砚,提起刘二刀,剑香的眼圈霎时就红了。那块端砚,据陈秘书说,柯议长已经私下与铁路局长议定,不管拍卖价升到多高,最后都要留给铁路局长,铁路局长有收藏癖好,他出价300大洋。柯议长估计拍卖也升不到此价,乐得做个人情。拍卖因为底价保密,最后收回总是容易的。柯议长之所以愿意拿此物出来拍卖,就是想告诉尹画家及诸同学,值此黎民百姓水深火热,不要吝惜身外之物。
砚台不翼而飞,更加重了它在铁路局长心中的分量,他与警察局长是两连襟。警察局长亲自带员到戏班住地侦寻。最后把怀疑重点落在刘二刀身上。一则刘与武家关系密切,二则搜到刘家几封来信,都是告断炊之急。再加上,陈秘书阴与局长说,刘二刀耽于剑香而不可得,XI外来人都心怀愤恨。
一条绳子把刘二刀缚往警察局。剑香当时在街上,等她赶到警察局时,已经听见里头的喝问与拷打。
剑香赶紧找陈秘书。陈秘书犹豫说,如果他真是偷了呢?你能肯定他不是偷儿。又说,这几天,柯议长情绪不好,连带得我也不安心。剑香说,不管怎么说,打坏了人怎么好!你要不救他,我从此就不理你了!
剑香一认真,陈秘书心就软了,跑去警察局,叫他们手下留情。
性情褊急的刘二刀对警察破口骂道,婊子养的,你们打吧,你们若不打死我,出去以后,我一刀两刀生劈了你们!
他这一骂,自然又要多吃皮肉之苦。陈秘书却因之感觉,可能确实是冤枉他了。
剑香给刘二刀送饭来,他也不理,不吃。
剑香求他,二刀哥,吃点吧。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他躺在不容翻身的一张窄床上,两眼一翻说,你不用为我操空心,你过你的好日子去吧!刘二刀穷死,也不容别人诬为贼!又说,没想到,你也这么看我!剑香无言以对。
第二天,就听说刘二刀跑了。半夜里,他嚷着肚子疼要上厕所,在暗处把看守的警察打昏,把他的枪也卸下翻墙逃逸了。
警察局长气得七窍生烟,大骂不是贼,是土匪,斥令到戏班子住地大搜检。这一搜检,刘二刀自然是搜不到,但未尝没有一些来历不明的金银首饰及其他值钱的物件,警察局长说,这些是什么?统统都是赃物,统统没收!
物主见自己的家财被劫,哪里肯放手,双方争打起来,直到警局鸣枪,这才放手。局长恼怒之下,连人带物,一并拘虏而去。大堤上哭声震天,一时间围观者如堵。
剑香在情急中帮忙,大腿也挨了警察一枪托,幸亏陈秘书过来救驾,不然也被一起带走了。
陈秘书对她说,柯议长见查抄到如许值钱物,也甚感惊讶,认为甚是可疑,因为,此前他来戏班视察,见到的是与灾民相差无几的饥寒交迫的景象。
剑香有口难言,她知道有些姐姐,因了生活,或因了诱惑,暗里给人做小的,得了钱,购置一些金银,为的是携带方便,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拿出来用的。演戏的女子,吃一口青春饭,不趁年轻攒点私房,回去以后,靠什么做生活呢。
陈秘书一再说,想不到你们这里头,也有大富大贵的呀!怕是不敢说偷抢来的,只怕比偷抢更叫人费猜详呢……
剑香实在听不下去了,道,你不要说得难听,她们就是偷抢了,也比那些贪官得来干净!
陈秘书脸色一变,你是骂柯议长?
剑香神情激奋道,我倒未必是指柯议长,像柯议长这样能为百姓着想的官儿天下从来都太少!那些既拿了高饷,身上夏天着缎冬着呢,嘴里成天打着饱嗝,又爱嫖谁嫖谁的高官儿,坐在车里还满像个人样儿的,有好多,只怕你比我心里更透亮些!
剑香一着恼,陈秘书先就软了。况且剑香说,如果不是他带来一块鬼也没见过的石头,哪会惹下一串的麻烦,这下好,把一干人全毁了一一拿走了物,还带走了人!剑香叫陈秘书务必去把人放回来。
陈秘书蹙着眉说,我哪有这么大面子呀,为刘二刀说情,已经在警察局长面前丢了信言了。要说,你去给柯议长说吧。你当我不敢呀!剑香当时就赶往参议局,向柯议长求情。柯议长原本还有些恼火,终于经不住剑香泪水涟涟的诉说,答应去警察局一趟。剑香身子一折就跪下来,议长的大恩大得,我只有来世报答了!如果她们回来了,东西拿不回,我也无颜再在戏班里呆下去了!砚台毕竟是在我屋里丢的呀!他们是受了我的牵连了。
柯议长摇头,一笑,你呀,真是厉害着呢!放人的事还没说,又把还物的条件提上了。
在柯议长的说项下,人物俱返,进警局少不了吃了皮肉之苦。感激剑香的人有;抱怨甚至诅咒剑香的,也有。剑香对陈秘书说,你的砚如果找不回来,我就永远不可能对人家做交代,包括柯议长、太太、二刀,还有戏班里所有的人!陈秘书叹道,真是一个谜呀。
剑香说,我怀疑,你是不是到我这里来之前,就让人掉了包了?你是不是在别人那停留过。说着,脸上就浮出别样的意味来。陈秘书说,瞎,我在别处停留过,你醋了?剑香说,我才不醋你呢,倒是你那太太,那天好好的,跑我这来没话找话,不是醋了才怪!
这一说,陈秘书也疑惑了,是不是她知道我会上你这来,根本就没把砚台放进去,好叫我抱怨你呢?可是那天,我并没有直接上你?这来,而是先到参议局,如果议长当时没有出去陪客人,我就肯定要交砚台出来的呀。
剑香一哼说,结果你毕竟是先上我这来了,是这么说,倒是天意要助她的呀。
陈秘书觉得这事越想越头疼,说,不去想它了。好在柯议长为人宽宏,倒是一句话也没有责备我。
他拴了门,搂着剑香求欢,说,你爸走了好,刘二刀走了也好,从此没有人打搅我们了。
剑香躺在那里,乜邪眼说,我这边倒是没挂碍了,你那边还有一个管你的太太呢。
陈秘书将头埋在她胸前说,不要提她好吗,这时候?柯议长操持的名人字书画及文物义卖活动搞得还算成功,此前,他令陈秘书又取了一些明清的字画,送给当地显贵,获取他们的捧场。头一天,正副市长就都来了,义卖所得近万元钱全部捐给了市府新成立的赈灾局。
赈灾义卖的成功,使柯议长对丢砚之事,从此没再过问一句。这日,剑香早晨起来,发现地上有一张纸条,写着:
集市当铺有一具端砚,就是柯议长的宝物。速带钱去。剑香一惊,赶紧跑街上告诉陈秘书。柯议长激动道,如果真是,花五百块钱也买它回来!陈秘书说,我怕认不准呢。
柯议长说,俞司机还在山上,如果有车,我就跟你去了!你先快去,上面如有苏东坡的《醉落魄》,就错不了。
待得陈秘书带着两个武弁赶到金鑫当铺,哪里还有端砚的影子!老板说,前几天确实有一个人放了一具砚在这当,说好三曰不取,就由当铺处理了。过了一周都没来赎,今上午才有一个瘦高个、戴副眼镜的斯文人买去了。陈秘书急问,多少钱买去的?
老板说,我一个粗人,哪识得价钱,三十块钱拿去的。陈秘书顿足道,三十?只怕三百我也要了!
老板大惊,有这么值钱?这买砚的人你以前认识吗?不认识,老板摇头,在街上也从没见过。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去了多久?
老板朝东向一指道,有一个时辰了。你们到那边守守看吧。陈秘书立即率武弁朝东而去。老板跟着出店,在后面说,今日大亏了一盘!
守到天黑,压根就没见过一个戴眼镜的在这边走过,沮丧回来汇报。柯议长默了一阵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算了。只是辜负了铁路局长的一番念想。
多日的雨水之后,是日炽一日的阳光,凤凰山的万千松杉越发郁郁葱葱。
别墅的墙角终日缭绕着袅袅的水汽。吴金说,树根憋足了水,只有四下里放出来,连墙缝也不放过。
在淑英身上盘桓的陈秘书说,吴金的话很有味道。淑英说,吴金是个老实人,是你想邪了。你若是要有吴金一半的老实,就好了。
陈秘书不满道,你若喜欢老实的,就不会……淑英打断他,你以为你又能调皮到哪里去!不就敢在一两个戏子里头揩油么。
陈秘书摇头,总归是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不是。淑英这就有些满足,嘴角一扬道,你还知道你的斤两。陈秘书肚子里翻腾着,他感觉眼前这个女人就像一只性情不可捉摸的母猫,尽情地玩耍着自己,那自己就是老鼠了?说老鼠又不大像,老鼠与猫是敌对的,自己其实更像她手里的一件宠物,而且是活的。
你又何尝不在玩她呢?吃她的,用她的,跟她睡觉!你还有自己意中的女孩子,但是,说到底,你却是她家养着的。正像那天尹画家的女儿平平说的,你是他家的食客。先秦时期,魏有信陵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都喜欢豢养食客,吕不韦是豪门贵族,家有食客三千。他柯家只有你一个,这样也好,省得有人与你争风吃醋。平平说着笑起来了,笑得如山涧流水般的清脆响亮。
他摸准她其实并不知道他与太太间的暧昧以后,也笑了,说,吴金、李婶,也算他家的食客。
不一样,平平说,在某种意义上,食客还是客人,也就是说与主人有朋友之谊的一面。吴金、李婶怎敢与柯议长和柯太太朋友相称!
陈秘书说,柯议长还是很开明的一个人,他从来只让我们叫欧阳太太,不让叫柯太太,他认为女性的独立自由,不应受婚姻的影响。
平平的眼睛异常尖利起来,说,你以为叫柯太太与叫欧阳太太有好大的区别?柯先生如果过分放纵他太太,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在某个方面,无能!
陈秘书的脸色刹地一白,欧阳太太对柯先生还是很好的,很体贴。
她对你肯定也不错。你不要乱说。
我当然不会乱说。平平又笑了。
那天是在一面向阳的山坡上,平平不时地在纤尘不染的岩石上跳跃着,几次闪失,掉在缝罅中,陈秘书在拉她的那一刻,突然萌生出一个恶意的念头,但是不容他多加思索,她巳经在他的一臂之助下跃然而起。她上身是一件咖啡色衬衫,下身着一条斑纹紧身裤,灿烂阳光下,她像一匹刚刚成熟的小鹿,诱惑而敏捷。即便在矿野,他对她也只能生出一种恶毒的淫想,她的漂亮而锐利,本身就是一道屏障。
这个讨人喜欢的小婊子啊。上路的时刻,他轻轻骂了一句。
晚饭以后,陈秘书陪淑英在林间漫步。
再热的天,凤凰山的夜晚也凉爽无比,氤氲的雾气妖娆地在草缝里、枝柯间徐徐升起,空气中转瞬就弥漫潮润的气息。
他们停留在一面岩石前,一棵老树的树根从岩石的四面八方穿凿而出,似乎听得见岩石的爆裂声,穿石而出的树跟又密步在岩石之上,苍劲得令人不可思议。淑英说,你听得见吗?他猜道,是石头的声音?
不对,她继续朝前走去,是树根的声音,它积聚了很久,愤怒了很久。
他说,死物总没法同活物较量。她笑了一声,你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他们后来就并肩站在一个小水库上,这个水库凤凰山居民的水源。水色映着晚霞,安静而凄美。
你知不知道,她问,剑香的身子有几个月了?陈秘书耸然一惊,你说什么?
她回过头来睨了他一眼,看出他不是装蒜,说,那天在江堤上,我一眼就看出她的身子来了。信不信,起码是三个月了。她难道没有告诉你?
陈秘书默然无语。事后他询问剑香,她果然告诉他,身上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来了。
他当时的感觉就是淑英的厉害,她居然隐忍不动,隔了那么些日子才告诉他。
淑英问,你真打算娶她吗?还是……
隔着一张椭圆的枣木桌面,她离他那么近,又似乎那么远,有一时的朦胧。他觉得眼前这个女人,只有深入她身体的时候,他才能把握住她。所以他在她体内逗留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竭尽全力。他要在她平日的驾驭之中找到反抗与拼搏的罅隙,床榻上是唯一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