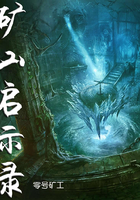景浩上了一天课,聂枫一日没出门,两顿饭做得十分熨帖。吃晚饭的时候,她兴奋地告诉景浩,过两日她就有一架美国产五星牌钢琴运上门。景浩心想有钢琴了,也能使她消除几分寂寞。晚七点她出门的时候,景浩问:“今晚回来吗?”聂枫一愣,看着他,脸上绽出一朵笑来说:“回来,散了场就回来。”
她走后,天平就来了。景浩于是与他同到张通宝老宅的后园口。没待多久,小武就出来,刚两岁的孩子,已经走得很稳。因家庭教师并不认识他俩,所以景浩和开平都露了面。景浩手持一架花花绿绿的飞机小风筝。小武一看就迷住了。家庭教师只笑笑并不过来。
两人用风筝将小武逗乐,渐渐引到木栅口边,那姑娘坐在石凳上看小说,起始还回回头,后来就管自不顾了。
景浩牵着风筝跑。天平说:“追哟。”抱起小武去追。拐到大路上,叫了一辆人力车匆遽走了。
直到家里小武仍对风筝有兴趣。问他喝不喝水的时候,他忽然叫道:“奶妈。”这才感觉到陌生,张嘴哭了。哭乏了就渐渐阖上了眼睛。
11点许,聂枫回来了。景浩开玩笑道:“今晚我有一个小伙伴,只能委屈你打地铺。”
聂枫问是谁,景浩叫她自己看。走到床边,聂楓万没料到是自己的亲骨肉小武,一愣之下,便扑过去。她凄楚地叫一声“宝贝”,泪落如珠,洒落在那张红扑扑的小脸上。景浩心酸了,说:“当心,别把他弄醒。”两个睡下来以后,景浩将“偷”的经过告诉了她。这时他不禁替那个家庭教师犯愁:“今天一晚她还不知怎么过呢,张通宝没准会揍死她。”
“唯一的办法是叫她逃跑。”
“对了,明日给她通个信,就说孩子回不去了,叫她跑。”聂枫说:“小武放在这里也不成,只怕张通宝会寻上门来,必须放到一个他不知道的地点。”
两人把所熟的朋友排了一遍,都觉得不尽合适。景浩忽然说:“放到你环亚公司的朋友家如何,那个地段人少,很幽静的。”
聂枫一愣,问:“你这家伙,跟踪我了?”景浩笑道:“我有千里眼,哪里需要跟踪呢!”景浩不是仔细生活也不易疑心的男人,聂枫想想不由叫道:“一准是天平那小子!”
但她也认为将小武寄放在边涛家比较合适。第二日清晨,她就把小武送过去了。这样她也只有呆在那边了。
天平知道以后,说景浩真傻,这岂不是给聂枫与那人苟合开了方便之门吗!景浩这才觉得是有点傻,一时又没别的办法。
第三日,景浩正在屋里作画的时候,张通宝领着两个警察来了,背后跟着那个家庭教师。一见景浩,那姑娘就失声叫道:“正是他!”
张通宝劈面给了景浩一巴掌,吼道:“还有一个是谁?小武藏到哪里去了?”
景浩愤怒地盯着他不做声。两个警察里外搜遍没找到。景浩被带往警察局。连着两天过堂审讯,景浩周身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只称聂枧把孩子带走了,不知带到哪去了。张通宝把夺妻子的双重仇恨统统发泄出来了,把景浩押在一个单个牢房里。里面臊臭逼人,一天只给二两霉米饭。
三天之后天平才知道他被羁押的消息,托路子进来探望。一见奄奄一息的景浩,大惊失色,赶紧通知一直未返家的聂枫。
聂枫匆匆赶到警察局,张通宝拒不见她,说只有用小武来换景浩。聂枫两难,天平叫道:“还犹豫个屁,再关几天,景浩就没命了!”
聂楓这才把小武送来,眼泪汪汪之中母子分别,待得景浩出来,两人抱头痛哭。
景浩内脏被打坏,调养了好一个时期都无法完全复原,常常闹胸口疼。
受此剧创,聂枫不再坚持不生孩子。1937年2月,她在医院生了一个女儿。取名阿芒,这回是难产,折腾了两天两夜,输了200cc血,聂枫才从死亡的边缘活了回来。
受此痛苦和惊吓,聂枫对阿芒遂生反感,尽管两只乳房胀得难受,她却一次也没给阿芒哺乳。
聂枫这时同家里的关系已经缓和,出院没两天她就回娘家休息去了。她说跟孩子在一起睡不好,已经神经衰弱了。
景浩绘画兼教课已经繁忙,陡然添了一个孩子,那种忙乱更可想而知。聂枫回家以后,叫人送来好几瓶美国奶粉,无奈阿芒一吃奶粉就拉稀。医生说孩子肠胃不好,只有用人乳喂养。
景浩只有去请聂枫回来,聂枫说奶水巳经退回去了。景浩说可以用催奶方子催回来。聂枫说她可不愿再受那份罪,景浩生气了,骂道:“你真是一个自私的女人!”
聂枫也勃然大怒:“我自私还是你自私?你明明看见我身体虚弱得不成样子,还要我再受折磨。那样不把我折磨死也得把我折磨成老太婆!我才二十六七的人,生了阿芒,额头就现出皱纹来了。”说着她拿起一面镜子照照。
“我又不嫌你脸上有敏纹,你怕什么?”
“说得轻巧,你既没当公司经理又没当歌厅老板,你能给我安排一份像样的职业?”聂枫满脸揶揄。
这时聂楓母亲也进来数落景浩:“我女儿原本一个好端端的小家,硬是被你拆散!她现在身体这样虚弱,你还忍心折磨她,你还算个文化人么!”
景浩心中憋气,一时又觉得无话可说。聂枫这时却不客气地对母亲道:“妈,你别来,没你的事!”她母亲只好悻悻退出,一边走一边又在数落女儿合当吃苦,当初放着洋行里的小开不嫁,越选越糟糕。
这时聂枫已经平静下来,叫他去找个干净点的奶娘,若是缺钱她会设法送些过来。
景浩说,不是没找,而是一时找不到。请她先生奶一段时间,一俟找到奶娘就让她回家休息。
聂枫叹了口气说,“早知如此,我又何必生她,找个合适人家送走了倒也自在。”
景浩见她把话说到这一步,情知劝她不转,转身就走。聂枫叫住他,塞了一百元钱在他衣袋里,搂着他的腰温柔道:“别怨我,感情上我很倔,这你早就知道,我从来就不喜欢逆着自己的感情行事。”
景浩有些感动,说:“常来看我,生你的气以后我加倍地想你。”
“会来的。”她回报了一个热烈而深长的吻。去年中心美术馆的那次美术联展,景浩的油画获誉较高,希堂画店出的一本精装画册,收了他六幅油画作品。
蔡先生认为国内擅油画的不多,锐意攻此,必可大进,聂枫这时却认为景浩应该把油画放一放,锐意攻国画。原因是他没有机会出国观摩学习,油画的意境表现总不脱前人窠臼;更主要的,她认为他的气质和文化背景更适合国画。尽管国内高手如林,仍然可以有所超越。
景浩后悔的是,不该把聂枫的观点说给蔡先生听。结果蔡先生又对她多了一层反感。当时他淡淡道:“一个不懂美术八60的女人,信口开河罢了。”
蔡先生给他定的宗旨是:中西兼进,西画为主。景浩暗里实施的是:“中西兼进,国画为主。”
这天蔡先生两口子带了几件小孩衣服来看景浩的小宝贝。见屋里凌乱不堪,景浩一个忙得不亦乐乎。满屋的奶腥尿臊,连个坐处都没有。阿芒早已哭哑了嗓子,却仍在哭着,听来让人心疼。师母从景浩手里抱过孩子,连连地哄她。
“怎么一个家乱成这样!”蔡先生问,“她娘呢?”景浩鼻头一酸:“聂枫身子虚,在娘家休息。”
“休息,她能忍心扔下孩子在娘家休息,病了么?”
“有些神经衰弱。”
聂枫来过两次,抱起小孩来以后就觉得放不下手。所以她跟景浩说,还是空一段时间不来。她说她不能再陷入母女的情感中去,她害怕以后又会发生类似小武那样的事情。再说她如果想依然保持年轻,就不能沉湎于母亲的角色。她说女人不像男人经老,女人若想延长青春,就必须有所放弃,学会自我爱护。
对聂枫的这些说法和做法,景浩是不支持却能理解。但是天平却认为她真是自私透顶。景浩心里明白,她的观点,蔡先生更不能接受,蔡师母温良恭俭,是与聂枫完全不同的女性。但是景浩依然挚爱聂枫,一如既往。
蔡先生有些轻蔑道:“有点神经衰弱就连孩子也不管了,不负责任。”
当听景浩说奶娘一时不好找时,蔡先生略一犹豫道:“蔡青正在奶孩子,叫她过来相帮一下好了。”
景浩心下喜欢,却有些难为情:“这怎么好。”蔡先生说,明日就叫女儿过来。
第二天,蔡先生差了一辆人力车亲自把蔡青送来就走了。为减轻景浩的负累,身为系主任的蔡先生还给景浩减了课时。薪水却照付。
蔡青的孩子炎炎已经半岁,能吃一些辅食了,但蔡青奶水仍足。
阿芒第一次吸着她的乳头时,十分贪婪,两只晶亮的小眼睛一眨也不眨,那情状令景浩激动又心酸,他后来据此绘了一幅油画,标题叫做《追本溯源》,再后来听从聂枫的建议,改做《纯》。
蔡青开始一天来一次,哺完乳休息一会就回家,再后来就呆在这里大半天。她的丈夫好打牌又嗜酒,输了牌或醉了酒就打她。她想同他离婚。蔡先生每次找他谈,他都谦恭知礼,一副知错即改的姿态。但父亲走后,他就凶相毕露,专朝女人的隐私处下手。蔡青痛不欲生,以后就索性再不同父亲讲了。而蔡先生却误以为女儿与女婿已经日渐修好。
这日,景浩在桌边作一幅工笔花鸟。蔡青将两个孩子哄睡以后,从书柜拿起一本《西厢记》随意翻看。一边说:“结婚以前,我是多么喜欢看书,学校里的文艺书籍我大都借阅过。那时候神游梦驰,有几多青春妙想,结婚以后一切都化作泡影……”
由她的哀怨,景浩想到聂枫也有过类似的感叹,但聂枫比她更执拗更强劲一些。聂枫似乎把握了自己又似乎放纵了自己。以她少有的敏慧,若是锐意于一门专业,那会有怎样的成就啊!可是她不,她性情潇洒、好玩而不知节制,这使景浩为她抱憾。然而设若她不是这种性情了,他又会如此痴爱她吗?
蔡青仍然站在他身边诉说:“婚姻好像是专为男人设置的,女人一旦成婚,就会失去属于自己的东西。”
景浩不赞同她的看法,认为这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聂枫,婚前婚后,她的性情行为改变不大。
蔡青幽怨地说,那是她找了个好丈夫的缘故,说着,她撩起衫子,露出两乳说:“你仔细看看,都是他掐咬的。”
景浩看时,果见双乳上都隐约着青斑和疤痕,还有烟头烙过的印迹。
她流着泪说:“最怕他喝醉了酒以后强迫干那事,横掐竖拧,还不许你叫疼,好多次我都想到了死。”
她哭诉着身子就眼见得软了下来,景浩搀她坐到床边。她恳求道:“抱一抱我,别离开我。”
景浩听从了她,双手搂着她的肩,她粹然倒在他怀里,在他胸前热烈地吻着,絮絮地说:“浩,你可知道我是多么地爱你!可是那时的我,自尊又自傲,把感情掩盖得严严实实,就期望你能主动。当我听到你跟聂枫跑了的消息,我在床上哭了一夜,我知道我从此永远失去了你……失去了的难再回来,可是我今天要你,现在你要听我一次,你不能拒绝我。”
景浩被她的热烈大胆惊呆了,同时又为她的痴情所感动。景浩没有勇气拒绝她的真挚的请求。
但在同时,景浩却又强烈地思恋聂枫,他有一种羞愧和后悔的感觉。
蔡青抱着孩子出门的时候,对他说:“原谅我。久久地才掉转头出门。”
景浩担心自己堕入蔡青情感的漩涡,他既不想伤害她又不想与之缠绵,正没个对策,晚饭后天平来了。他将心里的想法告诉天平,天平嘿嘿一笑:“我不是有意拆了你这个家,我看你倒不如跟蔡青结婚来得幸福。你那么痴恋聂枫,她却未必那么爱你。你这个有她一份,却又跟没她差不多!你看这个家乱成了什么样子。”景浩说,她若在家,收拾起来那是很麻利的。天平不同意,扳着指头说,一年三百六十日,她安生呆在家里又有几日呢。
景浩说起蔡青的遭遇,感叹道:“聂枫当然也有点过分,但是若像蔡青那样,被一个家窒息了,那我倒情愿她这样呢。”
天平望着好朋友瘦削的双颊说:“你也别太顾别人了,顾顾你自己吧!”
“人无完人。”景浩仍想修正天平对聂枫的印象。“虽然张倩和蔡青都爱我,但我以为,红粉知己,还是聂枫。”
天平不以为然:“还不是你认为她的美术直感好,于你有用?”景浩摇头:“不仅仅是这个,她的敏锐和智慧,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一份默契,使你觉得须臾不可离开。”
天平冷冷道:“可是这一次她离开你多久了,你可知道她近一段时间又在玩些什么?”
景浩茫然道:“我最近也很忙,所以无法顾及她。”天平忍不住叫起来:“不是她需要人顾及而是你需要人顾及,你看你瘦成什么样子!她在外面,有的是人陪她玩!”
原来那段时间,因聂枫的原因,边涛和他的妻子不和,聂枫就主动疏远了边涛。边涛不忘旧情,在聂枫怀孕辞了歌厅那份职业以后,仍不时寄情书给她,也不时经济上给她一些接济。聂枫知道他手头不薄,纳之坦然。
生了孩子以后,边涛企望与她重温旧梦,聂枫却表示:事过境迁,不再有那份兴致。边涛就断然不再寄钱给她。
有钱的时候不觉得,没钱的时候就难受。聂枫个人的日常开销不低,丈夫独自在家作画带孩子,她每月都要送一笔钱过去。此时没了进项,她在家里就再也呆不安稳了,通过朋友介绍,她结识了西华商场的梁经理,梁经理问她可做过会计出纳一类的事情,她说做过,其实心里一点也不摸底。
她到底心巧,看了半日账本,就明白了一个大概,因是熟人介绍,说好月薪100元,算是高的。可是做账不到三天,她就不胜其烦,认为和尚念经也不过如此枯燥。
梁经理问她:“那你以前怎么又耐得住性子?”她说她从来都没做过这么枯燥的事情。梁经理很惊讶,拿过她做的账细看,但见绳头小楷,一丝不苟,进账出账,笔笔不乱。说:“一点看不出你是个生手!”心里对她就有了几分怜惜。
梁经理问她喜欢做什么事情,她说和玩有关的事情她都喜欢。梁经理笑了,商场有什么和玩有关的事情呢,只有请她别寻一个去处。送她出门的时候,梁经理忽然想起英租界内的跑马场也有他的一个股份,便返身写了一封短信,叫她去找跑马场的邹荣棠。跑马场算是一个可以玩的地方。聂讽读中学的时候,曾去玩过。聂枫记得,跑马场对中国人的禁忌很多,酒吧间和舞厅禁止中国人人内,看赛马只能坐偏台,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军政官员进场打高尔夫球,洋人也漠然视之。解气的是那年春季,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带领几个随从偶临马场,英国人出门迎接,日本领事闻讯赶来,对他也十分恭敬。张学良却紧绷着面孔,当日本领事伸出手来时,他视若不见,不予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