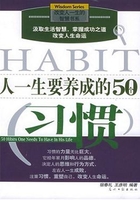这样,我们这些反“侵略”的文化“白血球”,便陷入了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之中。因为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乃是无间歇地寻求新的创造,以刺激文学的消费市场。这对于一切常态发展的文学艺术几乎是无一例外的规律。艺术家的弃旧图新,根本受制于欣赏者的喜新厌旧。既然如此,则一个开放社会的文艺一旦恢复了常态的运行,不改变思维惯性的“文化卫士”们的命运,便只能是永远如此这般的尴尬处境:开始是断然拒绝,后来又无可奈何地悄悄接受。
在文学的其他领域,情况也大体相似。开始拒绝王蒙不合常规(这个常规即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模式)的变革,在一阵纷扰之后,终于不再激动,默然认可了《春之声》、《海的梦》一类怪异的合理性。想想张洁《有一个青年》、《谁生活得更美好》一类作品赢得了多少喝彩声,再想想她的《拾麦穗》、《爱,是不能忘记的》换来了多少怀疑的目光和责难,便知道这乃是一个普遍的病症,而不是一个医学上的“特例”。
不独文学如此,在艺术的其他门类,这种尴尬的拒绝主义也是随处可见的。邵大箴一篇文章中有一段相当精彩的描述:
因为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偏于保守,在理论观念与理性信仰上多持绝对主义价值标准,对于相对的、多元的价值标准往往采取排斥的态度。在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点上,缺少积极的文化参与意识。在与外来文化碰撞的情况下,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容易产生盲目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卑感和优越感,其表现,就是以为自己民族的一切创造都优于其他民族的创造……对于那些“看不惯”、与本民族传统文化观念相异的东西,往往不加分析地予以排斥。(邵大箴:《当前美术界争论之我见》,载《文艺争鸣》,1987(6)。)论文作者列举了如同我们在前面论及的那种美术界的尴尬:齐白石崭露头角,由于他大胆从民间艺术中撷取了艺术观念和新鲜、活泼的表现手法,为此引来了维护传统方式的画界的惊呼,这些人认定齐白石背离了传统。接着轮到徐悲鸿,他从西方绘画造型中引进了写实的手段而与中国水墨画融汇,达到形神高度统一的效果。一些绘画界的保守派视之为违逆。李可染的绘画革新被谥之为“野怪乱墨”。在一些人的眼光中,这位艺术大师属于“传统功力不深”的画家之列。至于黄永玉、吴冠中的画,在一些传统卫道士的眼中,本来就很难得到认可,更不用论及立志于国画改革的不满现状的那些青年了。在音乐界,情况也是一样,对于那些“异端”性质的创新,一味地进行排斥和谴责,而那些不“离谱”的模式以及相当平庸的民间唱法,不论是如何“照虎画猫”,却毫无例外地得到嘉许。
文化偏见导致文化的无批判的兼收并蓄,以及无分析的粗暴拒绝。这就是:只要是遗产和传统,则可以不论其为糟粕或精华;只要是外来影响,则可以不问是否真有价值。这种无分析给中国文化的现代更新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是文化性格悲剧性导致的一个消极结果。
(三)对固有文化的奴性依附
文化的排他性最基本的思想根基,即保护民族文化的不致中断与失落。谈论这一命题时,一般都具有极大的神圣感,仿佛天将沦亡我华夏,而独有我辈在欧风美雨的袭击中抱有清醒坚定之态度。这个使命感的背后,是极浓厚的弱小民族的自卑心理。大而言之,是对华夏文化的维护;小而言之,则是对于自身参与其中落伍文学的自警,总的说是一种变态的敏感反应。
构成这一文化变态的另一因素,则是一种特殊意识的极端影响导致的心理倾斜。我们不仅为文学划定各色的阶级属性,而且也把服务于那些较少文化的人群当做文学唯一正确的方向性的体现。我们把文学的重心放在文盲或半文盲的欣赏者那里,以其形式和内容那些欣赏者是否乐于接受来宣布文学的成败,这成为一种惯例。文学的普及性事实上成了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准。
与此相关的,是另一种方式的排斥。常谓的“脱离实际”,指的是另一种或另几种形态的文学不适于特殊的中国社会(如战争时期,革命高涨时期,对文化进行“革命”的时期,等等,都会宣布某种艺术为不适宜的),以及特殊的中国接受者。许多的文化珍品和艺术奇葩都在这样的名义下遭到拒绝。常谓的“为艺术而艺术”,一般指的是艺术与宣传效用的背离。在褊狭的艺术观念那里,艺术的价值即宣传的价值,与宣传相脱离的艺术几乎就是精神的鸦片。无益即有害,它们的准绳是宣传的效用。
在这一名目中受到抑制的艺术品种之繁、数目之多是惊人的,而它造成的艺术生态失衡以及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估量。
许多迎合某一特殊群体欣赏趣味的艺术品,很难判断其必定为高尚的或崇高的,甚至很难判断其必定为无害的。民间流传的跑旱船或踩高跷一类艺术节目,由同性出演的打情骂俏情节,其间有不少恶俗成分,却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庸俗在这里得到不庸俗的宽待。一成不变且趣味不高的《猪八戒背媳妇》的历久不衰,若肯定唯有它方能体现出正确的阶级立场或艺术方向,这只能构成一种反讽。对于这些,人们不仅毫无所察,且津津有味地提倡,这同样是偏见构成了谬误。
传统文化确是民族智慧和世代创造的宝库,但同时也可能是思想和艺术糟粕的“宝库”。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成分,只有“五四”初期受到了一番表面的冲击,而后烟消云散,大抵以悄然不语的方式慢慢地又“浸润”了回来。《三国演义》中有多少封建思想体系的产物?《杨家将》中有多少封建道德的说教人们只忙于为它们的宣传开绿灯而无暇细察。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潮中,我们却无保留地默许了上述“封建毒菌”的蔓延。1987年6月,仅以北京几个电视节目而言,其中《乾隆下江南》、《红楼梦》、《赵匡胤演义》的连续播出,都是引人注目的现象。
民间的初级文艺形态中存在瑰宝,亟待有心人去挖掘。它不是如同过去那样赋予政治意义之后再加以偶像化。正确的态度是从遗产整理出发的认真开掘,不是照搬挪用,而是得其神髓,予以现代更新的再创造。王平的红土陶雕《雨》、《山里的人》,灰土陶雕《牛背上的孩子》,木雕《父子》,均得益于她所生活的贵州红土高原以及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民间艺术的滋润当然,她的灵感也得到非洲艺术、印第安艺术的启发)。但她却有效地驾驭并改造了这些原生态的艺术品质而使之完全的个人化。王平的艺术不是民间艺术,她也不是民间艺术的奴隶,而是独立的艺术家。更为重要的是她把她所吸收借鉴的一切现代化了。王平的艺术是现代艺术,而不是古代艺术或民间艺术。我们从她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艺术家作为现代女性所拥有的那种自由、无拘无束的心理状态和活泼的充满了生命冲动的激情。
王平的作品唤醒了我们沉睡的本原生命意识,体现了现代人对于生命复归的愿望。现代意识在这里顽强地反抗着现代“文明”。我们从这些艺术的探求中得到对于现实生活状态的反抗的满足。
对于民间初始文化形态的奴性膜拜,是一种消极的文化品格。这种品格再加上道德化的考虑,加重了它的庸俗倾向。一种对于外域文化的不加分析的美化和臣服,是一种奴性的表现;而由于非艺术的考虑而对固有文化(包括民间文化艺术)的无批判的接受与美化,同样是一种奴性的表现。媚外和媚俗同样构成了中国文化性格的劣质。而从历史发展的事实看,对传统文化形态的无批判意识,以及对民间艺术的局限性的无分析倾向则是主要的。
对于这种文艺迎合趣味不高的欣赏倾向的批评,我们通常听到的是关于流行音乐和抽象画方面的内容。中国的怪现象在于,一种低级趣味若是与“民族形式”保持了关联,那种低级趣味便受到了纵容和庇护。1986年春节,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了《济公传》主题歌。那位肮脏褴褛而且疯癫的酒肉和尚且歌且舞,唱的是这样的“民间小调”:
鞋儿破,帽儿破
身上的袈裟破
你笑我,他笑我
一把扇儿破
南无阿弥陀佛
…………
走啊走,乐啊乐
哪里有不平哪有我
天南地北到处走
佛祖在我心头坐
…………
笑我疯,笑我癫
酒肉穿肠过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小调引起全国轰动。在幼儿园小班,一个个小“济公”摇头晃脑,齐声高唱“鞋儿破”;在军营,一列列整齐动作的士兵用高亢调子把“酒肉穿肠过”当做了一首军歌。1987年春节,西南某着名的省城举行上海歌星的荟萃演唱,最后一个节目是曾经演过《海港》中马洪亮的着名演员登场。他唱了《大吊车》、《夫妻双双把家还》,又唱《济公传》主题歌。他且歌且舞,引起了全场的兴味。据亲历者回忆,台下至少有一半听众随着演员的节奏击掌齐声应和,群情激动,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情并没有结束于那场令人难忘的春节晚会。1987年6月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观众信箱”节目播出一封来信。来信对鹤壁市用高音喇叭在全市“报时”提出批评,而播出的内容是早上播送《济公传》主题歌,晚上播《霍元甲》主题歌。这种泛滥的推广已经引起群众的极大反感。更为惊人的消息来自1987年月26日的新闻报道。那晚在沈阳举行的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东亚区第二阶段第二场比赛现场直播中国队以12∶0胜尼泊尔队。从电视屏幕可以看到主方啦啦队的有力助威,而啦啦队唱的竟是济公和尚的咒语,全场至少数千人起而应和。
以上所举,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能不引人深思。济公在今日中国的复活,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诱因。尽管不乏合理的因素,但包括这种因素的作用在内,这一切都是畸形的和变态的。
而最大的变态则在于,我们的几乎所有的指导者和批评家都在这种变态面前无动于衷而扮演了一场默许的哑剧。这如果也是一种“喜闻乐见”,那么,这里所体现的“群众性”不正好表现了一种极为可悲的文化性格吗?鲁迅说:“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鲁迅全集》,第4卷,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鲁迅为何这般悲观和愤激?那正是鲁迅穿透中国腑脏的洞察力。
(四)破坏被解释为建设
中国文化性格由于特定社会条件的影响,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政策的长期规约,以及伴随社会改造过程而来的一场又一场学术的和文艺的批判运动。这些批判运动的粗暴和摧毁性的后果,已为社会所共知;但它对于文化性格的消极影响则没有受到注意。一方面我们对于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体系并没有认真地整理和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又标榜和高扬批判精神。这种批判实际上指向了新文学革命的成果,以及与借鉴西方文化有关联的领域--我们笼统地称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文学、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文化和文学。
极为丰富的新文学传统实际上只剩下一个鲁迅受到圣人般的供奉。极为丰富的世界文学被扫荡得干干净净。无数次的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和派生而出的文学批判运动,针对的几乎都是中国社会最有文化和才智的精英之士。这些运动的集大成就是“文化大革命”,口号是“横扫一切”、“打倒一切”。它把一切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统统视为应当“横扫”和“打倒”的“封、资、修”。
长期的约定俗成,培养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化品格。人们用来衡量立场是否坚定、方向是否正确的,不是他对于实践和理论建树的创造性,而恰恰是他的非建设性。即他是否能在别人的创造中找到可以攻击并施以破坏的可能性。而且,一旦发现了这种可能性,他是否能够坚定地以非正常的方式进行有效的实现,并以能置该人、该作品于死地的“批判”方式证明批判者的心迹。当然这类大批判有的是自愿的,有的则是不由自主的。
所谓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或“先破后立”的学术指导方针,都旨在养成这种文化性格。破是破坏,立是建设,破坏一切是前提和先决。“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在文学、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在创造和提倡破坏的气氛,并以此作价值的衡量。舆论的倡导和实际的体会,使整个氛围受到污染和毒害。人人竟以破坏为能事--而从事这种破坏均能享有与此种实践相反的美名。这样,从事这一恶行时,从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借助所谓大批判以保护自己者有之,以图仕途进展者有之,卖身投靠者亦有之。
这种配合“运动”造成的“大批判”,后来发展为一种非运动时期也无时不在进行的常态。正常的建设性文艺批评变成了非正常的破坏性文艺批评。尤为可悲的是人们往往视这种破坏为建设。这就造成了一般的和普遍的受害。人人身处其中而不以为异常。久之,就自然地养成了面对一切文学、艺术现象的“条件反射”--用一种至少是不信任、不尊重创造的挑剔的、恶意的甚而是敌对的眼光,对文学艺术劳动成果进行破坏。它不仅直接破坏了一种人们应有的对于艺术创造的心境,使艺术创造的美好情绪和氛围受到摧残,而且也直接地摧残了一个社会的良好风气。创造者和面对这种创造的人都紧张恐惧,而且彼此怀有敌意。
这种变态的气氛直接导致破坏性文化性格的滋长和蔓延。
因为创造必遭厄运,而“大批判”的破坏则直接可以占据“精神优胜”和取得实际好处。于是人人思为大批判的先锋和勇士,而人人不思在艺术上进行新奇的独创性劳动。它不仅是一场灾难性的文化毁灭,而且造成文艺生态的恶性循环。几代人的文化建设性格都受到了最严重的扭曲。这一严重后果一直延续至今,它并不随社会的转变而有明显的转变。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他们依然以破坏的目光和方式面对他们所不能适应的和不能同意的创造性劳动。他们的潜在心理状态依然是大批判的,包括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
(五)不求创造的趋向
中国人消极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诸种因素的促使。这些现象造成了一个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在这个基本上以个体方式进行的最具个性特征的精神生产领域,却弥漫着一种强大的基本是群体的而非个体的气氛。本来是非常自由的毫无拘束的,而且是以个人才能和灵感的充分发挥,从而形成不断求新求异的独创性劳动,变成了最循规蹈矩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小心翼翼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