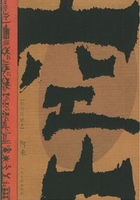当然,因地制宜的思想却非自李渔始,而是我国数千年造园艺术实践所逐渐形成的一条美学原则,历代着名的造园家都是按照这条原则进行园林艺术创造的。例如,唐代宋之问的“蓝田别墅”,王维的“辋川别业”,都是因自然地形加以人工营建而成。白居易在庐山结草堂,更是明显的例证。他在《草堂记》中说:“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砌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伫帏,率称是焉。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问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又南抵石涧,夹涧有古松、老杉,大仅十人围,高不知几百尺。修柯戛云,低枝拂潭,如幢竖,如盖张,如龙蛇走。松下多灌丛,萝茑叶蔓,骈织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风气如八九月时。下铺白石,为出入道。堂北五步,据层崖积石,嵌空垤堄,杂木异草,盖覆其上。绿阴蒙蒙,朱实离离,不识其名,四时一色。又有飞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见,可以销永日。堂东有瀑布,水悬三尺,泻阶隅,落石渠,昏晓如练色,夜中如环佩琴筑声。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线悬,自檐注砌,累累如贯珠,霏微如雨露,滴沥飘洒,随风远去。”通过以上这些描写,我们可以看到,或者清晰地想象出,当年的白居易在庐山是如何善于因地制宜,利用天然条件,巧施人工而结成草堂的。明代杰出的造园家和造园理论家计成,也为我们提供了因地制宜构造园林的范例。他在《园冶》自序中说,晋陵吴又予曾得元朝温相旧园,请他为之造新园,并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斯十亩为宅,馀五亩,可效司马温公‘独乐’制。”计成察看旧园地形:其基形最高,而穷其源最深,乔木参天,虬枝拂地。于是提出这样一个因地制宜的造园方案:“此制不第宜掇石而高,且宜搜土而下,合乔木参差山腰,蟠根嵌石,宛若画意;依水而上,构亭台错落池面,篆壑飞廓,想出意外。”这座园林建成后,吴又予高兴地说:“从进而出,计步仅四里,自得谓江南之胜,惟吾独收矣。”计成的朋友郑元勋赞扬说:“所谓地与人具有异宜,善于用因,莫无否(计成字)若也。”计成自己也在《园冶》中对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了精辟的理论阐发:“因者,随基势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这个思想当然对李渔产生深刻影响。李渔正是在继承和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阐发因地制宜这一美学原则的。
因地制宜的思想在李渔整个园林美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它几乎有形无形地贯穿和渗透在《闲情偶寄》论述园林艺术的所有理论文字中。譬如,在谈到房舍的“向背”时,李渔说:“屋以南面为正向,然不可必得,则面北者宜虚其后以受南薰。面东者宜虚右,面西者虚左,亦犹是也。如东西南北皆无馀地,则开窗借天以补之。”房舍的向背不仅关系于实用,也关系到审美效果。如果园林中的某座建筑是阴冷、昏暗的,不但令人不适,而且也很难产生美感。但是,面南也并非每座园林建筑所必得,理应面南而客观条件却不允许的事是常有的,这就需要因地制宜,想其他方法加以补救。假若园林设计者和施工者不按因地制宜的原则办事,明知不宜如是而强欲如是,则病其拘而又损其美。
因地制宜的原则当然应作广义的理解。它不仅包括因山制宜(有的园林以山石胜)、因水制宜(有的园林以水胜),而且包括因时制宜,还包括因材施用。关于因时制宜,李渔在谈到园林花木的栽培、观赏时,论述最详。因为各种花木都是有时间性的,必须因时因地栽种,也因时因地观赏。李渔说:“予有所命,各司一时,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秋海棠为命,冬以腊梅为命。无此四花,是无命也。一季缺予一花,是夺予一季之命也。”关于因材施用,李渔曾以许多例子加以说明。例一,利用枯树作牖:“己酉之夏,骤涨滔天,久而不涸,斋头淹死榴橙各一株。伐而为薪,因其坚也,刀斧难入。卧于阶除者累日。予见其枝柯盘曲,有似古梅,而老干又具盘错之势,似可取而为器者,因筹所以用之。是时栖云谷中,幽而不明,正思辟牖。乃翻然曰,道在是也。遂语工师,取老干之近直者,顺其本来,不加斧凿,为窗之上下两旁,是窗之外廓具矣。再取枝柯之一面盘曲、一面稍平者,分作梅树两株,一从上生而倒垂,一从下生而仰接。其稍平之一面,则略施斧斤去其皮节而向外,以便糊纸。其盘曲之一面,则匪特尽全其天,不稍戕斫,并疏枝细梗而留之。既成之后,剪彩作花,分红梅绿萼二种,缀于疏枝细梗之上,俨然活梅之初着花者。”例二,老僧利用零星碎石垒墙:“予见一老僧建寺,就石工斧凿之馀,收取零星碎石,几及千担,垒成一壁,高广皆过十仞。嶙峋崭绝,光怪陆离,大有峭壁悬崖之致。此僧诚韵人也。迄今三十馀年,此壁犹时时入梦,其系人思念可知。”例三,用竹作联:“截竹一筒,剖而为二,外去其青,内铲其节。磨之极光,务使如镜。然后书以联句,令名手镌之。掺以石青或石绿,即墨字亦可。以云乎雅,则未有雅于此者,以云乎俭,亦未有俭于此者。不宁惟是,从来柱上加联,非板不可;柱圆板方,柱窄板阔,彼此抵牾,势难贴服。何如以圆合圆,纤毫不谬,有天机凑拍之妙乎。此联不用铜勾挂柱,用则多此一物,是为赘疣。止用铜钉上下二枚,穿眼实钉,勿使移动。其穿眼处,反择有字处穿之。钉钉之后,仍用掺字之色,补于钉上,混然一色,不见钉形尤妙。”此外,如我们在《引言》中所引李渔以“瓮之碎裂者”为牖,以“柴之入画者”为扉,也是善于因材施用的例子。在李渔看来,“收牛溲马渤入药笼,用之得宜,其价值反在参苓之上”。
这里的关键在于“用之得宜”四字,只有“得宜”,才能创造出园林的美来。这也就是所谓:用之不当,变雅为俗,使金成铁;用之得宜,变俗为雅,点铁成金。
因地制宜的原则,其精义在于阐明了园林美的创造中自然与人工的辩证关系,同时也深刻反映了园林美创造中的一条根本规律。虽然三百年前的李渔对园林美创造中自然与人工的辩证关系和美学规律,不会有今天人们这样明确、深刻的认识和清楚、圆满的理论表述;但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或领悟到其中的一些根本道理。
大家知道,美从来就不是纯粹自然的现象,而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在人类产生之前,那洪荒世界固然无美可言;即使人类诞生之后,那山川湖海、日月星辰、花木鸟兽,假如完全同人类没有任何关系,同样也谈不上美。火星上的山石土地,至今并没有成为人类的审美对象;巴西的原始森林,在人迹未至之前,也很难说有什么审美意义。今天人们所欣赏的泰山的雄伟、昆仑的崇高、桂林的佳丽、西湖的秀美,实际上是对这些自然物进行人化的结果。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美(广义地说即审美对象)是自然与人力相搏斗、相融合、相占有、相统一的产物;自然美是如此,社会美是如此,技术美是如此,艺术美更是如此。
园林美是艺术美之一种。园林美的创造,既不能没有自然,更不能缺少人力。因地制宜的原则正是反映了园林美的创造中自然与人力相克相生、互渗互动从而合二而一的辩证关系。当然。自然与人力,主动权应该在人力这一边,即使遇到不可抗拒之自然力,人作为“有意识有意志”的“族类”也可作随机应变的对待和处理。“因地制宜”这四个字,也充分表现了人力的主动地位。具体地说,即园林美的创造中人对自然总是既因之又制之,在因之中制之,在制之中因之;同时,人在对自然的因之制之的过程中,也受制于自然,服从于自然,师法于自然。李渔对这几层关系都有相当深入的把握。
首先说因之。李渔认识到,在创造园林美时,为了获得成功,人必须顺自然之性而不戕自然之体,也就是说必须顺应和合乎自然的规律,而不是戕害和违反自然的规律。例如,在谈到窗棂的制作时,他提倡“宜自然,不宜雕斫”,要“顺其性”而不“戕其体”。他说:“事事以雕镂为戒,则人工渐去而天巧自呈矣。”这正是对“因”字的最好注释。“因”就是顺应、符合,不“顺其性”而“戕其体”就没有美。当然,制作窗棂时的“顺其性”而不“戕其体”的原则,首先是为了“坚”,即结实耐用。因为“顺其性者必坚,戕其体者易坏。木之为器,凡合笋使就者,皆顺其性以为之者也;雕刻使成者,皆戕其体而为之者也”。但是,“顺其性”而不“戕其体”,不只是为了坚实耐用,同时也是为了美观耐看,即为了收到“人工渐去而天巧自呈”的审美效果。因此,“顺其性”而不“戕其体”不只是实用的原则,同时也是审美的原则。这两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现在人们常说,美的必须是合规律的、真的。所谓合规律,所谓真,也就是李渔在这里所说的“顺其性”而不“戕其体”。不合规律性的东西,不“顺其性”而“戕其体”的东西,不真的东西,从根本上说不能是美的。中国女人缠足之丑即是例证。“顺其性”即合规律性,是美的必要条件,也是美的创造的一条重要规律。
“顺其性”而不“戕其体”虽然是李渔在谈窗棂制作时提出来的,但李渔并没有把它局限于窗棂制作,而是把它作为一条普遍原则。事实上,李渔是把这条原则贯穿于园林美创作的各个方面的。例如,园林总体的布局、设计,房舍的高下、向背,花木的栽种、培育,堂联斋匾的制作、书写,以至于挖池、筑山等等,莫不“顺其性”,注意符合自然的规律。
其次说制之。李渔认识到,顺自然之性并不是作自然的奴隶,而是顺其性而制之,充分发挥园林创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前面我们引述的李渔谈房舍“高下”的那段话中,就突出表现了这一思想。虽然造园者不应故意地勉强地制造“高下之势”,但是却可以在“顺其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体创造性。在那段话中,李渔认为“因地制宜”作为普遍原则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具体方法却可以有很多,甚至提出“总无一定之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非可以遥授方略者矣”。这就是说,只要符合因地制宜的原则,造园者的创造性几乎可以无穷尽地施展,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达到因之而又制之的目的。李渔举例性地提出三种方法:一是高者造屋卑者建楼,二是卑处掇山高处挖池,三是高者愈其高而卑者愈其卑。前两种方法是为了造成园林“高下之势”的相对徐缓的调和效果;后一种方法则是为了造成急剧变幻的对比效果。这是两种不同的造园风格,各呈其妙。这举例性的说明,意在告诉人们,造园者的创造馀地是非常广阔的,不同的造园者可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能否做到既因之而又能制之,就看造园者是否有才能,以及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如何了。我国造园史上那些有才能的造园家无一不是既能因之又能制之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前面提到的白居易在庐山结草堂,自不待说;计成为吴又予建园也不用多讲;现在我们看一看沈复在《浮生六记》中所记用重台叠馆法建造皖城“王氏园”的情况:“其地长于东西,短于南北。盖北紧背城,南则临湖故也。既限于地,颇难位置,而观其结构,作重台叠馆之法。重台者,屋上作月台为庭院,叠石栽花于上,使游人不知脚下有屋。盖上叠石者则下实,上庭院者则下虚,故花木乃得地气而生也。叠馆者,楼上作轩,轩上再作平台,上下盘折,重叠四层,且有小池,水不滴泄,竟莫测其何虚何实。”这真是善于因之而制之的绝好例证。在东西长,南北短,背城临湖的地盘局限之下,造园者顺其性而制之,极尽巧思,创造出层层叠叠、丰满充盈、出奇入胜的园林美景来。善于顺其性而制之,是园林艺术创作的一条普遍原则,李渔之前和之后的造园家们是普遍加以遵循的。不过,李渔于此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并给予相应的理论阐发。而且,整部《闲情偶寄》中所有论述园林的部分,都渗透着这一基本思想,甚至包括椅杌、几案的设计、制作、使用,花的种植,鸟的饲养,古董、器皿的摆设等等。
顺其性而制之,其中包含着一个深刻的美学道理。现在人们不是常说么,美必须合目的性,美的也应该是善的。这是对的。而李渔当年所说的“制”,恰恰就表现着造园者的目的性,就包含着善的因素。譬如,李渔谈到“寒俭之家”“以柴为扉,以瓮作牖,大有黄虞三代之风”,然而他又感到不满足:“怪其纯用自然,不加区画。”就是说,因之有馀而制之不足,没有充分表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目的性。李渔提出要“取瓮之碎裂者联之”,使“有哥窑冰裂之纹”;要“取柴之入画者为之”,“使疏密中窾”,这样即可收到“变俗为雅”之效。这正表现了人的目的性,达到了较高的审美效果。所谓“制之”即合目的性,是美的另一必要条件,也是美的创造的另一重要规律。
再次说因之与制之的关系。李渔从来都是把因之和制之紧密结合在一起加以论述的。譬如,前面我们曾引述李渔谈房舍“背向”的意见,其中谈到,当地形不允许房舍面南时,那么就须首先“顺其性”,接着便想法制之,即面北者虚后,面东者虚右,面西者虚左,东南西北皆无馀地则开天窗。在这里,因之与制之是分不开的。再如,谈到梅窗的制作时,关于取老干作外廓一事,李渔作了如下说明:“外廓者,窗之四面,即上下两旁是也。若以整木为之,则向内者古朴可爱,而向外一面,屈曲不平,以之着墙,势难贴伏。必取整木一段,分中锯开,以有锯路者着墙,天然木斫向内,则天巧人工,俱有所用矣。”事情本身看来极为平常、简单;但是其中却包含着关于审美创造问题的一个深刻道理,即人对自然,必须在因之中制之,在制之中因之。也就是说,在顺应它的天性时又不忘记克服它,在克服它时又顺应它的天性。因之与制之相反相成,相依为命。园林美就在这因之与制之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中诞生。
其实,因之与制之本来就是“因地制宜”这一创造园林美的根本原则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因之是制之的依据,制之是因之的目的。不因之而制之,则无依据,不合规律;不制之而因之,则无目的,失去主体性。美本来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真与善的统一。因之与制之相结合、相统一,也就是园林美的创造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结合、相统一。因之与制之相结合,才是“因地制宜”这一思想的全貌,李渔是掌握了这一全貌的。
此外,“因地制宜”中还包含着在创造园林美的过程中,人对自然的师法和遵从。这个问题下面将具体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