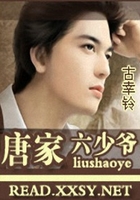连着下了两场雨,天气变得凉爽了,蓝天下的山和树能看出去老远,青龙河水也不是浑乎乎的样子,临近岸边的浅处,河底大大小小的卵石已经清晰可见。
赵国强一边参加着黄小凤组织召开的各种会议,一边带人整治大坝。他还想跟黄小凤认真谈谈,想说这个时节正是要紧的时节,不把大坝修好,过些天收秋了,再过些天天凉了,去外面做活的人也多了,村里再想把人聚起来干点大项目,就不容易了。可是,他找了黄小凤两次,黄小凤都说太忙,没好好搭理他。他又去找支书李广田,李广田这几日特别精神,整天忙着刷标语。赵国强在前街找到他时,他正刷得起劲。赵国强看四下没啥人,掏出烟说:“歇会儿,抽根儿烟吧。”
不料李广田连头也没回,说:“还有好几条子没刷呢,你忙去吧。”
赵国强心头起火:“支书呀,你咋对刷标语有这大兴趣?是不是发愁没运动搞了,闲的慌?”
李广田身上像被啥扎了一下,终于转过身,朝赵国强冷笑了几下,慢条斯理地说:“咋着?你怕来运动?”
赵国强说:“支书呀,中央都讲了,不能再搞运动了,得抓经济呀!好不容易村民们才安下心来奔日子,这么一折腾,不是又弄得人心不定吗!”
李广田说:“都是哪些人的心不定呀?我看大多数人的心都是挺定的,不定的是少数人。是谁?都是发财发红眼了的人。”
赵国强猛地抽口烟:“您这就说得不在行啦,中央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您也在会上传达过这精神。”
李广田说:“问题是,问题是谁知道有人就富成这样!旁人跟他们差一大截子,这,这叫社会主义吗?这么弄下去,穷的穷,富的富,两级分化,你怎么解释?”
赵国强愣了,两眼直勾勾地瞪着李广田。这么多天了,一直跟自己打迷魂阵的支书终于把他的心里话说出来啦!看来,他心里早就憋着这些话,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说出来。现在,他手里的大刷子把他的情绪鼓动起来,他憋不住了,或者,他认为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
赵国强使劲让自己的脑瓜子转几个个,想寻出些词儿来驳李广田。他记得在传达文件时,有过先让一些人富起来的话,同时还有共同富裕的话,至于这两个方面咋结合起来,好像也有那么一段说法,可惜没记住……
赵国强后悔自己过去不注重学习,到了关键时刻就没了过硬的词儿。不过,他并未因此卡壳,他采取另一种方法,也能和李广田论个短长。他又点着一根烟,抽着了说:“支书呀,其实解释这种事,一点也不难。”
李广田一下子被激怒了,猛地扭头问:“不难?你解释解释!”
赵国强说:“很简单嘛,就是因为有人闹了红眼病!”
李广田说:“放屁!谁闹红眼病啦!我看你是私心太重,钱满天、孙二柱都是你的亲戚,你才这么说话。”
赵国强的脸一下子发起烧来,他对这句话有点架不住,原因在于,这是任何一个当干部的人都很忌讳的事,这是对一个人人品的否定。何况,赵国强本来在对待自己亲戚上就格外注意,生怕有一点出格的让村民议论。没想到小心来小心去,旁人没说啥,支书反倒在这捅人心尖子的问题上泼自己一头脏水,实在是叫人无法接受……
赵国强又联想起这些接二连三遇到的窝心事,就像一下子捅破了窗户纸,立马就看清里面是咋个勾当,他说:“支书,你这么说话,可是把良心掖裤裆里啦。我哪点偏向我的亲戚?你一条一条摆出来!”
李广田说:“摆不摆,谁都清楚,你家亲戚,一个个富得流油,这谁还看不清楚!除非是瞎子,就是瞎子,要饭也闻得出这家锅子是熬菜还是炖肉。”
赵国强说:“熬菜炖肉是各家自己挣的。那还有娶不上媳妇的,你就能说娶了媳妇的都不对!”
李广田说:“我不跟你戗戗,你该干啥干啥去。”
赵国强说:“你是村支书,我是村主任,你这么耍白我,我咋干?”
李广田说:“你不愿意干,你可以走嘛,咱村口也没有大门,没人拦着你。”
赵国强血往脑门子上撞,一脚踢倒了装白灰水的桶,大声喊:“你想撵我走!那你当初非让我回来干啥!”
李广田身上脸上溅了不少白灰水,他抹了一把也喊:“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你跟我不是一个心,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
不知不觉的,旁边聚来不少村民。村民们几乎个个都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场面,不知如何是好。村里的支书和村主任干起架来,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看着看着,有爱操心的人就去找两家的人,或许是巧了,李广田的大儿子喜子和高秀红俩人正路过这儿,有人说快去吧你爹跟人干起架来啦。喜子一听虎啦巴唧地说:“还有这人?看我削蒙他。”顺手抄起根木棒,噔噔地跑过去。
高秀红没把这事上心,老公公跟人干架,让他干去呗,跟自己没关系。她瞥了一眼粗莽的喜子,嘴里嗑着瓜子说:“一沾打架就来劲,真是你爹下的好种儿。”
村民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不过,对方可不是善茬……”
高秀红漫不经心地问:“是谁呀?吃了老虎胆,跟支书干架。”
村民说:“是村主任国强。”
高秀红心里像被什么揪了一下,把手里的瓜子往地上一扔,撒腿就跑。她要拦住喜子,那二虎人真敢抡棒子,一棒子说不准就能打个好歹。这倒不是高秀红怕惹出麻烦事,是她不愿意看见赵国强挨这棒子。每次国强来找公公谈工作,高秀红心里总有股莫名的欢喜,她觉得这个个头不大、一肚子都是村里工作的男人怪好的,比喜子能强有一百倍……
赵家那边来帮着干架的竟然是赵德顺老汉。老汉是刚从大块地里回来,才进村,就见金香呼呼喘着跑来,说可不得了啦,你儿子跟人家干架啦,您老快去看看吧。赵德顺还挺明白,说:“他一个当干部的,跟人家干架干啥!不好,我不管。”
金香说:“是跟车支书,要是旁人我才不管呢。”
赵德顺的手有点发颤:“是,是他呀,他们咋能干架呢……我还是不管……”
金香点点头:“也是,您老啦,我去后街找桂芝。”
金香颠颠跑了。
赵德顺却突然明白过劲来,他自言自语:“李广田呀李广田,我一直把你当领导好好敬着……可是,你心里想的啥?我都知道,我坐在垄沟子里全听得清清楚楚。你想整治我儿子,想撵我儿子走,那就是要整治我们老赵家,要坑我这老头子……好不容易我才赶上这么个好世道,趁我这把老骨头还在,为我儿孙把家业打实,你小子坏了心眼子啦,要毁我的大业!今天,我饶不了你!”
赵德顺积问在心里多日的躁火,终于找到了发泄目标。他噔噔噔朝前街的人群处奔去,顺手把谁家门前戳着的一个破镐把拎着,也不知是要打人还是给自己壮胆,拎着走了几步,又当拐杖拄着,看上去,这老头子像是有点精神不大正常。
此时,人群中已经闹开了锅。喜子抡着棒子进来,他也不瞅准了,朝着他爹跟前那人的腚就是一棒子,打得那人嗷地跳起来,扭头骂:“你他妈的瞎啦!我劝架,他削我干鸡巴啥!”
原来是孙万友。他这阵子跟广田处得挺热乎,李广田答应借他几个钱去上访,所以,旁人在一边看热闹,他跳到当中帮助广田擦抹脸上身上的白灰水。这一棒子,可能是削他没啥肉的屁股尖上,把这老头疼得直蹦高。
李广田眼里掉进点白灰水,火辣辣烧得慌,一来气,他扬起手里的刷子就给了赵国强一下子,赵国强拿胳膊一挡,刷子没打着头,刷子上的白灰水却下雨般地甩了他一头,用手一抹,灰头灰脸,日头一晒,头发和脑门子见干,颜色渐渐发白……
赵国强踢水桶的那一瞬间,曾有点后悔--这么着太失身分,往后可咋在村民面前说话。等到见喜子抡起棒子,自己又被甩了这么一头一脸,他也就豁出来啦,心里说啥干部不干部,人家不让我干要撵我走,我还客气啥呀。于是,就不管不顾地往上冲,嘴里说你当支书也没啥了不起,别总想着整咕人……
赵德顺老汉拄着镐把进到人群里,见国强白头灰脸的样子,气得他浑身哆嗦,指着李广田爷俩骂:“你们两个王八犊子,你们要干啥呀!”
李广田看事情闹大了,忙说:“是你儿子发鲁,过来踢这水桶。”
喜子把棒子举起来说:“爹,你一边去,看我削蒙他们爷俩。”
这工夫不少村民就上前拉架了。可喜子人莽力气大,把身边的人一甩,棒子唆地就砸向国强的头。危急时刻,赵德顺老汉把手中镐把往上一挡,嘎吧一声,喜子手中的木棒变成两截,德顺老汉的手被震得发麻。他只觉得心口发热,嗓子眼发痒,一口红东西从嘴里喷出来。
“老爷子吐血啦!”
有人惊喊起来。人群顿时大乱。
赵国强眼睛红了,一指喜于道:“你敢下狠手!”
喜于鲁劲上来:“我连你一块打!”
高秀红扑上前,对着喜子连打带挠。喜子摔不及防,被打蒙了,嘴里喊:“是我,你咋打我呀!”
高秀红喊:“不打你就出人命啦!”
李广田一下子脑袋清醒了,冲喜子喊声快滚一边去,忙分开众人看赵德顺老汉。只见老汉脸色焦黄二日紧闭,吓得李广田腿都软了,忙喊:“快,快送医院!”
赵国强也明白过味儿来,赶忙用胳膊架住爹,等着车来。不料,车还没到,黄小凤到了。她是听人说这边出事了才放下电话赶过来,县委苏海峰副书记问这个点上的情况怎么样,他准备带人来搞调研。黄小凤自然要说得好一点,要不然不就显得自己工作能力太弱了吗。她说苏书记您就放心吧,这儿的工作一切顺利,群众发动起来了,干部思想也很统一……没等她把电话打完,窗外有人喊:“黄队长不得了啦,支书和赵国强在前街干架呢!你快去吧,晚了就出人命啦。”
也怨那位报信的嗓门大,连电话那边的苏书记都听得清清楚楚,苏书记立即问咋回事,支书咋和国强、就是村主任干起来啦,你快去看看。黄小凤尽量使自己保持镇静,说没大事,我去看看,回头再向您汇报。苏书记说不用啦,到时候我可就带人去啦。
黄小凤心中打小鼓似的来到前街,到人群里一瞅,她傻眼了,李广田和赵国强都一脸白灰,喜子脸上好几道子血印,高秀红头发乱糟糟,最可怕的是自己的公公嘴角子还挂着血迹,也不知打成啥样被人架着……
黄小凤脑袋嗡嗡的,她说:“这是干啥呀!干啥呀……”
福贵说:“干啥?好像就为刷这标语,俩人干起来。”
黄小凤朝墙上瞅瞅说:“这也太不应该啦,为这点小事干什么架。”
孙万友揉着屁股说:“这可不是小事,这是大事。不是大事,你来这当队长干啥。”
旁人说是啊,这根子说起来就在你黄队长这儿,你没来时,他俩处得挺好的,你这一来,把他们给搅坏了,村民这阵子也弄五迷啦,要么你就痛痛快快搞运动,该批就批,该斗就斗,要么就有啥事解决啥事,偷东西的警察抓,搞破鞋的往外拉,不交税的搬东西,不孝敬的罚死他……这么办,总比你这蒙里蒙登一个劲学习动员强多了……
可能是这种场合使人有话憋不住,众人七嘴八舌冲着黄小凤说起来。村民就这样,你若是让他一个一个说,他不说,他们要说得热闹,非得你一嘴我一嘴互相抢着说才行。这种说法又有特别的效果,就是听者根本没有还嘴的机会,只能是干受着,而且,过不多久,你就被他们说得头昏脑涨,无法作答。
一辆平板车把赵德顺老汉拉走了,村民们很快也散了,最终,剩下黄小凤和李广田。李广田还在揉眼睛,黄小凤问:“到底你俩为啥?”
李广田说:“不知道。”
黄小凤说:“不知道?那打啥架。”
李广田不回答,抄起刷子,蘸蘸桶里剩下的白灰水,往墙上接着刷字。他狠狠地写了个运动的运字。
黄小凤喊:“错啦,是活动!”
李广田把刷子一摔:“我倒霉就倒在你这活动上。不如搞运动!”
说罢,他头也不回就走了。
在青远县城的街上,赵国强转悠了好几圈了。说转悠,其实就是在两旁有商店饭铺的主街来回走了好几趟。这条主街怪古老的了,据说从明朝时这里就有不少商家和客栈,京剧苏三起解那出戏里,崇公道不是说去南京的没有,有去八沟、喇嘛庙的吗?那个喇嘛庙,就是今天内蒙古的赤峰,而八沟,就是叫人很难相信的只有一条街的青远县城。在人们的想象中,几百年过去了,就是发展得慢,起码也得繁衍出几条像样的街市,再有些看得过去的店铺……
然而,赵国强又感到有一股新的鲜活的内容包围着这条古街--四下里,机器声隆隆不断,烟尘腾空而起。到处都是工地,开路的,挖沟的,盖房的,架桥的,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听旁人说,县里正搞新城建设,即在旧城的旁边,重建一个新县城,不用说,新城的一切都将与旧城不能同日而语。
赵国强之所以在街上转悠,不是闲得没事,而是在医院里憋得难受,心里有话没处说,借口找大哥国民,他出来想把自己的事好好想想。自打和李广田干了那架以后,他俩人都没法儿干工作了。送老爹来县城看病,爹住了院,需要有人照顾,国民说你回去也不好处,干脆在这护些日子。桂芝说对对,就让国强在这,我弄不明白医院的这些牌牌,再者说,爹又下不了地……桂芝是要说老爷子是在床上大小便,自己一个儿媳妇,伺候着不方便。当时在场的还有玉琴和玉玲。玉玲瞥了她嫂子一眼,说爹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害臊的,你不愿意伺候你口去。这时老爷子发话了。他说话声音虽小,可很清楚,表明他脑子没事。他说玉琴玉玲都回家去,玉玲你回钱家去,留下国强和桂芝,过些日子我还出不了院,你们再来换。
赵德顺这时候说话,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就这么着,旁人走了,国强和桂芝留下有一个星期了。这期间,小山开着崭新的桑塔纳,拉着金矿长和孙家权来了。来了拉国强去饭馆喝酒,喝了几盅,金矿长就明挑了,说金矿承包给个人了,一切都他一个人说了算,希望国强去矿上帮他一把。孙家权说自己已经打了停薪留职的报告,准备去矿上,要赵国强跟着一块走。
事情来得很突然。又是喝着酒说的,酒劲烧得人心火辣辣,说起乡里村里那些烂事又让人烦躁,赵国强就拍了桌子,说去就去,省着在村里受窝囊气。金矿长当时掏出两千块钱往国强面前一扔,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十天之内上我那报到,然后,坐上车就走了。临走时,孙家权还一再嘱咐抓紧抓紧再抓紧。
把两千块钱带回医院交给桂芝时,赵国强才有点醒过酒来。桂芝从来没有一下子见过这么多钱,怕病房里的人看着,找了件衣服裹了又裹,塞在床头白色小方桌里。她让国强赶紧回村叫玉玲她们来换班。国强很惊讶,说我回去,爹这的事你一个人能成?桂芝说没事,多年的媳妇跟亲闺女一样,没有伺候不了的。国强忽然难过了,他明白这完全是钱的力量,几天前,桂芝还是另一个态度,逢到给老爷子端屎端尿,她不情愿上前……
可现在,赵国强离开病房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桂芝一个劲催他回村,催得他没法,只好离开医院来到街上。街东头就是汽车站,班车一辆一辆从院里驶出来。可能那儿也搞承包了,班车走在街上,只要见人招手,就立刻停下,所以,坐车变成十分方便的事。赵国强已经有几次要抬起胳膊招手,但都没彻底抬起来,以至有一次抬到半道,竟使一辆班车停下,车门哗啦打开,售票的喊快上呀。赵国强没办法说我没招呼车,售票的脸色大变骂你吃饱撑的举胳膊干啥。赵国强说我挠挠脑袋你管得着吗。说罢,他赶紧躲到一边,生怕再把哪辆车给招引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