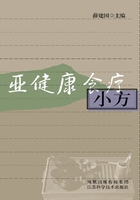在《千山万水》话剧中,李琦演的是一名代表反动势力的小头目,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他扮演的是那个浑身是资产阶级情调的角色罗克文,在《女贼》剧中他演过骗子,在《姑娘跟我走》剧中他演流氓……虽然是来来回回跑龙套,可那时他才真正懂得什么是演员,什么叫“演戏”,什么叫艺术。进门八年了,他开始人道,认真地演好每一个角色。
正当李琦刚刚人道醉心于当好一名演员时,改革开放的浪潮奔涌而来。经济建设的转轨,人们思想的转变,使刚刚繁荣了两年的戏剧舞台再次跌人低谷。无戏可演,就学门手艺吧,当时做家具成风,李琦无师自通,做起了家具。“服务上门,概不收费”,这李琦是拿主业当副业干,这是李琦的服务宗旨。家具越做越好,名气越来越大,门前的队也排得越来越长。李琦来者不拒,从东家做到西家。好烟好酒地供奉着,好菜好饭地伺候着,李琦乐此不疲。久而久之,李琦有了第一个业余职称--李木匠。
大院里的家具做完了,李琦改行当起了裁缝。那时刚刚流行“喇叭裤”,愿意穿的人多,可会做的人少,李琦心灵手巧,带头穿起了全团第一条“喇叭裤”。“李琦,这喇叭裤是从哪里买来的?”“我自己做的。”“能不能帮我做一条?”“没问题。”从此,李琦的宿舍成了裁缝铺,全团男女青年穿的“喇叭裤”几乎全部出自他之手。接着,人们送给他第二个业余职称--李裁缝。“喇叭裤”风靡了一阵过了潮头,李琦适时改行学理发。他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烫头的有了,染发的有了,美容的有了,人们在追求新追求美的同时,有人说,努力从服饰上、发型上、修饰上表现自己。李琦会理发?起初,周围的人不相信,当人们对他确信无疑时,他的“裁缝铺”很快成了“理发店”。于是,人们又送给他第三个业余职称--李师傅。李琦是热,人,结婚的找他当司仪,送葬的请他当“知事”,他来者不拒,有求必应。那两年,主业荒废了,可学了一身手艺,落了一个好人缘。他是全团最小的演员,嘴甜人也可爱,平时颇有些人缘,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他从不用心,老师检查作业的时候他却有心计,求师哥,拜师姐,把他们准备好的用不了的作业拣来,贴上自己的标签交差了事。
演男主角,唱男高音,打架子鼓,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
改革的春潮推动着文艺这盘老磨合着时代的节拍飞速旋转。陕西人艺改革出台的第一个方案,是志同道合者自愿组阁排戏,自负盈亏。李琦人缘好,各剧组争着抢着要,并安排他在话剧《女人的一生》中担任男主角。起初,他喜不自禁,这是自己人人艺以来第一次担任男主角。在舞台上要的不是“人缘”而是“演技”,自己能演好这个角色吗?拿到剧本,整个是一个大颠倒。下基层锻炼,李琦才觉得这副担子太重,演砸了,无疑就结束了自己的艺术生命。结果,李琦一炮打响。那出戏第一次代表陕西人艺走出潼关,走进北京,赢得一致好评。舞台形象成功了,面对记者们的采访和提问,李琦常常处于尴尬的境地,要不难以张口,要不词不达意。他知道自己缺少文化素养,要想当一名合格的演员,需要充实自己。机会来了,1985年,中央戏剧学院招收一个表演专修班。李琦闻讯后,立马赶到北京应试,他本想来这里全方位地包装一下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文化层次、有艺术修养的演员。这一次他没能如愿,带着寻找的失落回到人艺。李琦刚从北京回来,人艺开始精简机构,从领导的谈话中他得知自己被划入“精简”之列。他苦恼,他不解,他愤怒。自从自己懵懵懂懂地走进人艺以来,一直“混”了十多年,实则是到下面接受锻炼。在基层接受锻炼,现在刚刚找到自己的定位,并真心地热爱这份事业时,却被“精简”了。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当即向领导提出三点要求:一、我要在同龄的男演员中打一个擂台;二、离开时给我安排一场告别演出;三、给我开一张介绍信,我要去告状,告那些任人唯亲、排除异己的昏官。满足我这三点要求,我明天就离开。领导的“将军”坚定了李琦的反叛性格:宁肯在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也不离开人艺。按说,那时的李琦,已经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他虽然“触电”较晚,可那时的他已经拍了两部电视剧,尝到了“触电”的甜头,搞影视,有名有利,何苦要在人艺这棵树上吊死?
就在决定李琦人生命运的当口,人艺换了新领导。老领导对李琦的成见一笔勾销,新领导对李琦的认识重新开始。他总是脏活儿累活儿抢着干,老师布置了作业,他总是敷衍了事去应付。新领导上任后抓的第一出戏是《情祭》,从总政话剧团请来一位导演。为了体现公平竞争的原则,导演在分配角色前对所有演员进行了一次摸底测试,每人上台演一段小品。测试后的第三天,公告栏公布测试结果,李琦的名字赫然名列榜首,拿副业当主业干,由他出演第一男主角。导演慧眼识珠,给了李琦一个充分展示才华的机会。在排练过程中,导演发现李琦多才多艺,架子鼓打得棒,歌唱得也不错,在演职员名单上曾三次出现李琦的名字:男主角--李琦,司鼓--李琦,男高音--李琦。这出戏,李琦的确出够了风头。公演后,有人给他开玩笑说:“李琦,你还会干啥?会不会生孩子?”李琦一笑了之。
从一个不被领导重视而被“精简”的对象,一跃成为让人嫉妒得眼红的台柱子,李琦觉得可笑而又可悲。得到重用后的李琦突然感到自己掉进窟窿里。掉进窟窿里的感觉很可怕,不能再去“触电”了,不能外出挣钱了,只能一心一意地演好戏。在宁夏话剧团工作的妻子在领导的关心下调到西安,接着团里又给解决了住房。士为知己者死。从此,李琦心无旁骛,安岗敬业。尽管他失去了发财的机会,可他最为珍视的是得到了领导的器重和信任。那年,陕西人艺一鼓作气推出三台大型话剧进京演出,李琦在古装戏《自居易在长安》中演配角,出人意料的是,每次下基层都能得到领导一个“有正确的劳动观点”的好评。对李琦的评价也不尽相同,主角黯然失色,演配角的李琦却捧回了令人炫目的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李琦成了“梅花奖”的得主,有人对他刮目相看,有人则在其背后指指戳戳。“这一回进京演出,等于给李琦抬了一回轿子。”“兄弟,话可不能这么说。要说是抬轿子,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轿夫,不过,我不像有些人是弯着腰抬轿,而我是挺起胸抬轿,所以人家看上了我这个挺胸的。”这是李琦的回答。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李琦成名了,成名后的李琦却多了几分忧虑和烦恼。演员们恢复了正业,舞台上有了新戏。周围那么多亲善的目光突然间变得尖刻起来,周围那么多朋友突然问变得陌生起来。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过错,人干吗要为“名”所累?远远地离开这个“名利场”,外面也许还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芳草地。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走了,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了那块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离开了他所钟爱的为之奋斗了十多年并登上理想高地的艺术事业,是年他三十六岁。他把自己的未来贴上一张邮票交付给人生那条没有航标的河流。
演马戏,住地下室,啃方便面,闯京城的日子经受磨难离乡背井闯京城者无外乎两种人,说是到基层办学,一种是心高气傲、不安于现状的年轻人,他们出来寻找大世界,他不属于这一种;另一种人是成名后来京城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他亦不属于这后一种。三十六岁的他为生活所迫而来,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次没有回程的“背水一战”。
京城,一个五光十色的大世界,那么多的高楼,那么多的汽车,那么多的宾馆和饭店,哪里是自己的归宿?这里人地两生,举目无亲,一切要从头开始,一切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
来北京的第一个夜晚,全家人是挤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地下室里度过的,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晚餐是每人一碗方便面。
要想立足北京,最重要的是尽快找一份能挣钱的工作。他说不清“求爷爷、拜奶奶”跑了多少趟,也说不清这期间鼻子上碰过多少次灰,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总算是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月坛体育馆“晚宴剧”中当演员。当了十多年演员,他第一次听说“晚宴剧”。所谓“晚宴剧”,实则是马戏团。当时月坛的“晚宴剧”正红火,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三:法国的“红磨坊”,纷纷下工厂、下部队、下农村,美国的“中世纪”,接下来便是中国的“哈哕,兵马俑”。看了一场“晚宴剧”的演出,李琦才知道这碗饭不好吃,演马戏要的是真功夫,要有胆有识、有勇有谋,要能腾能跳、能倒能立,这是勇敢者的事业,也是冒险性的职业。迫于生计,李琦居然和老板签了“生死约”。那的确是“生死场”上的搏击,现在回想起来也让人不寒而栗。
骑马不同于骑车,骑车只要一个脑子,骑马却要两个脑子,一个人脑子,一个马脑子,弄不好就出事,轻则摔它个鼻青脸肿,重则摔它个筋断骨折。那次团里刚来了一匹黑马,李琦不识其脾性,对其进行“放野”训练。那是一个秋日的清晨,旭日东升,霞光万道,李琦扬鞭跃马,有的是热情,春风得意,一路迎着朝阳飞奔而去。黑骏马一阵撒野的狂奔之后,突然出乎意料地来了个“急刹车”,李琦一个空中前扑,被强大的惯性推出足有二十米,用身体划了一个黑色的抛物线,重重地摔在地上。那一跤摔得好惨,右臂撕脱性骨折,眼膜破裂,轻微脑震荡。胳膊断了,打上弹力绷带继续练,这是竞争的需要,也是生存的需要。美国的“中世纪”训练一位熟练的马术演员时间是一年半,可“哈哕,兵马俑”的老板要求是三个月,这是胆识的训练,这是意志的训练,这是超强的训练。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文艺舞台迎来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百花盛开春满园”的繁荣景象。马上对刀是最具感官刺激的场面,那是真枪真刀的较量,那场面刀光剑影,壮怀激烈。一把钢刀演出三场就被砍成锯齿形,流血事件时常发生,身上被砍破了,他有的是力气,扎上绷带继续上台演出。李琦在马戏团干了两年,那两年真是摔打出来的,直到今天他才明白,那时挣的才是真正的“血汗钱”。
后来“晚宴剧”的老板破产关张了,至今还欠李琦两万元“血汗钱”没还。李琦说:“想起那段经历和那个无情无义的老板,我恨得咬牙切齿。那时我最需要钱,所做的一切冒险动作也是为了钱。黑心的老板每月只给三百元基本生活费。无力养活老婆孩子,只得把他们送回老家。”
来北京后的第一个春节想来让人心寒。冷锅冷灶,无亲无友,李琦在一个路边小酒店里炒了两个小菜,要了半斤二锅头,喝了个一醉方休。走出酒店,他觉得直想哭,一个男子汉哭什么?他不知道,可无法控制自己,还是在东四十字路口哭了一阵。他想给远在宁夏的老婆孩子通个电话。当时。‘路边没有电话亭,只得作罢,带着一把眼泪回到那个冰冷的家。大年初一早上,李琦刚刚泡上一包方便面,有人来敲门。打开房门,见是青年艺术剧院新识的朋友刘金山。“李琦,就你一个人在这里过年啊,凄凄冷冷的,李琦恰恰相反,走,到我家里去喝酒。”不负朋友盛情,李琦在朋友家过了一个伤心而又难忘的春节。
这期间李琦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之一就是他的“黄金搭档”陈佩思。李琦说:“佩思这仁兄爱才如命,爱戏如命,我能有今天,和他的帮助和提携是分不开的。”
“哈咿,兵马俑”倒闭后,李琦进了佩思的大道影业公司。起初,和佩思一起演小品。北京有线一台“天乐时光”栏目几乎成了他们独家经营的园地,每周二十五分钟节目,作品一个接着一个推出。回忆那段近乎荒唐的往事,李琦感慨地说,那些年,虽然没有上台演过戏,可从师哥、师姐身上学了不少,学校实行开门办学那阵子,严格地说是从他们身上“偷”来不少东西。那一年,他们接连演了三十多个小品,有《擦车》《焰火师的奇遇》《袁大头外传》……在带给人们笑声的同时,他也渐渐地被人们所熟悉。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函来了,北京电视台的邀请函来了,来者不拒,李琦抓住每一个机缘,不失时机地展示自己。他想,如果真的是一块玉石,就要把自己打磨得光彩照人,向世人展现自己的风采。
在京城风风火火闯荡了三年,磕磕碰碰地走过三载,很多人怕苦怕累,李琦慢慢地悟出了生存之道:如果说中国的文艺界有十条凳子,别人坐满了,你就要站着,因为你是第十一个。前面有人走了,才轮到你坐下。一开始你站着不说话,别人会认为你傻。后来,别人问话,你说了,别人认为你不傻。再后来,让你做事,你做得很好,人家会对你刮目相看。
“人熟是个宝,人好是个宝,人乖是个宝。听人劝,吃饱饭。”祖母当年给他留下的古训他一直奉为人生的座右铭。他老的不媚,少的不欺,该伸就伸,该缩就缩,不与人争,不与世争,扎扎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渐渐地落下一个好人缘、好名声。就这样,文艺团体如法效仿,李琦在北京立足了,小品他演,电视他拍,舞台戏他演,音乐会他唱,杂技他耍,演艺界的“十八般武艺”他样样上手。不久前,李琦又拜范圣琦为师,学吹萨克斯管。李琦说:“我唱歌不识谱,连业余也够不上。有时进录音棚,导演给我谱,这不是出我的洋相吗?我压根儿就不识谱。跟范圣琦老师学萨克斯管也是一样,先学拿乐器,再学1、2、3(刀、来、米)。有一次我问范老师,你教过基础这么差的学生吗?他说没有,可你不笨。我觉得爵士乐适合我的性格,有哀婉的音色,能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过去是听别人吹,有一天我将吹给别人听。我这个人好奇心强,好胜心强,什么事都想尝试一下。”“李哥,你这又吹又唱的,让我们吃什么?”身边的朋友这样跟他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