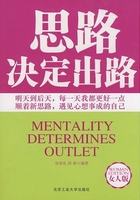一时间,明独秀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卢小姐,我大姐来到帝京不过十天而已,从未拜访过贵府,又怎会见到令尊呢?”
“我父亲前几日找令尊议事,恰巧遇见明大小姐回府,向令尊奉茶,又向我父亲见礼。所以我父亲才称赞她。”卢燕儿三言两语解释完,又奇怪道:“怎么,明大小姐没和你说么?”
明独秀心头暗恨,勉力维持住灿烂的笑容,说道:“许是大姐见我这几日忙于筹备此会,便没和我提起。”
言下之意,是在提醒众人,明华容虽然一时得了卢尚书的夸奖,明府最得意的小姐仍是她明独秀,再无人能越过她去。
但正处在震惊之中的众人此时已无暇分心细品她的话,纷纷猜测好奇着,明尚书家这位刚刚回府的小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因为同样的刻板才得到卢尚书青眼?抑或又是另有原因?
见众人仍旧议论纷纷,明独秀几乎要挂不住脸上虚假的笑容。这时,一个宛若天籁的温和男声恰到好处地为她解了围:“各位,反正明二小姐这就着人去相请明大小姐了,我们还是速去书房,不要让肖先生久等。”
“瑾王殿下说得是。”
“还是殿下想得周全。”
话音甫落,便是一片附议声。
明独秀感激地看了瑾王一眼,对方的支持让她重新找回了冷静与信心。她招手叫来贴身丫鬟阳春,低低吩咐了几句。
待阳春领命而去,她回头看了一眼疏影轩的方向,眼中露出一抹冷意。
随即,这份冷意很快便被惯常的爽朗微笑代替:“诸位这边请。”
为了今日的听课之会,昨日书院便停课一天,府上小厮们将三间并排厢房的间墙打通,又以纱帐相隔,预备让小姐们坐在右首厢房,少爷们坐在左首,肖维宏则在中间讲课。这样一来,既合规矩,又不影响听课。
明华容来到书院时,意外地看到肖维宏竟已先到了,正负手立于院内,展眼看向屋后细叶尽凋,唯余竹节的竹林,面上一派萧索,也不知在想什么。
相处数日,明华容早摸清了这位名士老师的脾气,知道他最是疏放不过。此时离开课还有半个多时辰,他却已站在这里,肯定不是为了备课,也不会是像寻常先生那样紧张得坐立不安,而是必有心事。
她对这位学问精深的老师还是比较敬重的,加上见都见了,也没有掉头就走的道理,便上来福了一福,问道:“老师来得好早,是不是有什么事?”
肖维宏长叹一声,声音里说不尽的颓然,但一开口,说的话却是没头没脑:“今日之事,我本不愿意。”
明华容了然地点头。以听课为名,给明独秀和瑾王制造机会,本就是白氏的主意。明守靖不忍拂她之意,又觉得这是桩雅事,且对自己有利,只象征性地询问了下肖维宏的意见,便就此定下。而肖维宏一介布衣,虽然声名在外,却也不好为这种事便惹得明守靖这堂堂尚书不快。
“什么听课,什么拜会,不过是个好听的幌子罢了。若在从前,我肯定拂袖就走。如今——”肖维宏面上满是颓然之色,“二十几年来,心气儿都消磨得差不多了。近来有时候更是会想,如果当初不是那么意气用事,现在也不用仰人鼻息地过日子。”
看着默然无语的明华容,他又苦笑一下:“这些话我再不会对别人讲,唉……也是奇怪,为什么单单就告诉了你这新学生。”
明华容却是暗暗奇怪,前几日老师虽然不太高兴,却没有露出这么明显的烦燥。莫非,最近他遇上了什么烦心事?会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动摇了一直坚持的信念,流露出对功名权势的向往?
但明华容并不觉得这是见不得人的事,想了想,便说道:“老师,人一辈子很长,不知会遇到什么事,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改了主意。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不是没有,但那未必就值得称许。我倒觉得,因势制宜,改变想法乃至追寻之物并不是坏事,反而理所应当。”
她本是想要安慰一下肖维宏,不想说着说着,却把心里话都讲了出来。前世的她从小在乡间长大,受乡下妇人的影响笃信菩萨,坚信只要忍耐付出,便会苦尽甘来,今日所受种种苦难,来日都会得到偿报。
可还报的结果是什么?一碗毒药,一把利剑,多年的欺骗利用,临死的嘲讽不屑!
她曾以为得到了幸福,实际所谓的良人只是一头披了画皮的白眼狼!
想起旧事,她一时心绪翻涌,一双杏眼微微眯起,眸中冷光幽幽,更胜寒冰:“若大难临头,仍然一昧固执地坚持原本的作法,或许有些人会将这称之为气节。但我却觉得,这是冥顽不灵,只会让人束手待毙!简直是最愚蠢的死法。”
所以重活一世,她不会再坚持什么以德报怨,不再对人性抱有幻想。她要的是步步为营,将他们亏欠她的一一讨回!不死不休!
肖维宏惊讶地看着这个学生,她脸上完全不见平日的沉静,表情幽冷,目光寒厉。那模样不免令他暗暗心惊,但心中莫名地生不出排斥厌恶,反而颇有几分怜惜。
而她说的话虽然听之惊心动魄,细细思量起来却不无道理。想到这个学生的坎坷身世,再联想到自己近来的忧心事,一个模糊的念头在肖维宏心中慢慢成形。他刚要说话,却听明华容说道:“一时口快,老师勿怪。您还没磨墨吧?我替您磨墨。”
说着,也不待肖维宏答应,她便径自往房内走去,拿起上好的松烟墨条,便在进贡的端砚中缓缓研磨。那沉静从容的模样,恍然又是平日的恭谨学生,刚才的冷厉言语,仿佛全是一场错觉。
看着她的侧影,肖维宏心中突然生出一个荒诞的念头:这学生心智与城府都非常人能比,将来成就,恐怕犹在她父亲之上。虽然他自己也说不出,一名闺阁弱女的成就要如何超越位极人臣的尚书,但这个念头依旧在心中扎下了根。
这时,众人在明独秀的带领下正好来到书院。一眼看到的,便是一名白衣少女皓腕微露,站在长案边研墨。浓黑的墨条被素白纤手一握,衬得白者愈洁,竟似将手背上覆的白绫衣缘都生生压下去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