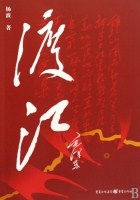偶尔会有人[772]来陪我钓鱼,他住在康科德镇的那边,穿过镇区到我家来做客,结伴钓鱼和共同进餐差不多,也算是一种社会交往吧。
隐者[773]:我在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三个小时以来,我甚至连蝗虫在香蕨木[774]上发出的声音都听不到。鸽子在它们的巢里睡觉,完全没有动静。刚才是某个农夫在森林那边吹响正午的号角[775]吧?那些雇工正在奔着煮熟的腌牛肉、苹果酒和玉米饼而去。人们为何要如此自寻烦恼呢?人只要不吃饭,就无需劳动[776]。我很好奇他们到底收获了什么。有谁愿意住在狗吠叫人不得安宁的地方呢?还有家务!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有家室的人得擦亮大门上该死的把手,还要擦净他的浴缸!其实没有家更好。倒不如住在空心的树里,那就无需操心晨访与晚会!只有啄木鸟的敲击声。人们麇集而居,那里的日头太过温暖;在我看来,他们入世太深了。我从甘泉取来清水,木架上有块黑面包[777]。听啊!我听见树叶的沙沙响。是镇上哪条饿犬到这边来追捕猎物吗?抑或是那头丢失的猪?据说它就在这片森林里,我曾在雨后看到它的踪迹。那声音迅速地移动着;我的漆树和锈红蔷薇[778]正在颤抖。诗人先生,是你吗?你今天觉得这个世界怎么样?
诗人:看看那些白云啊,它们高高地飘在空中!那是我今天见过的最伟大的东西。古老的画作里没有这样的云彩,异域的大地上没有这样的天空——除非是在西班牙的海边[779]。那是真正的地中海[780]蓝天。既然日子总要过下去,而我今天还没吃过东西,我想不如钓鱼去吧。那是真正适合诗人干的事业。那是我唯一学会的手艺。走啊,我们一起去。
隐者:我无法拒绝。我的黑面包很快就会吃完。等下我会很高兴地陪你去,现在我要结束一次严肃的冥思。应该很快就好。所以暂时让我独处吧。但为了节省时间,你可以先去挖鱼饵。这附近的蚯蚓比较少见,因为土壤中的肥料不多;那种虫子差不多绝迹了。如果你不是太饿的话,挖蚯蚓的乐趣并不亚于钓鱼;这件事今天就全靠你啦。我建议你到那边的地豆丛里去挖,你看到吗,就在金丝桃摇曳的那边。如果你好好观察挖起的草根,就像锄草那么仔细,我保证你每挖三下就能找到一条蚯蚓。或者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去,那也不失为好主意,因为我已经发现,离这里越远,地里的鱼饵就越多。
独处的隐者:让我看看啊;刚才想到哪里了呢?大概是在这个思维框架里吧,从这个角度看待世界。我应该到天堂去,还是去钓鱼呢?假如我匆匆结束这次冥思,将来还能得到如此美妙的机会吗?刚才我几乎就要与万物融为一体,那是毕生未曾有过的体验。我担心今后再也不会有这些灵感。如果吹口哨能让它们回来,我是很愿意吹的。假如灵感前来敲击我们的心扉,而我们却说你先等等啊,这应该是很不明智的吧?我的灵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再也找不到那条思路。刚才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呢?今天是个阴霾的日子。我准备再思考几句孔夫子说过的话;它们也许替我找回先前的状态。我不知道那种状态到底是困惑,抑或是萌芽中的狂喜。千万要记住。这样的机会永远只有一次。
诗人:现在怎么样,隐者,我会不会太快?我已经抓到十三条完整的蚯蚓,还有几条断的和没长大的;不过它们可以用来钓小鱼;它们穿在钓钩上正正好。这些乡下的蚯蚓实在是太大了;闪光鱼说不定都吃饱了还没碰到钓钩呢。
隐者:很好,那我们走吧。我们应该到康科德河去吗?如果水位不太高的话,去那边钓鱼是很好的消遣。
为什么世界恰恰是由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构成的呢?为什么人的邻居正好是这些动物,仿佛只有老鼠才能填充这个裂缝?我怀疑毗德拜公司[781]已经将动物派上了最好的用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是些负重的动物,承载着部分人类的思想。
在我家出没的老鼠不是常见的家鼠(那种家鼠据说是从外地来的),而是镇上看不到的本地野鼠。我曾寄了一只给某位杰出的博物学家[782],他对其非常感兴趣。在我盖房子的时候,有只野鼠把窝安在我的屋底下;当时我尚未铺好地板,刨花也还没扫掉,它常常在午餐时间跑出来,到我脚边吃面包屑。它原本也许从未见过人,很快就和我混得非常熟,会从我的鞋子爬到我身上的衣服来。它蹦几下就能爬上木屋的墙壁,特别像松鼠,连动作都像。后来有一天,我倚着长桌,手肘压在桌面上,它爬上我的衣服,顺着袖子爬到桌面,围着我用来包食物的那张纸不停地转圈,我把食物裹好,拿在手里晃来晃去逗它玩;最后我用大拇指和食指捏起一小块奶酪并稳住不动,它走到我的掌心坐下,旁若无人地啃了起来,吃完后像苍蝇般擦擦脸和爪子,潇洒地走掉了。
有只灰胸长尾霸鹟[783]很快在我的木屋里筑了巢,一只旅鸫[784]也到屋边的松树上寻找庇护。六月间,榛鸡(Tetrao umbellus)带着幼鸟经过我窗边,从屋后的森林飞到屋前,像母鸡般咯咯地对着它们叫唤,从其行为来看,它活脱脱是森林里的母鸡。这种鸟非常害羞,要是有人走近,母亲会发出信号,那些小鸟就突然散开,像是被大风卷走了。它们长得特别像落叶和枯枝,所以经常有过路者踏到幼鸟中间,然后听见老鸟扑扑地振翅飞走,同时发出焦急的啼唤和哀鸣,或者张开双翼想要引起他的注意,却浑然不觉脚下有群小鸟。当了父母的榛鸡有时候会装疯卖傻地在你面前打滚和转圈,让你一时间弄不明白它是何方神圣。幼鸟则乖乖地蹲着,常常把脑袋埋在树叶之下,只会留意它们的母亲从远处发出的指令,你走近了它们也不会现身跑开。你甚至可能踩到它们身上,或者盯着它们看了一分钟,都不会发现它们的存在。我曾在这样的时候把它们捧在手里,由于只听从母亲和本能,它们依然乖乖地蹲着,既不害怕也不发抖。这种本能实在是非常完美,有一次我把它们放回到树叶上,其中一只小鸟偶然翻了下来,隔了十分钟后,我发现它跟其他小鸟仍在原地,而它还是保持着那个姿势。和大多数鸟类的幼雏相比,它们其实算是早熟的,它们的羽毛甚至长得比小鸡还要丰满。这些幼鸟有着严肃的大眼睛,眼神特别成熟,然而又透露着天真无邪,真叫人过目难忘。它们的眼睛似乎蕴含着无穷的智慧。那里面不仅有婴幼的纯真,也有久经岁月磨砺的睿智。这样的眼睛不是在那些小鸟诞生时出现的,而是和它们所映照的天空一样古老。它们是森林里最珍贵的宝石。路过的人并不常常看到如此清澈的深井。无知而又粗俗的猎人常常在这个时节击毙它们的父母,让这些无辜的幼雏成为野兽和猛禽的猎物,或者渐渐地随着那些和它们十分相似的落叶腐烂下去。据说要是由母鸡孵出来,它们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四散奔逃,从而迷失在外,因为它们永远不会听到母亲再次召集它们的啼唤。这些就是我的母鸡和小鸡。
让人称奇的是,有许多野生动物自由而秘密地生活在森林里,至今仍然到城镇附近觅食,只有猎人才能发现它们的踪迹。这里的水獭[785]活得多么隐秘啊!他可能长到三四英尺长,像小孩那么大,但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我先前曾在屋后的森林看到过几只浣熊,可能还曾在夜里听到他们的叫唤。我通常耕作到中午,然后到树荫下休息一两个小时,先把午饭吃了,再去泉边看会书;那泉离我的田地有半英里,从布里斯特山[786]下面冒出来,是一片沼泽和一条小溪的源头。要到那边去,得经过几处地势逐渐降低的洼地,那些洼地生长着许多青草,还有年轻的刚松,然后再走到沼泽边一片面积较广的林地。树林里有个非常僻静和荫凉的地方,那里有棵茂密的白松树,树下有块干净而牢固的草地可以坐坐。我挖掉泉边的泥土,挖出一口井来,里面满是灰色的清澈泉水,这样我用瓢取水也不会让其变浑。到了盛夏时节,我几乎每天都到那边挑水,因为那时候湖水比较热。丘鹬[787]也会领着她的幼雏去那里,在泥土里寻找蚯蚓,又沿着泉水边缘低飞,离地面大概只有一英尺,她的子女则在下方奔跑着。后来丘鹬发现了我,于是离开那些幼鸟,围着我不断地转圈,越转越近,直到离我只有四五英尺,做出歪歪扭扭的怪样子,试图引开我的注意力,别去骚扰她的孩子;而那些幼鸟在她的指引之下,已经迈开步伐,在微弱无力的啼叫声中,排成一队走进了沼泽。有时候我能听见幼鸟的叫声,却看不见母鸟的踪影。那里也有哀鸽[788],或坐在泉边,或在我头上柔软的白松枝条间飞来飞去;还有红松鼠[789],从最近的树枝溜下来,表现得特别亲热和好奇。只要在森林里某些迷人的地方坐得足够久,那里所有的居民都会轮流到你面前来展示它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