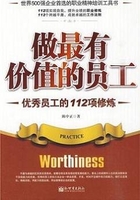我也目睹过些许没这么祥和的事件。那天我走出门外,到我的木料堆或者说废木堆去,到了之后看见两只大蚂蚁,一只是红色的,另外那只体型大得多,差不多有半英寸长,是黑色的,正在激烈地打斗。一旦相互缠上,它们就再也不肯松开,而是在木板上不停地扭打翻滚。朝更远的地方看,我惊奇地发现,许多木板上布满了这些战士,原来这并非两者的决斗,而是群体的大混战,是两种蚂蚁间的战争,红的总是向黑的扑过去,通常是两只红的对阵一只黑的。这些迈密登军团[790]覆盖了我的木场里所有的高山和峡谷,地面已经到处散落着死者与垂死者,红的黑的都有。那是我唯一亲眼见到的战争,那是我唯一亲身经历的炮火正酣的战场;一边是红色的共和大军,另一边是黑色的帝国部队。双方正在进行殊死搏斗,可是我听不见任何噪音,人类的士兵未曾如此决绝地战斗过。当时正是中午,我看见在木板间一个洒满阳光的小峡谷里,有两只蚂蚁死死地抓住对方,准备奋战到太阳下山,或者到死为止。体型较小的红色斗士像铁钳般抓住敌手的脑门,在战场上翻来滚去的同时,不停地去咬对方触须的根部,而且已经把另外那根触须给咬掉;那只更为强壮的黑蚂蚁则举着他甩来甩去,我靠近了看,发现原来红蚂蚁也有几个部位被咬掉。他们打起架来比斗牛犬还要狠。双方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他们的战斗口号显然是“不战胜,毋宁死”。就在这个时候,有只红蚂蚁独自来到峡谷的半山腰,显得特别兴奋,可能已经击败了敌人,也可能尚未参加战斗;大概是后者吧,因为他的肢体完好无损;他的母亲要求他拿着盾牌凯旋而归,要么战死沙场躺在盾牌上回来[791]。或许他是阿喀琉斯,已经平抑了胸中的怒火,前来复仇或者拯救他的帕特罗克洛斯[792]。在远处看到这场不对等的打斗(因为黑蚂蚁的体型差不多是红蚂蚁的两倍),他迅速地走到旁边占好位置,离两位战斗者只有半英寸;他看到有机可乘,立刻向黑兵扑过去,开始用各种招数攻击对方的右前脚根部,完全不顾敌人要击打他自己身上哪个部位;于是这三只蚂蚁为了活命而纠缠得难解难分,仿佛有一种新发明的、让铁锁和水泥相形见拙的黏合剂将它们粘了起来。此时此刻,就算看到某块显眼的木板上有双方的军乐团,吹奏着各自的国歌,以便催促行动缓慢者奋勇向前,鼓舞受伤垂死者的情绪,我也不会觉得奇怪。甚至连我自己也有点兴奋,仿佛这些蚂蚁就是人。你思考得越深入,两者的区别就越小。美国的历史且不去说,至少康科德历史上肯定没有哪场战役能够与此相提并论,无论是从参战的士兵数量上来看,还是从展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和英勇无畏的精神上来看。就士兵的数量和惨烈的程度而言,这场战斗堪比奥斯特里茨大会战[793]或德雷斯顿大战役[794]。康科德战役[795]算什么!不过是爱国军牺牲了两个人,路德·布兰夏德[796]受伤而已!这里的每只蚂蚁都是布特里克[797]——“开火!以神的名义,开火!”——而且有数千只蚂蚁遭遇了戴维斯和霍兹莫[798]的命运。这里没有雇佣兵。我毫不怀疑他们交战是为了某些原则,我们的祖先也是为了原则而战,并非只是让他们的茶叶免交三便士的税金[799];这场战役的重要程度和值得纪念的程度,至少和班克山大战[800]不相上下。
我捡起那块有三只蚂蚁在上面大战的木板,把它拎进屋里,摆在窗台上,再用玻璃杯将三只蚂蚁罩住,准备看看战况到底如何。我拿起放大镜对准了最早提到那只红蚂蚁,发现它虽然奋力咬住敌人的前腿,已经弄断对手剩下那根触须,但他自己的胸膛也被撕开,里面的重要器官全都暴露给黑蚂蚁的利齿,可是他又刺不穿黑蚂蚁胸前的铠甲,因为那对他来说显然太厚;这受伤者的黑色眼珠闪烁着只有战争才能激起的怒火。他们在玻璃杯下面又打斗了半个小时,等到我再去看时,那位黑色战士已将敌人的脑袋砍下来,那两个头还会动,挂在他背后的两侧,活像是挂在马鞍边的可怕战利品,却仍然死死地咬住不放。黑蚂蚁丢掉了两根触须,腿也只剩下一条,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伤口,他软弱无力地挣扎着,想要把两个脑袋从自己身上甩掉;又过了半个小时,他终于成功了。我拿起玻璃杯,他就那样趔趄地从窗台爬了出去。他最后是否能够从这场战争中逃得生命,在伤残医院里度过余生,我并不知道;但我认为他今后可能做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事情。我不知道获胜的是哪方,也不知道双方交战的原因;但是那天剩下的时光里,我的心情因为目睹了这场争斗而激动和悲伤,仿佛在我门前上演的是一场人类的大战。
克尔比和斯宾瑟告诉我们,人类早就注意到蚂蚁的战争,也记录了许多战役的日期;不过他们又说,现代作家里面似乎只有哈勃[801]见证过这些战役。他们说:“埃尼阿斯·西尔维乌斯[802]在详细地描写大蚂蚁和小蚂蚁在梨树上展开的惨烈战争之后,又补充道:‘这场战争发生于教宗恩仁四世[803]在位期间,目击者是尼古拉斯·皮斯托里恩西斯[804],这位杰出的讼师极尽忠实地记录了这场战争的全部历史。’奥劳斯·梅格努斯[805]也曾记录大蚂蚁和小蚂蚁的战役,那次的获胜方是小蚂蚁;据说小蚂蚁埋葬了己方阵亡士兵的遗骸,但对敌方巨大的尸体则弃之不顾,任由飞鸟去啄食。这件事发生在暴君克里斯蒂安二世[806]被驱逐出瑞典之前。”[807]我看到的战争则发生在波尔克[808]担任总统期间,韦伯斯特[809]的《流亡奴隶法案》[810]生效五年之前。
镇上有些看门的狗,明明只有在储藏食物的地窖追逐拟鳄龟的本事,却偏偏瞒着主人,到森林里来活动其笨拙的四肢,徒劳无功地去嗅狐狸的老巢或者土拨鼠的洞穴;大概是某只狡猾的猎犬领来的吧,那猎犬灵巧地在树丛间穿行,生活在森林里的动物也许对他还有一种天生的恐惧;这时看门的狗远远地落在他的向导后面,像斗牛犬般朝着某只早已爬到树上察看动静的小松鼠吠个不停,然后转身走开,肥胖的身体把灌木丛都压弯了,还以为他刚才追逐的是离群的沙鼠[811]。我曾看到有只猫走在满是石子的湖岸,当时感到很意外,因为它们很少流落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来。那只猫看到我也很吃惊。虽然那是只最寻常的家猫,成天躺在地毯上,可是到了森林里她像是回了家,灵巧敏捷的动作证明她比森林里常见的动物更加适合这个地方。有一次,在采摘浆果的时候,我在森林里遇到一只大猫和几只小猫,那些小猫特别野性,和他们的母亲一样,看到我之后立刻拱起后背,恶狠狠地对着我叫。在我搬到森林里生活之前几年,大家都说有只“长着翅膀的猫”[812]生活在林肯镇离瓦尔登湖最近的农场,也就是吉利安·贝克尔的农场[813]。我曾在1842年6月去拜访她(我不知道那只猫是公的母的,姑且用这个较为常见的代词吧),当时她又习惯性地到森林里捕猎去了,但是她的女主人对我说,她到邻近地区来是一年多前的4月,最后被他们家收留了;她是棕灰色的,喉咙有个白点,脚也是白的,尾巴像狐狸般又大又多毛;到了冬天,她的毛发会变厚,从身体的两侧平伸而出,大概有十到十二英寸长和半英寸宽,脖子的毛则变得像暖手筒,上边很蓬松,下边像毛毡般粘在一起;春天这些附加物都会脱落。他们送了我一对她的“翅膀”,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呢。它们看上去不像是猫身上长出来东西。有些人认为她有鼯鼠[814]或者其他野兽的血统,这倒也不是不可能,因为按照某些博物学家的说法,貂和家猫交配可以生出许多各不相同的杂种。如果我要养猫的话,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既然诗人的马是有翅膀的,他的猫也应该有吧?[815]
秋天的早晨,我还没有起床,潜鸟如同往年,到湖里来脱毛和洗澡,他那狂放的笑声在树林间回荡。听到他已经莅临的消息,镇上的猎人纷纷出动,或驾驶二轮马车,或徒步,带着猎枪、子弹和望远镜,三三两两地来到森林里。他们穿过树林,像秋天的落叶般发出沙沙的响声,一只潜鸟至少会引来十个猎人。有些埋伏在湖这边,有些在湖那边,因为那可怜的鸟儿总要在某个地方出现的;如果他从这里潜入水底,肯定要在那里出来。但这时好心的秋风渐渐变大,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在湖面激起了波浪,这样潜鸟的声音就不会被听到,踪迹也不会被看见;但他的敌人用望远镜扫视着湖面,让树林回响着他们的枪声。湖里翻涌起巨大的波浪,愤怒地拍打着湖岸;这些波浪是和所有水禽同一阵线的,我们的猎人只好撤退到镇上,回到他们的店铺里,或者回去继续干着原先抛下的活计。但他们经常能够如愿以偿。每当我在清晨到湖边去提水,往往能看到这种高贵的鸟在我的湖湾里航行,和我只隔着几杆的距离。如果我想要划着小船超过他,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他就会潜到水里,随即彻底消失,有时候我要到当天下午才能再次看见他。但说到在湖面上比快,他可不是我的对手。要是遇到下雨天,他就飞走了。
在10月某个非常安静的午后[816],我沿北岸划着船,因为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很可能会在湖泊停驻,像乳草[817]的绒毛般飘然而下;正当我在湖面上寻找潜鸟却毫无所获时,突然有一只从岸边向着湖心游去,在我前面几杆远的地方;他发出了狂野的笑声,暴露了他自己的行踪。我赶紧划船追过去,他潜入水底,但等到他浮出来,我比刚才离得更近。他又钻到水里去,但这次我估错了他逃走的方向,等到他冒出湖面,我们相隔足足有五十杆,因为刚才我和他背道而驰;他再次大笑了很久,显然是在嘲笑我。他的行动特别奸猾,我和他始终隔着至少五六杆的距离。每次浮出水面,他都会扭着头左看右看,冷静地察看湖水和陆地,显然是在选择潜水的路线,以便他正好在水面最开阔、离小船最远的地方浮上来。最让人称奇的是,他做出决定非常迅速,执行起来又特别坚决。他很快将我引到最开阔的湖面,再也没有被逼到死角之虞。当他在脑海中思考一件事的时候,我也努力地在我的脑海里分析他的想法。这真是一场漂亮的棋局,平滑的湖面充当了棋盘,对弈的是一个人和一只潜鸟。突然间,对手的棋子消失在棋盘之下,现在你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你的棋子摆在离他下次出现最近的地方。有时候,他会出其不意地从我的背面出现,显然是直接经过了我的船底。他憋气的功夫非常了得,而且体力也非常充沛,所以有时候尽管已经游了很远,他还能够再次扎进水底;谁也猜不出来在平静的湖面之下,他会像鱼儿般游到多深的地方,因为他有时间和能力去踏访瓦尔登湖的最深处。据说在纽约的湖泊,有些潜鸟曾被水底八十英尺用来钓鳟鱼的铁钩钩住——然而瓦尔登可不只那么深。鱼儿看到这位来自其他领域的怪客迅速地在他们之间游动,肯定感到很吃惊吧!然而他好像在水底也是认路的,跟在水面没有区别,而且在水里的游动要快得多。我有一两次看到湖上泛起波纹,原来是他碰到了水面,稍稍把头探出来再次确认路线,随即又沉下去。我发现与其费神去计算他会在哪里冒出来,倒不如停下双桨好好休息,等他再次出现;因为一次又一次,每当我朝某个方向死盯着湖面,他会突然在我背后怪笑,吓我一大跳。可是他明明如此奸诈,每次出水时为什么非要大笑,从而暴露自己的行迹呢?难道那白色的胸羽还不足以出卖他吗?他真是一只愚蠢的潜鸟,我想。我通常能听见他出来时湖水的泼溅声,从而探测到他的所在。但过了一个小时以后,他的精力还是那么充沛,潜起水来还是那么高兴,而且游得甚至比刚开始还要远。从水底浮出来以后,胸羽依然齐整的他在湖面上航行着,全靠宽大的脚蹼在水里不停地拨动,那器宇轩昂的样子真叫人惊奇。他的声音通常是邪恶的奸笑,然而水禽差不多都是这么叫的;但是有时候,当他成功地避开了我,游到非常远的地方再冒出来,他会发出一声长长的、怪异的嚎叫,与其说是鸟啼,不如说是狼嚎;很像是野兽故意把嘴部贴到地面而发出来的吼声。这是潜鸟特有的叫声——也许是这里的人们听到过最狂野的声音,远远地传遍了整片森林。我认为他是在嘲笑我白费力气,对他自己的本领很有信心。虽然这时的天空已是阴云密布,湖面仍旧非常平静,所以在听不到他的声音时,我也能从水面的涟漪发现他的所在。他那白色的胸膛、静止的空气和平滑的湖面统统不利于他隐藏行迹。到最后,他在离我五十杆的地方浮现,发出一声长长的嚎叫,仿佛是在呼唤潜鸟之神前来帮忙,立刻有一阵风从东边吹来,让湖面泛起了波澜,又让整个天空飘起了迷蒙的细雨,我感觉这好像是潜鸟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他的神因我而愤怒,于是离开了他,任由他在波浪翻涌的湖面渐行渐远。
秋天时,我常常花好几个小时,观看成群的野鸭灵巧地在湖心游来游去,远远地避开那些猎人;等他们去了路易斯安那[818]的湖沼,大概就无需使用这些技巧了吧。等到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他们会盘旋而起,在瓦尔登湖上方高高地翱翔,变成了天空中的黑点,在那么高的地方,他们应该很容易看到其他湖泊和江河;正当我以为他们早已朝那边飞去的时候,他们会斜斜地飞上四分之一英里,落到远处不受猎人骚扰的湖面;但他们在瓦尔登湖的湖心畅游,除了安全以外,是否还有别的收获,我就不知道了。大概他们和我一样,也是莫名地热爱着这片湖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