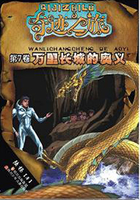外面风吹得很轻,平平淡淡吹不起半丝波澜。
屋里,南宫老太太絮絮叨叨询问她冷漾的情况,子矜偏过头适度的答着,颊边一束灼热的目光逡巡而上,烙红了脸。
终于,她忍受不住,偏过头狠狠地瞪过去,迎上的却是由黑眼眸中深深的愤怒和伤痛,那眼神仿佛有了魔力,连她的心,也痛起来。
他瘦了许多,也比以前更加沉稳,举手投足散发着成熟男子的魅力。
“昙儿?”
老太太的声音打破寂静,自上而下地传来,她猛然回神,掠去脸上一闪即逝的惊诧,恢复眼中淡笑:“娘!”
“你这孩子,最近老是心不在焉的。”老太太嗔怪的看了她一眼,扫到她潮红的脸,立即绷紧了弦,探下身子急道:“昙儿,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可是病又犯了么?”
“呃……”
子矜面对老太太的关心有些无措,情不自禁的摸红的滚烫的脸,余光扫到安王面无表情的脸,尴尬的笑道:“娘,没什么大碍,孩儿只是有些热。”
老头子对老太太的大惊小怪很是不满,抬手轻轻的敲着桌子,不满的望着老伴提醒:“注意仪态,人家安王爷还在这里呢。”
安王脸上含笑,淡淡瞥了子矜一眼很快别过头继续和二老寒暄。
外面的鸟儿雀跃的穿梭在枝头,叫得欢快。
他不知费了多大的力气才将心中诸多喜悦与愤怒并存的情感归于平静,然后急不可待的赶到南宫府,他曾想过诸多见面的情景,四年,她瞒了他四年,还是在他眼皮底下,这让他愤怒而又挫败,他想他应该狠狠地吻住她,让她知道这四年的煎熬和惩罚,他也想应该紧紧地将她拥进怀中,因为这四年,她一定吃了很多苦。可是,见到男装的她,他突然打消了这个念头。
看得出来,她终于找到要极力维护的东西,无论是南宫家还是南宫二老在她心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也许,他可以帮她一起守护她所努力守护的,他已不想再分离,四年,他终于尝到失去与思念噬骨的滋味。
只是,这世上,到底谁在守护着谁呢?
他抿了口茶,微偏的角度显示出他优美高贵的下颚。
手下悄声进来,在他耳畔低语几声,他的眉不自觉地皱起来。
子矜的指尖忍不住轻轻一跳,抬眸看去,他已经站起身来向二老请辞。
心中是难掩的不舍,苦涩的溢出来,口中上好的茶水也失了味道。
又是离别……
就算不能在一起,哪怕,能常常看到,也是幸福的,可是,偏偏没有这样的机会。
是啊,她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得到幸福。
安王优雅的起身,看到的是子矜恍惚而缥缈的眼神。
心不自觉地又痛起来,也许,昙的死对她的打击真的很大,她和冷漾平安无事,昙却失了音信,想想都回知道是怎么回事。
“南宫少爷不打算送送本王么?”
他卓然立在那里,脸上带着戏谑与怜惜。
“唔。”
子矜这才迟钝的放下手中的茶盅,抬脚将他让了出来。
周围是一片葱郁的绿,两人并排走在路上,谁都不曾说话,也许,只是千言万语,不知如何开口而已。
路漫长而短暂。
终于,路到了尽头,南宫府的大门紧在咫尺,子矜突然觉得绝望,那种绝望仿佛蔓延的藤萝紧紧缠绕而上,几乎窒息。
她理了理思绪,脸上的笑僵硬而淡定,做了个请的姿势,望着那张冷峻的脸幽幽叹息:“王爷请。”
安王却没有说话,站在离她近在咫尺的地方,突然勾下头,伸出修长的指勾住她颈边领口,显露出白皙的肌肤。子矜吃了一惊,刚要躲。他的鼻尖已经凑过来,灼热的气息喷涂到脖颈上,带着些许的挑逗气息,声音磁性而低沉的喷吐过来:“不知南宫少爷用的什么香,怎这般清香的难以忘怀呢?”
身后的随从们惊讶的张大了嘴,南宫府的仆人们目瞪口呆,两人姿势这般暧昧,让人感觉他们仙一般的少爷被眼前这个男子调戏了。
子矜的脸瞬间涨红,白皙的脖颈也浮上淡红粉色,又不能冒昧的推开他,心中突然冒出无名火,突觉安王这种举动是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牙根咬得有些响,只硬着头皮绷着脸道:“王爷说笑了,在下一向不用香。”
“咦,那就怪了。”
安王脸上出现少有的惊诧神情,松了手,站直身体,双眸深邃的锁住她的脸嘴角勾的意味深长:“是本王的失误,只是南宫少爷身上的香确实让本王难忘之极啊。”
肩头的气息不在,心中怅然若失,却被安王脸上的无辜表情击的粉碎,在她的记忆里,安王从没有这么恶劣,他的话暧昧不明,无故的在她心中漾起圈圈涟漪,她都是考虑好了的,帮他,做他的左膀右臂,她可以做他的手下可以是他的幕僚,助他得天下,可是却不该是这种被调戏的感觉,这样的安王,让她不知如何是好。
只是她不知道,四年的时间,足足可以改变许多,爱不变,只是方式变了而已。
“告辞!”
心中纷乱不已,安王已经退开几步向她告辞,神情淡定冷峻,仿佛在他面前的真的是一个刚刚见面的男子而已。子矜没有来的一阵失望,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仿佛在心底开了一个大大的洞,空虚的难以自抑。
“呃,再会。”
她回过神送他上了轿子,自己都不知道口中无意识的说出“再会”两个字。
安王正俯身进轿子,听到她这样说反倒停了动作,抬头定定看她,目光穿越稀薄的气息略到她白皙的脸上,半晌笑起来,缓缓道:“再会。”
轿帘落了下来,他修长的身形隐在帘后,看不真切。
轿夫缓缓起轿,身后的随从阵势俨然的走过。
整齐而有力步伐仿佛踏在她的心上一般,恐慌的难以捉摸的仿佛失去。
就这样,四年后的重逢就这样简单的结束了?
她有些不可置信,以他的个性不是部的目的不罢休的么,就算她总是离开,总是逃避,他也会设法把她捉回来,报复也好,愤怒也好,起码,她知道他是在乎的。
只是……
这样不是很好么,好聚好散而已。
她不是也想这样么,平平静静的,她站在他的身后仰望他,帮他,看着他喜看着他怒?
她不该那样傻,不该那样自私的想着他还会一如既往的待她好,她肆意的伤他,不顾他的感受躲他,她辜负了爱他每一个人,这是她应得的惩罚。
她怔怔站着,努力的安慰着自己。
“少爷?”
身后的声音低沉冷漠,回身,是寒夜无表情的脸,只是若是她细心些,可以发现他眼底的笑意。
“是否让属下去查查安王爷这四年有没有过别的女人?”
他平静无波的说这这句话。
子矜白皙的脸开始变青变红,随后化作深深的无奈,绷起脸努力维持南宫少爷的威严:“多话,回府。”
都过去了,过去了……
安王离开不到一个时辰,寒夜便送来了消息。
“离京?”
子矜有些诧异,按了按额头,皱着眉喃喃:“怎么偏偏这个时候?”
“皇上虽然多年对政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儿子们的动静他还是知道的,这次,安王爷和九王爷都对南宫珠宝行下手,为避免争执,他也不会无动于衷的。”
寒夜站在一旁提醒道。
子矜抿着唇不语,半晌才叹息道:“他到底是个父亲,不愿意看到兄弟相残的,只是老头子的心思越来越难以捉摸了,我想不通他为何派殇……安王出去,而不是九王爷。”
“想必有他得考量吧。”寒夜望着她,边说边从袖中拿出一个锦盒递给她。
子矜诧异的望他一眼。低头打开,里面是三颗颗粒饱满的红豆,嫩红的表皮光滑而细嫩,在微光中散发着盈盈光晕,仿佛鲜艳欲滴的朱砂,绚丽的绽放。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安王府送来的。”
寒夜轻声开口。
盒子“啪”的一声阖上,她站起身来,匆忙得跑了出去。
驿站旁,他骑在马上,白衣胜雪遮去周围光华,唇角的笑冷静淡漠。
禄王和烈王悄悄为他送行,说穿了,是奉了密旨查些陈年旧事,谁都知道,宸妃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
锦盒几乎握得断裂,她隐在暗影里望着他拉动缰绳离开。
似有所觉般,安王突然回过头望着个角落望过来,似乎没有看到什么,又重新回过头,光晕碎玉般的掠过,他的眼眸深邃似海。
为什么不告诉她呢,她想不通,还是她表明的立场不够明显,是否应该告诉他,她是要站在他身旁帮他的,其实,有些事情,根本就不用说。
她不明白,他只是不想让她卷进去,可他也明白,当她有了南宫昙这个身份时,她已经无预警的卷了进去。
南宫家,是一块人人都想得到的肥肉。
答应父皇,只是不想让他发现她就是南宫昙而已,一切的一切里,没有谁对谁错,他们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苦衷,只是竭力的演绎着自己的角色,爱了,痴了,满足了……而已。
白色的身影渐渐远行。
她站在阴影里,痴痴望着。
烈王转身上马,经过那个角落却停下了,修长的指紧紧捏住缰绳,皱着眉不语。
总觉得离开那里,就仿佛会失去什么。
“四哥,你怎么了?”
禄王上了马,见他不走,回过头询问。
“哦,没什么,走吧。”
他回过神,眉头皱得更深,别过头都动缰绳,马缓缓前行。
光晕中,他的黑衣泛着白亮的光。
心里空落落的。
仿佛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而且,这一辈子……只怕永远……也得不到了……
脚下是一个简陋的院落,青青的石板,简陋的青石房子。
不知为何,心中难受时,总是不自觉地走到这里。
门吱呀打开了,里面露出一张调皮可爱的笑脸,女子蓝色的衣在阳光下发出靓丽的光晕。
“子矜姐姐,你来啦。”
“颦儿”
子矜笑着打招呼。
“爹爹在屋里呢,你来。”
那个叫颦儿的女子亲热地挽了她的胳膊,将她踉跄的拉进屋内。
屋内,一个中年男子负手而立,深邃的目光掠过窗外落到虚无的远处,修长的身型在午后阳光处带着略略的落寞。
听到脚步声,缓缓地回头,就看到子矜被踉跄拉着的样子,他不由皱起了眉。
“颦儿,你子矜姐姐身子不好,别老拉拉扯扯的。”
男子沉稳的声音带着少许的严厉。
“爹,子矜姐姐一来,你的心立即就偏过去了。”
颦儿还拉着子矜的袖子,听到男子的声音,不满的嘟起唇,粉嫩的色泽仿佛娇嫩的桃花。
子矜好笑的拍拍颦儿的手,松开被握的起了褶皱的袖子,抬头对男子礼貌的颔首:“君叔。”
男子站在屋内,朝她点了点头,眼眸深处闪过几丝无法忽略的忧伤,让子矜不由一怔。
“子矜姐姐,我爹肯定又沏了好茶,你来。”
颦儿一脸笑妍,灿烂的连院中葱郁都失了颜色。
香茶浓郁,清香袅袅。
子矜抿了口,真诚的赞道:“好茶。”
男子看她喝下,脸上的神情带着几丝恍惚,怔了怔才回过神,道:“你喜欢就好。”
子矜缓缓地放下茶盅,青色的衣铺满了蒲团,水汽缥缈中,她的面容带着几丝朦胧,男子的眼眸不由又恍惚起来,皱着眉,仿佛陷入某种回忆。
“君叔……可是有心事么?”
迟疑片刻,她终于问出口,见男子微愣,忙尴尬的道:“君叔若是为难自不用说,只是四年前,君叔救了我和漾儿,君叔便是子矜的再生父母,子衿只是想帮君叔分忧而已。”
也许是“再生父母”四个字深深触动男子,他俊朗的面容开始松动,沉吟半晌才道:“从未听你说起过你的父母,有你这样善解人意的女儿当真是天大的福分。”
话一落地,子衿的脸却黯然起来,她勾着嘴角,无奈的自嘲:“君叔说的什么话,有我这样的女儿……是他们的不幸吧。”
见男子神情一变,子衿随即笑起来,别过头看向外面,喃喃自语:“娘亲一定会怪我,可是,我啊,把一切都搞砸了,现在,连见她一面都不敢。”
她的脸在光晕中略显苍白,茶香飘缈,带着几分落寞。
男子禁不住安慰:“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当时我和颦儿发现你们时并没有看到你所说的男子,他还活着也说不定。”
子矜微怔,缓缓地摇了摇头,忧伤的低语:“你不知道……我是亲眼看着他……”
话却再也说不下去,胸口被刺道一般的痛,脸色也愈加苍白的厉害。
一股灼热的暖流透过衫子由肌肤传过来,温和如春风,将那痛意缓缓驱散开来。
“你娘不会怪你,她所做的都是为你好,又怎会怪你,况且她当年那么做也是为了你好,你又何必自责这么多年……”男子叹了口气,松开按在她穴位上的掌怔怔问道:“你可恨你的父亲,他狠心的扔下你们母女,你可恨他么?”
不知为何,她觉得男子的情绪有些激动,抬眸望去,却平静无波。
也许,错觉吧……
“恨吧。”
她笑,翘起的睫毛在眼底投下一片淡淡的阴影,随即喃喃起来:“可是他有他的苦衷吧,除非他不爱我们,不然不会不管的。”她淡淡笑着,没有注意到男子忧郁深沉的脸。
“他是爱你们的。”
良久,男子拍了拍子矜消瘦的肩,突兀的说出这句话,子衿惊诧的抬头,他淡淡笑起来,温和的转移话题:“珠宝行的生意怎样?”
“多亏了君叔一直帮子矜出谋划策,不然怎会有这样的成绩。”
见他不愿说,子衿也不强求,只笑着答着。
“我只是提些建议罢了,重要的还是你自己。”
他微微勾了勾唇,抬手为她沏了杯茶,嘱咐道:“别太勉强自己。”
子矜怔了怔,没有说话。
院子里的花开得灿烂。
颦儿嘟着唇无聊的坐在秋千上晃动着双腿,精致的脸却带着少有的忧郁。
一个修长的青色身影从屋子里风姿卓越的走出来,行云流水般的举止清丽淡雅,步步生莲仿佛喷吐幽香的梨花。
她怔了怔,欢快朝她招手:“子矜姐姐,这里。”
子矜这才向她走过来,嘴角含笑,男装的她眉目间含带着少许的英气。
颦儿眯了眼抬头望她,半认真半开玩笑的道:“子矜姐姐,你若真是男子,颦儿就嫁你。”
子矜闻言无奈笑起来,阳光在她脸上洒下绚丽的色彩。
颦儿望着她喃喃自语:“你知道么,有时候你们真的很像。”
“像,谁?”
子矜诧异的挑眉。
“他啊,一个美的不似凡人的人,那时他截住我和爹爹,说什么要我们去救人,爹爹没有答应,令人动了手,后来爹爹不知和他说了什么,他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我从没见过那样美的男子……仿佛……瞬间开放的昙花……”
子矜脸上的笑缓缓僵住。
还有谁比他更适合这个名字,昙花一般的美丽,绚丽的炫目。
恍惚中,眼前又浮现那个男子的脸,烟花般灿然的笑,眼眸中是望不到底的雾气。
他温柔唤她,声音似乐:“丫头……”
心,又不可抑制的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