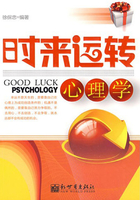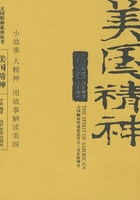九王爷的声音仿佛一根根刺一般,狠狠的扎到两人心上。
安王紧紧地捏住子矜的手,胸口剧烈的起伏着,他面色痛楚的看向皇帝,声音沙哑的低笑:“父皇这是要儿臣的命么,子矜是儿臣此生挚爱,她若出了什么事,儿臣靠什么继续活下去?”
子矜的唇微微抖动着,紧紧地回握,仿佛誓言一般。
皇帝本来紧闭双目,听到他这样说猛地睁开眼睛,他看着安王,脸上流露深深失望,也是这种时候,他才真正明白当年他的父皇又是以何种心情来看他的。
“混账!”
皇帝气得脸色扭曲,他沉痛的敲击着桌面,神色黑的骇人:“你这个孽子,你宁愿要美人也不要这个江山是不是?”他狠狠的瞪着他,仿佛在做着一个极大的决定,半晌才艰难的吐出字句:“好!朕成全你!”
他说完这句话,痛苦的闭上眼睛,朝一旁的九王爷摆了摆手。
九王爷会意,唤来锦衣卫,扫了二人一眼,视线停滞在子矜身上,目光深沉的可怕。
“押进大牢!”
他说。
“王爷,请吧!”
安王到底在军队中有着很高的声望,锦衣卫对其均是崇敬有加,在这个时候自也不会难为他们。
他扫了子矜一眼,淡淡点头,压低声音道:“内子麻烦各位多加照顾!”
“王爷放心,属下们定当竭尽全力!”
锦衣卫诚挚应是,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
安王深深看了子矜一眼,转身大步走了出去。
外面桃花开的粉嫩,春意盎然,散发着浓浓活力。
暗色的夜里,他雪白的身影孤寂挺直。
子矜的心却恍若结了冰一般,在这个慵懒安详的春夜,她的心入坠冰窟。
“姑娘!”
锦衣卫见她出神,忙提醒她,子矜这才回过神,点了点头,也举步走了出去。
春夜里,她的背影依然挺直孤寂。
屋内很静。
皇帝已经起驾回宫。
客厅里空空荡荡的只剩他一人,地上雪白的碎片在夜色里散发着刺眼的光亮。
九王爷呆呆的站在原地,忘了恭送皇帝,只望着远处雪白碎片上的那几滴猩红怔怔出神。
他做到了不是么,他们从小到大一直想要的,最后终于落到了他的手里。
他笑了,随即又沉寂在俊秀狰狞的神情里。
可是,代价,他的代价是什么呢,是他心爱女子的鲜血吧。
从没想过,温暖的春意里,有的地方也可以阴暗的冷如骨髓。
三面是冷冰冰的墙壁,另一面是刺骨的铁栏杆,斗大的铁锁将里面的人封闭在牢笼里。
换了一身囚衣的子矜抱着膝坐在低矮的床铺上,望着外面出神。
多么可笑,她,连同她最亲近的人都被关进了这里,虽然相互见不到,却能清晰地感觉到彼此的存在。
她觉得伤心,也清楚,从小到大一直追求的,顷刻间没有了希望,会有多么的无望和悲伤,铁骨铮铮的他,将这巨大的伤痛埋进那幅傲骨里,掩饰的一丝不漏,临走还不忘给她一个鼓励的眼神。
可是,这种时候,她却不能陪在他身边鼓励他,安慰他。
她突觉得以前得自己是多么自以为是和任性,她曾经期望他放弃所有只要她一人,现在她才明白,那是他的梦想,就像她的梦想一般,她利用他对她的爱逼他放弃自己的梦想,是多么残忍和不理智。
子矜懊悔的将头埋进膝间,泪流满面。
一次,就一次,给她一个机会,让她能为他做些什么吧。
朝廷里人心惶惶,本来四王爷被押进大牢就已经足够让大臣们乱猜不已,好在当时安王雷厉风行将这件事压下去,才有所好转,现在禄王和安王也相继入狱,在众多皇子里,也只剩九王爷有些作为,一时,九王府门庭若市。
皇帝也渐渐将一些朝内事务交与九王爷,只是却远远没有对安王那般信任,在皇帝身体欠佳的那段时日里,他都坚持亲自处理,交与九王爷的不过一些小案子罢了,一时,朝内又是猜测不已。
奈何,圣心难测,过了一段时日,皇帝宣布安王一案由他亲自处理,烈王无罪释放,也将家产还给了烈王,甚至赏赐黄金万两,以示安抚。
朝廷上下突然分成两派,一派烈王,一派九王爷,自然,摇摆不定的也大有人在。
奇怪的是,烈王自从被释放出来以后,闭门不出也不参政,皇帝没有诸多表示,却也不强制他参与,只下了道旨,让烈王安心静养再无其它。
九王爷依然在人前保持温和作风,见人含笑,如沐春风。
朝廷之上,千变万化,风起云涌。
过了几日,烈王一身黑袍回到朝堂之上,与九王爷并肩立于皇帝左右,皇帝脸上才有了少许欣喜之色,朝臣们心中这才踏实了许多,都说烈王守的云开见明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子矜的肚子愈加大了起来,加上牢内饭食并不怎样,虽然安王暗中托了人照顾,终是他们能力有限,饭食往往被克扣,又行动不便,有了身孕往往嗜吃,大部分时间却只能空腹忍耐,本来应该发胖的子矜迅速瘦了许多。
安王还好些,他是皇子,又在军中极具声望,狱中的人自不敢怠慢,只是,他担心子矜,生怕有什么意外,却只能在牢中无力等待,这对办事一向事事顺风的他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煎熬。
“吃饭了!”
牢内又响起狱卒的吆喝声,铁栏杆内出现一碗一筷,发焦的米饭上零星盖着几片菜叶,刺鼻的糊味充斥着整个感官。
子矜艰难的翻身下床,缓缓挪动身体,弯腰将那碗筷端起来,望了一眼,咬着牙将米饭往口里送。
她不怕的,小的时候这种苦不是没有吃过,只是,苦了她腹中的孩子,她小时候受的苦,绝不能让她的孩子也受这种苦。
握紧了拳,她痛苦的吞咽。
为了孩子,为了他,她也要好好活着。
腹中突然传来一阵抽痛,“啪”的一声,手中的碗掉到地上,她痛苦的弯下腰,仿佛感受到腹中的孩子一点点的流失,她恐慌的去捂住腹部,腹部越来越痛,发丝被汗水打湿,腻腻的粘在额上。
不要,她的孩子……
子矜感到没有来的无助,手指紧紧地抓住冰冷的栏杆,泛着骇人的白。
耳旁空隆隆一片,嘈杂的,混乱的她都感受不到,她只感到腹部的痛,那痛让她无法呼吸,心也痛起来。
“哐”的一声,似乎牢门被打开,一个怀抱紧紧拥住她,有力地掌握住她的肩,他在她耳畔焦急的低喃:“子矜,子矜……”
那声音将她从痛苦中拉出来,汗水流下脸颊,打失了浓密的睫毛,她蹙着眉,朦胧得睁开眼,一个与安王有几分相似的脸出现在眼前。
“殇……”
她死死的抓住他,指甲只掐进他的肉里,眼中雾气浓浓,她焦急地望着他,仿佛抓到一棵救命草:“孩子……殇……救救我们的孩子……”
失了力气般,她昏死过去。
“子矜!”
烈王的身形微僵,他紧紧抱着她,癫狂的朝身后怒吼:“还不去找大夫。”
他身上带着一种骇人的邪气,黑色的衣冷的仿佛杀人不眨眼的酷吏。
狱卒只吓的踉跄后退,闻声慌忙的向外面跑去。
“子矜,我在这,殇在这,你好好的,你……腹中的孩子也好好的。”
他拥紧她,语无伦次。
牢内的油灯静静的燃着,昏黄的光晕打在冷硬的墙面上,难得的温暖。
床板上的人脸色苍白,薄薄的被子盖住她纤细的肩,眼眸死寂的抿着,没有一丝生息。
牢外,烈王阴沉着脸站着,提着药箱的大夫一个劲地擦汗。
“到底怎样!”
烈王冷声低喝。
“这个……”大夫在一次用帕子擦了擦额头,小心的措辞:“孩子暂时保住了,只是王爷您看这种环境,那女子需要精心调养,再这样下去孩子是绝对保不住的。”
烈王目光一冷,挥了挥袖,冷冷吐出一个字:“滚!”
那大夫却视这个字如获至宝,忙拎了箱子,踉跄的跑出去。
烈王放轻脚步走进去,扫到她苍白消瘦的脸颊,心如针扎,小心的坐到榻旁,抬手想为她拂去发丝终是停滞在半空。
“你放心,我会帮你。”
他望着她低声说着,为她盖好了被子,对手下嘱咐了几声,起身出去了。
混沌寒冷的牢内,一个修长沉稳的身影卓然而立,仿佛是竹笋中唯一挺拔的绿竹,酌亮闪耀,让人不可忽视。
纵使穿着囚衣,依然玉树临风,不减往日风采。
烈王停住脚,遥遥的望过去。
安王也在牢内看着他,黝黑的眸子在日渐消瘦深邃的眼眶中灼灼如星。
微微迟疑,烈王终究走了过去。
“她怎样?”
安王最先开口,声音沙哑的厉害,透出他内心的煎熬与担忧。
烈王看他一眼,皱了皱眉,才道:“孩子保住了,可她,不是很好。”
安王的身体猛然僵直,眼眸似海。
烈王低着头,看到他身上的囚衣,嘴角邪邪的勾起来:“现在你也变成这个样子,我本来应该很高兴,可是,我高兴不起来。”
他转过身,背对他:“我回去求父皇,接子矜到我府上修养,到时候,她一感动,能忘了你也说不定。”说着,他低低笑起来,举步离开。
“四弟。”
安王沉声唤他。
烈王猛地停住脚步。
“谢谢你!”安王勾起嘴角,会心地笑起来。
他的身体陡然僵直,冷哼一声,拂袖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