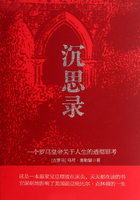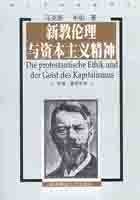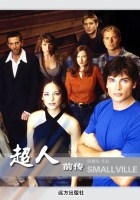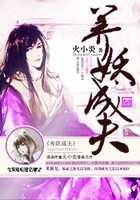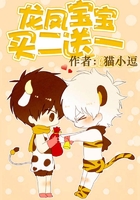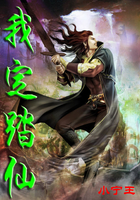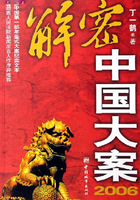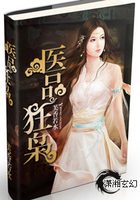罗钦顺在理气论上赞成程颢的理气浑然一体而反对程颐、朱熹的理气为二,但在心性论上,却赞成程颐、朱熹,因为他主张“理之所在谓之心”。这里把心主要看做盛贮、显现性的器官,它本身是灵明的。“心之所有谓之性”是这一意思的反说。“理之所在谓之心”意在强调,人
的受伦理原则支配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质及由此产生的观念形态才是人的根本规定和本质属性。人从禀气受生时,就被赋予了这一本质属性。这是被给予的、先天的、无法拒绝的。这一本质属性必定要表现为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质。所以心和性不离不杂。心性
之别,在具有了一定的学问功夫后才能见得真切。心性之别甚微妙,稍不清晰,便谬以千里。
罗钦顺关于心与性的界说,是与程颐、朱熹基本相同的。他所说的“虚灵知觉,心之妙也;精微纯一,性之真也”(《困知记》第2页)正是朱熹关于心性的基本思想。罗钦顺又说:“至精者性也,至变者情也,至神者心也。”(《困知记》第2页)在性情关系上,罗钦顺认为,性即所谓“道心”,情即所谓“人心”,这里道心人心之说,亦沿用了朱熹《中庸章句》中的说法。朱熹所谓道心,是领受了义理的心;人心,是领受了耳目之欲的心。罗钦顺虽援用朱熹的道心人心概念,但意义却不同于朱熹。关于道心人心之分,罗钦顺说:
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言两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困知记》第2页)
这里,以人心为动,道心为静,人心为用,道心为体。就是说,“未发是道心,已发是人心”。动静是表示心的状态的范畴,体用是表示心的层次的范畴,而道心人心却是表示伦理意义的范畴。把这二者等同起来,就是表示,在罗钦顺看来,心在未发时,在静时是体,是天理,在已发时,在动时是用,是有理有欲。而按照体用这对范畴的原意,没有不表示为用的体,也没有无体之用。体为道心,为天理;用为人心,为人欲。这是矛盾不通的说法。罗钦顺在心性论上的漏洞为后来刘宗周、黄宗羲所指摘,同时的王阳明对这种观点也有批评。如王阳明《答陆原静书》云:
未发之中即良知也,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有事无事可以言动静,而良知无分于有事无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动静,而良知无分于寂然感通也。动静者,所遇之时,心之本体固无分于动静也。理无动者也,动即为欲。循理则虽酬酢万变而未尝动也,从欲则虽槁心一念而未尝静也。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又何疑乎?(《传习录》中)
罗钦顺以动静体用分天理人欲,这是他的理论中不如王阳明通透的地方。
但罗钦顺在后来思想发展中,对前期关于理与欲、道心与人心的思想有所修正。他说: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程子此言本之《乐记》,自是分明。后来诸公往往将人欲二字看得过了,故议论间有未归一处。夫性必有欲,非人也,天也;既曰天矣,其可去乎?欲之有节无节,非天也,人也;既曰人矣,其可纵乎?(《困知记》第90页)
这里是说,所谓人欲,即人天生就有的欲望,既然是天生的,就不能尽去,只能加以合理节制,勿使放纵。合理的人欲即是天理,人人所同,不可无也。这一意思,他在对陆九渊理欲论的批评中也申述过:
夫人之有欲,固出于天,盖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当然而不可易者。于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当然之则,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纵欲而不知反,斯为恶尔。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为言,盖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严,但语言似乎偏重。(《困知记》第28页)
罗钦顺这一修正,显然有见于理学末流以人心之欲望为恶,试图据儒家先贤之说,给人的欲望一个合理的位置,不一概斥之为恶而克去。他的愿望是求人的欲望的合理满足,以理制欲。但他承认《礼记·乐记》中“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以动静分性情,已开性静情动、性善情恶的衅端。罗钦顺虽惩王学末流偏重之言,但他未能指出《乐记》这一段话理论上的纰漏,也未能指出由性静情动到性善情恶逻辑上的跳跃。这已为他理气论与心性论的矛盾埋下伏笔。而他对“十六字心传”的解释:“道心,寂然不动者也,至精之体,
不可见,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变之用,不可测,故危。”(《困知记》第1页)确乎以动静体用分微危,与他所指斥的偏重之言已难分辨了,这一点正是后来黄宗羲所极力反驳的。罗钦顺服膺朱熹“理一分殊”之说,以之为性命论的指导原则,他曾说:
理一分殊四字,本程子论《西铭》之言,其言至简,而推之天下之理,无所不尽。在天固然,在人亦然,在物亦然;在一身则然,在一家亦然,在天下亦然;在一岁则然,在一日亦然,在万古亦然。(《困知记》第9页)
就是说:“理一分殊”可以解释往古来今天地人物一切道理,无所不通。他用理一分殊来阐发他关于性命的主张。在罗钦顺,性指宇宙根本之理在人、物之上的体现,命指这种体现的不容选择,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与个体因不同遭遇而有的差异的必然性。性多自主体言,命多自客体言。性命之理,概括起来就是理一分殊,它可以说明事物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罗钦顺说:
窃以性命之妙,无出理一分殊四字。……盖人物之生,受气之初,其理性一。成形之后,其分则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为性命之妙也。(《困知记》第7页)
这是说,人物禀受了相同的理,本有相同的性,在人物的形成过程中,受各自所处条件的影响,有了彼此不同的面貌。而这种不同是自然而然的,非有一物主宰其间,这就是各自的命。理一就在分殊中,性就在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善与性有善有恶之说都是有根据的。性善说自理一言,性有善有恶说自分殊言。人不能不禀受天理,故不能无性;不能不禀气而生,故不能无命。罗钦顺反对把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并列,他指出,说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二种性是错误的。因为天命之性必表现于气质,天命之性无独立自存的可能。故说天命之性
时,就已逻辑地包含着气质之性了,并非气质之性别为一性。他说:“但曰‘天命之性’,固已就气质而言之矣;曰‘气质之性’,性非天命之谓乎?一性而两名,且以气质与天命对言,语终未莹。”(《困知记》第7页)这里他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就气上认理”的原则和程颢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来立论的。本然之性无独立自在的性质,故不容说,说得出来的都是包含在气质中的本然之性。
严格说,“包含在气质中的本然之性”已有二之之嫌。所以罗钦顺反对朱熹对气质之性的解释:“气质之性即太极全体堕在气质之中。”既言堕,则未堕时自为一物,这里与“就气上认理”、“理气无缝隙”的原则相抵触。朱熹的理一分殊是要说明宇宙根本法则(理一)与它的不同体现(分殊)的关系。这个命题实际上是个伦理意义的命题,它中间包含的实然的物理意义很弱。“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是说人物皆含有宇宙根本法则,但因万物所禀受的气不同,这个宇宙根本法则在具体事物上的表现亦不同。如同清水,盛在黑碗中人看到的是一
样色,盛在青碗中人看到的又是一样色。朱熹在理一分殊的解释上所持的根本观点是“理同气异”,但朱熹在说明万物实然的物理上的差异时,是用气禀不同,即气的厚薄清浊去说明的。这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不能说朱熹理论有矛盾。理一分殊、理同气异在朱熹的理论体系
中是统一的,但他视万物中的理为同一的、绝对的“理一”的不同表现,这就难以避免理、太极独立于气、阴阳而别为一物的嫌疑。罗钦顺在理气论上主张“就气认理”,而在心性上却又同于朱熹的理一分殊,承认分殊之前有理一。这在罗钦顺的理论体系中是非常突出的矛盾。
这个矛盾在他阐释程颢“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一段时表现得很明确,罗钦顺说:“人生而静,即未发之中,一性之真,湛然而已。”(《困知记》第20页)就明显地认性理为一物,有离于形气独立之时,和他就气上认理的原则已不能归一。
罗钦顺的理气论和心性论之间的矛盾刘宗周即已看出,他在关于罗钦顺的评论中说:
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犹之理与气;而其终不可得而分者,亦犹之乎理与气也。先生既不与宋儒天命、气质之说,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谓“理即是气之理”,是矣,独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于一分一合之间终有二焉,则理气是何物?心与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间既有个合气之理,又有个离气之理;既有个离心之性,又有个离性之情,又乌在其为一本也乎?(《明儒学案》第10页)黄宗羲承乃师之义,在《明儒学案》关于罗钦顺的案语中,对罗钦顺也有意思大致相近的批评:
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第先生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相矛盾。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人受天之气以生,只有一心而已,而一动一静,喜怒哀乐,循环无已。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感应纷纭,历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谓性也。初非别有一物,立于心之先,附于心之中也。(《明儒学案》第1109页)
刘宗周、黄宗羲以上对罗钦顺的批评有相当的道理。一个有体系的思想家,他的理气论与心性论应该是统一的,他的心性论应该是他的理气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罗钦顺所谓理,是气的条理,气的运行规律,千头万绪,纷纭胶葛而不乱者。他所谓性,也应该是情的适宜,千头万绪,感应纷纭而历然不昧者。宇宙实体统一于气,人的伦理活动统一于心。也就是说,根据他的理气论,他的心性论应是如后来戴震所谓情之不爽失者。罗钦顺把“理一”作为人人共有的东西,把“理一”在各各不同的气质中的表现作为人与人、人与物区别的根据。这就势必导致理在气外别为一物的结论。按罗钦顺的理气论,世间万物的不同,应是由禀气的不同而有理的不同,即“气异理异”,而罗钦顺的心性论却是“理同气异”。实际上,关于人物同异,程颐、朱熹已有气异性异之说,罗钦顺已看出这一点。他也认为,程颐既主理一分殊,又主张人的才能的不同源于气禀,这二者是矛盾的。罗钦顺说:“伊川既有此言(指理一分殊),又以为‘才禀于气’,岂其所谓分之殊者,专指气而言之乎!”(《困知记》第9页)这里,他已指出程颐理一分殊之论不能一贯。而罗钦顺自己则因理一分殊而放弃了气异故理异之说,同样未能一贯。
罗钦顺之所以出现这一矛盾,是因为他试图把孟子和告子、大程和小程、朱熹和陆象山这两样性质和趋向根本不同的学说统合起来。他试图克服朱熹以理为根本范畴,以理统气的学说,但在心性论上又沿用了《礼记·乐记》、《中庸》及朱熹的学说。他试图吸收陆象山的“心即理”,使“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这一命题表达一种圆融的意思,但又吸收朱熹、《礼记》等分言动静、体用、中和的说法,屏除了陆象山合形上形下体用动静为一,而皆统一于心的学说。他在理气论上试图返回张载,纠正朱熹,但他的心性论又大体上追随朱熹。罗钦顺的哲学是在王阳明心学盛行的背景下,试图既纠正王阳明心学又避免程颐和朱熹理气论的矛盾所作的努力。
三对佛教和心学的批评
罗钦顺之学,早年由禅学入,从“庭前柏树子”话头得悟,又以所悟参证永嘉玄觉的《禅宗证道歌》,觉得甚有收获。但自官南京国子司业后,逐渐摒弃佛学,归本孔孟,晚年抨击佛教甚力。从《困知记》辩论的内容来看,罗钦顺曾经读过《金刚经》、《心经》、《楞伽经》、《华严经》等佛教重要经典及禅宗史传,于佛家名相如心、意、识等亦多有辨析,其用力之深可知。罗钦顺对佛教的批评集中在斥佛教以心为性,以性为觉,觉外无余事,抛却格物致知功夫等方面。
罗钦顺认为,儒释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性”这一重要范畴的理解不同。他说:
夫佛氏之所谓性者,觉;吾儒之所谓性者,理。得失之际,无待言说。然人物之生,莫不有此理,亦莫不有此觉。(《困知记》第33页)
佛家最重要的概念是“性”,此“性”又叫“佛性”。罗钦顺指出,佛教所谓性,内容即觉,觉即能悟解的本性。佛家所谓“人与物皆具佛性”,是说人与物皆具有能觉悟的本性。就人而论,“一阐提皆得成佛”;就物而论,“青青翠竹,都是般若,郁郁黄花,无非佛性”。佛家义理以此为最根本。性是佛家所谓人人物物皆得成佛的内在根据,是佛教全部理论的基础。罗钦顺认为,佛家所谓性,没有儒家“仁”的内容。程颐、朱熹皆主“性即理”,此理是事物的条理、规律,同时也是伦理法则;理既是科学认识的对象,又是伦理认识的对象,二者二而一,一而二。佛家所谓性既无理的内容,所以佛家抛弃穷理尽性,抛弃天地之化育和人伦之仁义礼智。这是儒佛最大的区别。罗钦顺同时认为,天下物既有理又有觉,儒家重在认识理,佛家则遗却理而专求觉。罗钦顺说:
千圣相传,只是一理。……盖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则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后理之一者可见。既有见矣,必从而固守之,然后应酬之际无或差谬。此博约所以为吾儒之实学也。禅家所见,只是一片虚空旷荡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与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识其至精至微之状为何如,而顾以理为障。(《困知记》第84页)
儒者追求的是理,此理是“理一分殊”的。万物根本之理是一,此理一表现于具体事物之上为分殊之理。儒家见得此理,以诚敬涵养,变为自己修身应物的准则。穷理与涵养,博与约,是儒家实学。而佛家所追求的,是“空”,守一空字为养性之术,不但不穷理,反以理为守空之障。罗钦顺就此批评说:
《大学》之教,不曰“无意”,惟曰“诚意”。《中庸》之训,不曰“无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门,积德之基,穷理尽性必由于此,断断乎其不可易者,安得举异端之邪说以乱之哉!彼禅学者,惟以顿悟为主,必欲扫除意见,屏绝思虑,将四方八面路头一齐塞住,使其心更无一线可通,牢关固闭,以冀其一旦忽然而有省。终其所见,不过灵觉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实未尝有见也。安得举此以乱吾儒穷理尽性之学哉!(《困知记》第81页)
罗钦顺对于佛教的批评,由性之内容延伸到觉的方法。他指出,佛家讲“无意”、“无念为宗”、“心如虚空”,目的在悟。在禅宗,“一悟即是佛地”,心地空明、中无一物的状态,即是佛的境界。一切修养功夫,目的都在获得这种境界。为了获得和保持这种境界,要“于念而无念”,闭锁感官与心灵的通路,这样,心中所见,无非空明。此即罗钦顺所说“灵觉之光影”。儒家虽也讲无意,但此无意是不有私意,不有先入主见,保持心的廓然大公,并非一切念头皆不起。儒家的无意,实际上是诚意。诚意的目的,不是得到虚灵之光影,而是作为穷理尽性的
基础。通过穷理尽性,内以完成圣贤人格理想,外以赞天地之化育。这是儒佛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