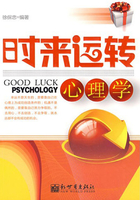唐末五代间,南岳一系又分出沩仰、临济两宗,青原一系分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合称禅宗五家,也称五宗。慧能禅宗是中国佛教中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宗派。
慧能禅宗的基本著作是《坛经》,此经系慧能在韶州大梵寺为大众说法,后由门人法海整理而成。《坛经》的中心思想是注重净性,强调自悟,提倡顿教。他说:“我于忍(弘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伍(悟),顿见真如本性。……今学道者顿伍(悟)菩提,各自观心,令自本性顿悟。”(敦煌本《坛经》)又说:“如是一切法,尽在自姓(性)。自姓(性)常清净。日月常名(明),只为云盖覆,上名(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参罗,一时皆现。世人性净,犹如清天。……忘念浮云盖覆,自姓(性)不能明,遇善知识(善于开导使人悟入佛道者)开真法,吹却名(迷)妄,内外名(明)彻。于自姓(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在自姓(性),名为清净法身。”(同上)这是说,人的本性本来清净,具有先天的智慧,只是因为一向被妄念的浮云所盖覆,所以未能自悟。
只要得到善知识的开导,灭除妄念,就能内外明彻,顿见真如本性,自成佛道。所以,慧能又说:“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敦煌本《坛经》)迷悟是一念之差,本性只要一念相应,众生自我认识本心,就能成佛。成佛并非另有佛身,自性就是佛。这就把心外的佛变成心内的佛,把佛变为举目常见的平常人,或者说把平常人提高到与佛相等的地位。这也就是所谓“见性成佛”或“顿悟成佛”的学说。
慧能禅宗主张不立语言文字,教外别传,不仅和包括神秀北宗在内的以往禅学不同,也和中国其他佛教宗派不同,更和印度佛教有别。如此特殊的佛教宗派,却在中国佛教史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这显然是和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以及禅宗自身的宗教哲学思想及其简易明快的方法直接相关的。
三、宋元明清佛教的哲学思想唐代以后,佛教总的情况是高潮已过,大势已去,开始转向衰落了。在宋元明清时代,佛教的各个宗派以及佛教在不同地区的发展变化并不平衡。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主要是禅宗还在流传,其次是净土宗,此外,天台宗、华严宗曾一度中兴,律宗等也余绪未绝。宋代以来,佛教各宗的界限愈来愈模糊了,佛教学者虽以某某宗相标榜,实际上往往是诸宗思想的融合者。这也是区别于唐代佛教的最大的思想特点。
禅宗。慧能禅宗的根据地在南方山区,受当时政治冲击较少,在五代时继续有较大的发展。
法眼宗创始人延寿(904—975)主张禅教兼重、性相融合,他曾约集天台、华严、法相唯识诸宗的佛教学者,就佛教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并以禅宗的观点进行折中。他还广泛征引300多种文献资料,编成长达百卷的巨著《宗镜录》,以肯定禅教一致的主张。宋初,禅宗不同流派发生重大变化,五家中的沩仰宗已不传,曹洞宗和法眼宗也都委靡不振,而临济宗和云门宗却盛行于各地。北宋时临济宗人楚圆门下慧南和方会在江西分别开创了黄龙和杨岐两派,和原来的临济等五家合称为“七宗”。至南宋,黄龙派趋于衰落,杨岐派成了临济宗的正统。杨岐派大慧宗杲提倡“看话禅”,即把前辈祖师用以判断是非迷悟的言论(“公案”)中的某些语句当作“话头”(即题目)来进行内省式的参究,影响久远。云门宗人雪窦重显著《颂古百则》,一度大振宗风。又灵隐契嵩(1007—1072)一反当时禅教一致的常见,重新强调教外别传。同时,又作《辅教篇》,竭力调和佛教和儒家的矛盾。云门宗至南宋时代又趋于衰微。此外,曹洞宗人正觉与宗杲交谊颇深,但因反对“看话禅”,提倡静坐看心的“默照禅”,而引起与宗杲的彼此非难,互不相下。此后,禅宗在学说思想方面也就趋于停滞了。
天台宗。唐会昌灭佛以来,天台宗典籍散失。五代时,吴越王钱弘遣使高丽访求天台宗教典,后得智的大部分著述和若干论疏,由此典据大备,推动天台宗在江浙一带呈中兴的气象。宋代天台宗人知礼和庆昭、智圆争论智《金光明玄义》广本的真伪问题,而分为山家(本宗)、山外两派。后来知礼一系的山家派影响超过山外派,代表了天台宗,流行于南宋、元代。在明代,智旭为天台最后的一大家。
华严宗。唐会昌灭佛后,华严宗一直比较沉寂。至宋初,长水子璿继承唐代宗密一系的教禅一致的思想,重兴华严学,弟子有净源等。后来高丽王子义天来华师事净源,带来了散失在异域的唐代华严宗人的大量章疏,极大地帮助了华严宗的复兴。到了南宋,华严宗也比较活跃。宋以后,华严宗的典籍仍为一些佛教学者所重视,但此宗流传的势头是愈来愈衰弱了。
中国佛教哲学发展到唐代,已达到了顶峰。但是在宋代,由于当时从海外陆续返流回来已经散失了的天台、华严二家著述,也由于在衰落中图求佛教生存的需要日益迫切,又激发了一些佛教学者研究的兴趣,从而使佛教哲学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宋元明清时代,佛教哲学思想最可注意者有三:(1)心性问题为哲学理论的核心;(2)各宗的融通趋势;(3)调和儒、道思想的鲜明倾向。
宋代以来,佛教各宗和宋明理学遥相呼应,都重视心性问题,如禅宗讲自性,华严宗讲真心,天台宗重观心等,并且愈来愈用“自心”来统一佛教各派,调和儒佛道三教。入宋以来,佛教内部在理论上的主要争论是真心观妄心观和性善性恶两个问题。前面提到的天台宗山家、山外两派之争,是以智的《金光明玄义》广本的真伪为争论的起点,而争论的中心是观境的真心、妄心问题。山家派主妄心观,认为所观的境是妄心,即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因为此派认为真如本体和“无明”(无知)是众生无始以来就具有的,心一定意义上说是妄心,妄心呈现出外境,所以,观心是把所要观的道理集中在心上来观,以求悟解。山外派主真心观,认为所观的境是真心,即真如本体。因为此派认为真如本体随缘而变为各种现象,现象的真实(实相)就是真如,也就是真心,所以要观现象的实相,应当直接观之,不必经过观心。山外派认为,所谓观实相,就是观真心,而山家派离开实相以观心,只能是观妄心而已。山外派的观点接近华严宗的缘起论,山家派批评山外派,反映了捍卫天台一家宗义、贬低华严理论价值的倾向。就哲学思想来说,天台宗两派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天台宗和华严宗在万物缘起理论上的某些差别。
关于性善性恶问题,唐代天台宗人强调性是先天具有的,有善有恶,佛的心也如此。这种观点影响颇大,不仅天台宗学者,如宋代知礼(960—1028)继续坚持这种观点,认为众生的本体真如本来具有愚痴无知的“无明”,是众生生死轮回的基因,而且一些禅宗学者也赞成这种观点,如五代宋之际禅宗法眼宗人延寿,深受天台宗的影响,把先天具有的性和后天行为的修分为善恶两种,认为佛和一阐提都有善性和恶性,只是后天行为有所不同。他说:“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万善同归集》)这种理论和唐代以来儒家的性三品说与灭情复性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是符合当时思想统治的需要的。同时,这种佛和一阐提都有善性恶性的说法,对于生活在苦难中的广大人民,也确实具有较大的思想吸引力。
自唐代后期起,中国佛教各宗派的融通趋势愈来愈显著,大体上先是禅教相互融通,次是各宗分别与净土宗相合一,再是以禅净合一为中心的各派大融合。率先大力消除禅教对立的是唐代宗密,他强调佛内心的意向(“禅”)和佛言说的教义(“教”)是完全一致的。宋代延寿对于禅宗学人空疏不通教理、指鹿为马的现象深感不安,强调“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宗镜录》)他为统一各宗学说而编定的巨著《宗镜录》,对尔后影响颇大。“明代四高僧”即佛教四大师袾宏、真可、德清和智旭,也都是兼修各宗学说于一身的人物。如智旭(1599—1655)说:“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不于心外别觅禅、教、律,又岂于禅、教、律外别觅自心?如此则终日参禅,看教,学律,皆与大事大心正法眼藏相应于一念间矣。”(《灵峰宗论·法语三》)把禅、教、律三学融通并归于一念,正是后期佛教趋于诸宗合一的历史演变的典型表现。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大体上一直处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附庸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调和儒道思想的倾向也愈来愈明显了。北宋天台宗学者智圆(976—1022)自号“中庸子”。
他宣称自己晚年所作是“以宗儒为本”,因为“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而“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中庸子传·上》)这里包含了把儒置于释之上的倾向。又如契嵩作《辅教篇》,宣扬“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辅教篇·中》)。孔子和释迦牟尼都是圣人,儒和佛都是为了使人向善,因而是一致的。他作《孝论》十二章(《辅教篇·下》),系统地论证了佛教和儒家孝道的关系,竟说佛教最重孝,“孝为戒先”。他撰《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的中庸之道。契嵩认为许多道理“皆造其端于儒,而广推效于佛”(《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实际上是把佛家理论归结为儒家学说。明代佛教四大师也都提倡儒佛道融合。袾宏(1535—1615)宣扬“儒主治世,佛主出世”(《云栖法汇·手著》),并认为佛教可以“阴助王化之所不及”,儒教可以“显助佛法之所不及”,儒和佛可相互辅助,相得益彰。真可(1543—1603)认为儒佛道三家是“门墙虽异本相同”。德清(1546—1623)撰有阐发儒与道的思想的多种著作,竭力调和儒道佛三教,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梦游全集·说·学要》)他宣扬“孔、老即佛之化身”,实是以儒和道代佛。智旭也著《四书蕅益解》、《孝闻说》、《广孝序》等文,大力赞扬儒家思想。他还提出三教同源在于“自心”的观点,说:“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灵峰宗论·金陵三教祠重劝施棺疏》)“三教圣人,不昧本心而已。”(《灵峰宗论·法语三》)“自心”即“本心”,是三教的共同的根本。智旭就这样把三教安置在“自心”基础上而使三者统一起来了。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佛教后期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