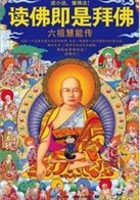四、密教的哲学思想大约公元7世纪至12世纪是密教时期。由于大乘佛教倾向于烦琐的空洞的理论论证,难以为一般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再者,此时印度教又日益兴盛,佛教为了争取群众,便采用印度教的方法,使佛教和印度教以及当地流行的迷信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为新的教派——密教。其所以称为密教,是因为主张身、语、意三密相应行,以求得出世的果报。也就是双手做各种姿势,手结契印,这种手势,称为“身密”,口诵真言咒语密宗通常用“、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这是祈求往生极乐世界所唱念的六个字。密宗宣传信徒常念此六字真言可以超脱生死轮回。六字中的“”字,被视为真言中最为神圣、魔力最大的一种,密宗说此字最能与佛相应、相通。,称为“语密”,心作观想,称为“意密”,三者相应,“即身成佛”。密教以咒术、仪礼、粗俗信仰为特征,哲学思想贫乏。它的主要哲学思想是“六大”缘起说。
它宣传宇宙的本体和现象二而为一,两者都由“六大”(地、水、火、风、空、识)所构成,宇宙万有都是“六大法身”的显现,而“六大法身”就是佛的真身,也就是说,宇宙万有都是佛的化身、产物。印度佛教哲学最后就以这种极度的神秘主义说教宣告了它的历史的终结。
§§§第二节中国佛教哲学略史
中国佛教哲学是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而后形成的一种宗教哲学。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主要是儒家的思想,再是道家、玄学家的思想以及原有的迷信观念等,相接触、击撞、斗争、融合,导致自身的不断改造、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质的新学说、新体系。这就是说,中国佛教哲学是既吸收了印度佛教理论,又摄取了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并对其加以融合改铸而形成的新思想。它既有别于印度的佛教思想,也不同于中国的儒、道等固有思想;同时它又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哲学而注入于中国哲学思想洪流之中,从而又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部分。
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方面。中国佛教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阶段,这是佛教由传入到日趋兴盛的阶段;二是隋唐阶段,这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哲学最为繁荣的时期;三是宋元明清阶段,这是佛教日趋衰落的时期,也是佛教哲学被吸收于理学之中,与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等融会的时期。下面我们按照上述三大阶段,略述一下中国佛教哲学的历史演变。
一、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佛教的哲学思想佛教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此后直至整个三国时代,佛教的流传都还是微弱的、缓慢的。
它起初只在皇室宫廷的狭小天地内获得信奉,到西晋时才逐渐推及于民间。此时佛教的主要活动是译经,着重译出的是禅经和般若经。相应地流传的佛教主要是两派:一派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一派是以支谶(支娄迦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即空宗学说。前者偏重于宗教修持,标榜默坐专念,构成所谓“心专一境”的精神境界。后者则偏重于教义的研究和宣传,以论证现实世界是虚幻的。由于汉代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流行,中国人往往视佛教和黄老之学为同类,禅学被看作学道成仙的方术之一。如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传》),就是把黄老学说和佛教学说等量齐观。东汉时期佛教是在与道术方士思想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东晋十六国时代,南北分立,长期战乱,社会动荡不安,这就为佛教的滋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与以往的缓慢发展情况不同,此时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佛典的大量翻译,中国僧侣佛学论著的纷纷问世,般若学不同学派的相继出现,民间信仰的日益广泛和深入,由此而汇合成中国佛教的第一个高潮。
东晋十六国时代,在佛教哲学上有着不同程度建树的主要是道安和慧远、鸠摩罗什和僧肇。最重要的佛教哲学思潮,一是般若学的“空”论——这样那样否认事物的真实性的思想,二是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
般若学“空”论思潮,集中地表现为“六家七宗”的形成和僧肇“不真空论”的建立。自东汉末年支谶传译《道行般若经》以来,西晋东晋的佛学理论的主潮是般若性空学说。由于《道行》、《放光》、《光赞》诸本般若经的文义并不十分畅达,而魏晋又盛行有无(空)之辩的玄学,以至于佛教学者往往以玄学的观点去理解和阐释《般若经》的思想,对《般若经》所谓“空”的意义理解不一形成了“六家七宗”:(1)本无家——道安主张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竺法深、法汰也说从无生有,万物出于无。(2)即色家——支道林主张即色空,“色”指物质现象。就是说,物质现象没有自体,本性是空的。(3)心无家——主张对外物不起执著有无之心。(4)识含家——于法开谓世界万物都是妄惑的心识所变现。(5)幻化家——道壹认为世界万物都如幻如化,是不真实的。(6)缘会宗——于道邃认为世界万物都由因缘和合而生,都无实体。又因在以上六家之外,本无家分化出竺法深的本无异家,故还合称为“七宗”。“六家七宗”就其基本观点来说,主要是本无、即色和心无三家。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般若学流派实际上是魏晋玄学不同流派的变相。般若学正是在与玄学的结合中得到广泛传播的。
般若学“六家七宗”的形成,反映了中国佛教哲学前进的足迹,但它并不完全符合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正统观点。鸠摩罗什系统地译出了《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等般若佛典后,他的高足僧肇(384—414)在充分理解、把握般若学经论原义的基础上撰写了《不真空论》等文,准确地阐发了空宗的要义。僧肇集中批评心无、即色和本无三家,指出心无家是“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肇论·不真空论》),就是说,心无家正确的方面是主张主观精神(心)的清静空寂,错误的方面是在外物虚无的问题上,没有懂得“不真空”的道理,没有真正否认外物的存在。他批评即色家说:“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肇论·不真空论》)意思是说,所谓物质现象,应当自身就是有物质性的,何尝是把物质性的自体赋予物质现象后才算是物质现象呢?即色家只说物质现象没有自体,而没有认识到物质现象本身就是非物质性的。僧肇对本无家的批评是:“本无者,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亦无。寻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同上)这是说,本无家过于偏重无,在言论上抬高无的地位,非有是无,非无的无还是无,寻求佛教圣者立言的本旨,是讲非有不是真有,非无不是真无,何必说非有就没有这个有,非无就没有那个无呢?僧肇认为本无家把有和无的相即关系变成相离关系,进而过于强调无,是错误的。他以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也就是“非有非无”,或者说“非真有非真无”,这便叫做“不真空”。所谓“不真空”,就是说万物没有真实性,但不是不存在,万物是虚妄不真而空,是不真的存在。僧肇的“非有非无”的“不真空”论,既是对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的批判总结,也是对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辩的批判总结。此外,僧肇还针对人们通常认为万物不断运动的观点,撰写了《物不迁论》,阐述了动静观,强调“动静未始异”,主张“即动而求静”。他还作《般若无知论》,指出有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智慧:一种是“圣智”,即圣人(佛)的智慧认识,叫做“般若”;一种是“惑智”,是一般人迷惑于事物的本性而产生的荒诞认识。
所谓般若无知就是无“惑智”,就是洞照无相的真理而无所不知。实际上就是非通常认识的神秘主义直观。由于僧肇的文章在自然观、动静观和认识论方面蕴涵深邃精巧的唯心主义思辨,因此也就把当时的般若学中观学说推向了新的高峰。
宣扬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道安的高足慧远(334—416)。慧远是东晋后期的佛教领袖,他隐居江西庐山30多年,聚徒讲学,撰写文章,阐发佛教哲学思想。他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和《三报论》,是几篇比较重要的佛教哲学论文,着重论证和发挥了佛教教义的基本问题——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
慧远根据印度佛教的业报轮回的学说,吸取我国原有的信仰观念,但又和我国古代由上帝司善惩恶,从外面主宰人的命运的说法不同,直接从人自身的主体活动中建立因果报应说。他说:
“三业体殊,自同有定报。”(《三报论》)“业”,指身、口、意三方面的活动。“三业”就是指人的行为、言语和思想活动。三业的性质不同,有善、恶和无记三种。无记是指不善不恶、无所谓善恶的活动,可见三业的性质主要是善、恶两种。慧远强调有因必有果,业发生后不会消除,不同性质的业必有不同的报应:“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同上)所谓现报就是今生作业,今生便受报应;生报是今生作业,下一世受报应;后报是今生作业,经数生乃至千百生,然后受报应。由于人们要受报应,人死后就要依据生时所作业的善恶而转生为较高于或较低于今生的东西,这也就是轮回。这样,人的生命就不只是限于现在这一生,还有所谓前生和后生,后生不止是一次而是无数次,所以就有“三生”或“三世”。人有三业,业有三报,生有三世,这就是因果报应说和轮回转生说。慧远宣扬,因果报应和轮回转生是人生的最大痛苦,人应当信仰佛教,努力修持,以超出报应和轮回,求得永远的解脱,获得永恒的幸福。
因果报应理论逻辑地要求阐明一个果报的承受者问题,但是印度早期佛教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含混模糊的。它宣称“人无我”,否定人有一个绝对的永恒的实体,这样,也就逻辑地否认了灵魂的存在。同时,它又宣扬轮回转生的学说,认为人生而复死,死而复生,生生死死轮转不已,这又逻辑地包含了轮回转生的连续性精神实体的存在,从而也等于承认灵魂的存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受中国传统的神不灭思想的影响,一般人都认为灵魂不死不灭是佛教轮回报应说的当然的理论前提。慧远也继承了这种传统观念,进一步论证了神不灭论,为佛教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说充实了理论内容。他说:“夫神者何耶?精极而为灵者也。精极则非卦象之所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言。虽有上智,犹不能定其体状,穷其幽致。”(《沙门不敬王者论》)意思是说,所谓神是一种非常精灵的东西,没有形象,也难以穷尽它的奥妙。神的作用是十分神妙而巨大的,它和情欲密切联系着,推动了人生的轮回流转。慧远宣扬情欲是人生流转变化的原因,精神是情欲的根子。情欲能执著融合万物使之流转变化,精神则借这种流转变化而不断地传递延续。这就是说,精神、灵魂是人生死轮回的主体,是不随人的形体的死亡而消灭的。他还援引薪火之喻来论证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
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沙门不敬王者论》)神可以从这一形体传到另一形体,永恒不灭。慧远的神不灭论和印度早期佛教的理论并不完全一致,和中国传统的神不灭论也不完全相同,是一种和幻想成佛的学说直接相联系的灵魂不灭的理论。这既是对印度佛教业报轮回说的重要发展,也是中国神不灭论的新形态。
南北朝时期继东晋十六国的分立状态,又持续分裂169年,此时佛教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东晋十六国时代主要是出现般若学学派不同,此时随着各类佛典的纷至沓来,专攻某一经论之风益盛,独尊一经一论的经师、论师各立门户,相互争鸣。这些经师、论师虽重师承关系,但并没有传宗定祖的世系,他们是基于对不同经论的理解而形成的学派。在南朝,先是涅槃师代般若学派而出,到梁代涅槃学派盛极一时,同时三论师出,并和成实师各立门户,到陈代三论师更受推重。在北朝以涅槃师、毗昙师、成实师、地论师、摄论师最为重要。从佛教风气的转变和佛学潮流的变化来说,此时最重要的是涅槃学。涅槃学主要是阐发佛性学说。“涅槃佛性”的问题是南朝时代佛教理论的中心问题。当时涅槃学流派之多,佛教史载有12家和13家之别。在由般若学转到涅槃学、由谈“空”转到讲“有”的转折时刻,鸠摩罗什的另一高足竺道生(355—434),早年精于般若,后来盛唱涅槃,“真空”“妙有”,契合无间,独立思索,有所突破,历史地成为了上接般若下开涅槃,宣扬佛性说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道生的学说主要有两方面:涅槃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佛性是指成佛的原因、根据、可能,是所谓成佛的根本前提。晋宋期间一些佛教学者往往把般若学和涅槃学对立起来,以般若的“空”否定涅槃的“有”,以“人无我”否定“佛性我”;也有的学者根据般若学“识神”(承受果报的精神实体)性空的观点,把佛性常住视为因果报应的神明(灵魂)不灭而加以指责。正是在佛教众说纷纭的情况下,道生把涅槃学和般若学调和起来,强调众生都有“佛性我”。他说:“理既不从我为空,岂有我能制之哉?则无我矣。无我本无生死中我,非不有佛性我也。”(《注维摩诘经》)意思是说,“理”(佛性、本体)并不因为“我”这个实在自体而空,难道“我”能制止“理”的存在吗?所以,这种实在自体的“我”是不存在的,是“无我”。但是,“无我”是指由“四大”(地、水、火、风)构成的、有生死的人“我”并不真正存在,而不是没有“佛性我”,佛性这种实在自体是有的。进而他又说,“佛性即我”,“本有佛性,即是慈念众生也”(《大般涅槃经集解》)。众生都有佛性,众生都能成佛。“一切众生,皆当作佛。
”(《妙法莲华经疏》)道生把佛性真我和般若无我统一起来,强调涅槃和生死不二,众生都能成佛,反映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重大变化。
道生在涅槃佛性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独创性的顿悟成佛说。“顿悟”是关于所谓成佛的步骤、方法问题。在中国佛学界,对于成佛的步骤、方法问题一直存在分歧。如上面提到的,安世高一派的小乘禅学主张渐悟,而支谶、支谦一派的般若学则接近于顿悟。东晋时代般若学者对于顿悟又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在渐悟过程中达到一定阶段就获得彻悟,然后再进修就能成佛,这称为小顿悟;另一种认为,在渐悟过程中不能获得彻悟,只有真正悟解佛理、体认本体的时刻,才能成佛。道生正是后一种观点的鼓吹者。这种神秘主义的直观理论、直觉思维,对于尔后的佛教思想和宋明理学都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