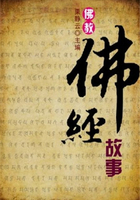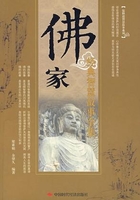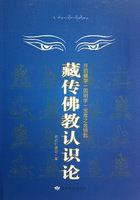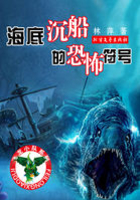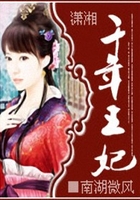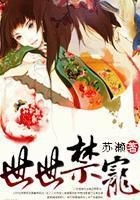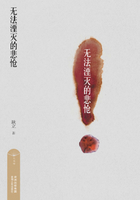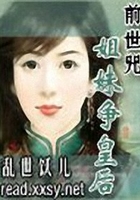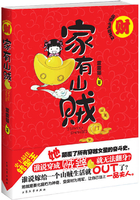上座部就是一些长老的主张,强调严守原来的教义和戒律,属于正统派。大众部是众多僧侣的主张,提出了教义的一些新说和开禁了部分戒律,是比较强调发展的流派。据世友著、唐玄奘译北传佛教《异部宗轮论》载,先是大众部分化出8部,后上座部又分化出10部,共为18部。大众部先后分为一说部、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说假部、制多山部、西山部和北山部。上座部先分化为说一切有部和雪山部(原上座部),说一切有部又分化出犊子部,犊子部又分化出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说一切有部又分化出化地部,由化地部又演化为法藏部。说一切有部还分化出饮光部和说经部。以上派生的18部连同根本二部即上座部和大众部共为20部。关于部派佛教,另据南传佛教史书载为18部,即去掉北传佛教所说的西山部和北山部。此外,部派名称和传承关系也有些差异。20个部派中有些部派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所在地域有所不同而已。在这些众多的部派中,最主要的是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分歧,史称佛教的“根本分裂”。变化最多、分化最快的是说一切有部(简称有部),这表明上座部系统没有也不能长期坚持正统的观念。在哲学思想上最重要的流派是说一切有部和说经部(经量部)。
部派佛教和早期佛教的区别以及部派佛教的内部分歧,表现在宗教实践、宗教理想和哲学理论等各个方面。我们侧重于论述的是哲学思想的演变,同时也兼及其他方面。
在宗教实践方面,由于有些教徒滋生出一种对于部分戒律的违抗,佛教为此曾多次举行结集,专门讨论是否放宽正统的戒律的问题。例如,随着布施范围的扩大,人们对寺院奉献的财物越来越多,原来规定比丘不准接受金银财物的施舍,大众部认为可以受蓄,上座部反对改变,大众部又拒绝服从,并被驱逐或开除,从而分别形成为相对独立的流派。
在宗教理想方面,上座部认为佛陀是历史人物,其所以伟大,主要是由于理想的崇高、思想的正确、智慧的精湛和精神的纯洁。一般人修行的最高果位不是佛果,只能是趋向佛果的阿罗汉,即能达到所谓断尽一切烦恼、不再生死轮回的果位。大众部则倾向于抬高佛陀的形象和人格,他们提出“超人间佛陀”或“超自然佛陀”的理论,吸取和加强神话创作,来烘托释迦牟尼的超凡神圣,并制定一套仪式,对释迦牟尼顶礼膜拜,也就是把佛陀看作超凡的或超自然的存在,是一位离情绝欲、神通广大的真正的“神”。他们还贬低阿罗汉果位,强调阿罗汉还有许多不足。大众部的这种观点,后来为大乘佛教所继承,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哲学思想方面,部派佛教已由早期佛教侧重于人生哲学扩展到宇宙观领域。由于早期佛教对于缘起说的阐述不明确、不彻底,而导致部派佛教内部对轮回流转、业果相续的主体问题和宇宙万物实有假有问题的严重对立。
一般地说,上座部各派偏重于说“有”,也就是认为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是实在的。例如,说一切有部,是部派佛教中最有力量、最重要的一派,所谓“说一切有”,就是承认精神和物质的存在,承认一切存在。从时间观念来说,就是承认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都普遍存在。说一切有部毗婆沙论师坚持认为,人们既然都具有事物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存在的观念,那就证明事物是实际存在的,因为如果事物不存在,人们就没有思想的对象了。再者,按照缘起说,过去的思想行为产生结果,由因而有果,果不能产生于空无,既然因能生果,那就说明因是实在的。由此也就证明过去的因是时时存在、永远存在的。说一切有部承认一切普遍存在的理论(三世实有)是和早期佛教的“无常”观念不一致的,是一种全新的哲学理论。
从说一切有部分化出来的犊子部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分为过去、现在、未来、无为、不可说五类,认为都是实有的。它还特别强调“补特伽罗”(“我”)是“不可说”的,是实有的。“补特伽罗”与人身是“不即不离”的关系。这实质上是一种朦胧的、半真实的人,是一种实体性的灵魂,是轮回转世的承负者。犊子部承认“有我”也是和早期佛教的“无我”论相对立的一种新说。
从说一切有部分出的说经部又转而肯定佛陀的无常学说,否认说一切有部主张的一切事物永远存在的论点,强调一切事物仅仅是在目前存在,也就是反对三世实有说,主张刹那说。说经部认为,所谓事物的实有或存在,是就事物发挥某种作用而言,事物只有发挥作用才是真实的。事物也只能占有特定的时空位置,发挥其特定的作用。而所谓发挥作用,就意味着产生结果。也就是说,事物的实有只有在它产生特定的结果时才是真实的。而所谓事物产生特有的结果,就是转化成为下一种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只有在它转化为它下一种的存在方式时,才是实有的。说经部由此得出结论:事物的实有或存在是刹那间的,事物是刹那存在,而不是三世存在。说经部由此还否定涅槃是永恒幸福境界的观点,认为一切都是无常的,涅槃也仅仅是停止受苦、停止轮回的境界。这就是倾向于事物是空的说法。说经部的论点遭到毗婆沙论师的反对,被指斥为是一种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理论。
大众部各派偏重于讲“空”,或是只承认现在实有,认为过去和未来都是没有实体的。与此相联系,在心性及其解脱问题上,大众部和上座部虽然都主张“心性本净”,但是两派所讲的“心性本净”的含义却大相径庭。上座部所说的“心性本净”是指心本来就是净的,大众部则指心在未来可能是净的,心净是未来可能达到的境界,实际上是认为原来的心并不净,是染心,是强调染心可以得到解脱。可见两派的观点是对立的。
从宗教实践和宗教理想的角度来看,大众部对后来大乘佛教的影响比较深刻。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看,大众部的理论与大乘空宗具有较多的渊源关系,而从上座部向说经部的演变,后来又在深受大乘空宗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大乘有宗。
三、大乘佛教的哲学思想公元1世纪左右,印度出现了大乘佛教的思潮,发生了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历史性分裂。
大乘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又演化为中观学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两大派别。唐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对印度流行的部派和大乘空、有两宗有明确的介绍。中观学派主张观察问题要不落一边(如空与有、常与无常各为一边),即同时观察二边,以合乎中道,因而得名。由龙树(约150—250)及其学生提婆(圣天,约170—270)所创立,奉《大品般若经》为主要经典。龙树著的《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和提婆著的《百论》为此宗的基本理论著作。提婆的后继者是罗罗跋陀罗,罗罗系传至清辨及佛护,随后又分裂为不同的派系。约公元4至5世纪,大乘佛教又形成瑜伽行派,此派成为佛教的主流。“瑜伽”是相应的意思,指一种观悟佛教“真理”的修行方法。此派尊弥勒为始祖,以《解深密经》和《瑜伽师地论》等为主要经典。创始人是无著、世亲兄弟。无著著的《摄大乘论》,世亲著的《二十唯识论》、《三十唯识论》和《大乘百法明门论》等,在创宗方面作用最大。继世亲的有亲胜和火辨二家,相继发挥亲胜学说的有德慧、安慧和真谛,以上称为前期瑜伽行派。另外继承世亲、火辨一系的陈那,特别重视因明,即重视逻辑论证和认识论探讨。发挥陈那思想的有无性、护法、戒贤(玄奘的师父)和法称等,为后期瑜伽行派。
龙树一系反对部派佛教某些流派的万物实有的观点,认为人生的痛苦在于,人们对世间的一切事物缺乏真正的了解,产生了颠倒分别的无益戏论。要解脱痛苦,最根本的是要体会一切事物的“实际”,认清一切事物并无实体,是无“自性”,是“空”。这就是空观。中观学派“空论”的根据是缘起说。此派认为万物既然是因缘和合而生,即依靠其他原因、条件而生,不是从它自身中产生,这就说明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因缘所生就证明事物的内在的不真实。任何事物只要是依靠先行的事物而得以存在,它就必定失去声称自己有内在真实性的权利。依赖的存在不是真正的存在。佛教原来的缘起说,是讲任何事物都是有原因的,否则就不是实有的事物,也就是说,由于事物是有原因的,因此是实有的。中观学派则认为,一切有原因的事物都是不真实的,正因为是有原因的,所以是不真实的。这是在原来的缘起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缘起性空”、“一切皆空”的宇宙观。因此,中观学派又称为“大乘空宗”。
瑜伽行派继承了中观学派的空观思想,但又认为“一切皆空”的说法会导致否定成佛的主体和境界的理论危机,危及佛教自身的存在,于是此派提出万物唯识所变、识有境无的主张。众生的识是变现万物的根源,由于万物由识所变,因此,万物(境)是无(空)。由于识能变现万物,因此,识是有。瑜伽行派主张识有,所以又名“大乘有宗”。识能变现万物,识也是众生轮回转生的主体。由此瑜伽行派进一步提出“转依”的宗旨,用作“解脱”的代替语。所谓“依”,指人们的意识,“转依”就是从人们与生俱来的相续不断的意识状态着眼,认为人们意识、认识的转变会影响到行为,可以改变客观环境;主客观不断地交互影响,就会使整个的认识行为和环境都发生转化,众生也随着这种转化而成为佛。
瑜伽行派还展开了认识论和逻辑学的论证,一方面为其唯识哲学作论证,一方面又推进了认识论和逻辑学。
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后来都发生分化,形成不同派别。同时又出现中观瑜伽合流的趋势,至8世纪,寂护(700—760)更是正式创立瑜伽中观派。瑜伽行派主张唯心无境,识有境无,肯定心识,否定外境。中观学派主张境无心也无,心和境都不可得。瑜伽中观派认为,在世俗谛是唯心无境,在胜义谛是心境俱无,并且以为只有从唯心无境的观点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诸法无我”,即一切事物无自性的真谛。
大乘佛教思潮的出现,是继部派佛教之后佛教内部的第二次大分化,也是对早期佛教和部派佛教的最大冲击。从整个印度佛教史来看,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大乘佛教指斥前期佛教只求个人解脱,是“小乘”,标榜自己是普度众生,使众生渡过无边的苦海,到达幸福的彼岸,是“大乘”。前期佛教学者则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小乘,认为自己是佛教的正统。他们指责大乘佛教的教义是杜撰的,认为“大乘非佛说”,大乘并不是佛教的正统。大小乘佛教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大乘佛教是在批判继承小乘佛教的基础上的新发展,但是大小乘佛教在精神和实质上确又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在对佛的看法上,小乘佛教一般认为释迦牟尼是觉者、教祖、教主、传教师,而大乘佛教则强调依靠佛的愿力和他力得救,把佛视为超人的存在。大乘佛教在释迦牟尼身上罩上一团团迷雾,奉其为全智全能的最高人格神、神格化的救世主以及彼岸世界的统治者,后来更用造型艺术加以形象化的表现,为其建造宏伟的佛殿,对其顶礼膜拜。小乘佛教一般认为佛只有一个,就是释迦牟尼;大乘佛教则认为十方三世有无量无数的诸佛,如阿佛、阿弥陀佛、弥勒佛、药师佛等,进一步宣扬佛是整个宇宙力量的体现,佛是各方世界和极乐净土的主宰者。
(2)在追求的理想上,大乘佛教以成佛为目的,而小乘佛教则以“灰身灭智”、成就阿罗汉为最高目标。所谓阿罗汉就是烦恼已经消除、生死已获解脱、应当值得供养尊敬的圣者。
小乘佛教偏重于个人解脱,大乘佛教则宣扬普度众生,致力于一切众生的解脱。大乘佛教还提出“菩萨摩诃萨”的名称,大菩萨是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为志愿的,即从事传教活动以拯救他人者,是成就正觉(佛)的准备,也就是候补佛。例如大乘经典注重宣扬、中国佛教所特别尊崇的“四大菩萨”观世音(“大悲”)、文殊师利(“大智”)、普贤(“大行”)和地藏(“大愿”),就是重要的菩萨,而小乘佛教则完全不承认这些菩萨。小乘佛教所求的解脱,偏重于断除烦恼,灭绝生死,而大乘佛教如空宗则认为应以菩提(觉悟、智慧)为目标。菩提是佛体。众生只要去掉无明(无知),就可进入究竟的境界——涅槃。普度众生的理想不在于寂灭,而在于永生。
(3)在修持的方法上,小乘佛教认为人生痛苦的原因在于人生的“业”和“惑”,即由于种种行为(“业”)和种种烦恼(“惑”)而产生了苦果,应当重“教”尊“闻”,追求断“业”灭“惑”,不使再生,由此主张个人远离社会,隐遁禁欲。也就是说,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非出家过禁欲生活不可。大乘佛教认为人生问题不应孤立解决,应当全面解决,不仅自己要解除痛苦,也要使他人解除痛苦,也就是强调众生的“共业”的共同转化。他们重“行为”,强调不应逃避现实世界,而要面对现实世界,理解现实世界,努力使自己的宗教实践不脱离世间的实际,在现实中求得解脱。因此,大乘佛教特别是在初期很重视在家,不提倡出家。事实上按照大乘佛教的主张,有些修持是出家人也难以做到的,例如,布施中的财施,只有在家且有钱财的人才能做到。
(4)在理论上,正如前面所讲过的,小乘佛教学者拘泥于佛说,认为佛说的都是实在的,佛说有某类概念,就有某类实在。他们偏于细密的思辨,着重于对生死问题的探求。他们一般只承认人无我,即人并没有独立的永恒的实体,人是空的,至于宇宙万有则不是空的,而是有的(“法有”),这就是所谓人空法有说。小乘佛教中也有不同观点,如《成实论》不仅认为人是空的,还主张法也是空的。大乘佛教学者偏于融通、直觉,着重赞颂佛的功德,对于佛说带有自由解释、发挥的色彩。他们认为不仅人空,法也空,即宇宙万有也都没有独立的永恒的实体,也是空的,“一切皆空”,主体和客体都是空的,一切存在都如泡如影、如幻如梦。
大乘空宗和有宗将佛教唯心主义哲学发挥到极致,达到了宗教理论思维的高峰,可以说基本上标志着印度佛教哲学思想的完成和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