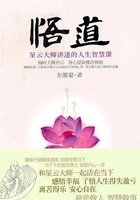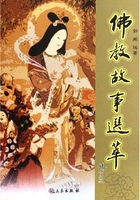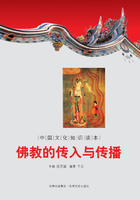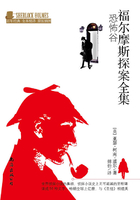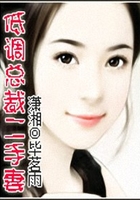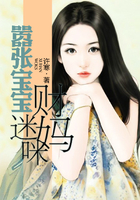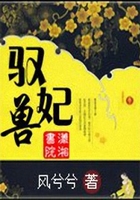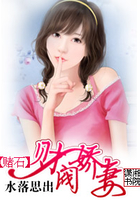南宋以前,许逊崇拜者将其信仰的孝道神格化,谓由玄、元、始三?化生出日、月、星斗中的孝道仙王、孝道明王和孝悌王,由它们将此孝道传于人间。故那时的孝道信仰,基本保持在道德观念与鬼神崇拜相结合的水平上。南宋理学大兴之后,元初刘玉受其影响,除继承上述神道信仰外,又借助宋明理学将此孝道扩展为忠孝,并使之哲理化,提出一个被宗教所“净化”、被理学所“熏染”了的“真忠真孝”,作为修持净明道的理想境界和最终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刘玉提出了修持净明道的三步骤:“始于忠孝立本,中于去欲正心,终于直至净明。”(《玉真先生语录》)
1.忠孝立本
刘玉以忠孝为修净明道的根本,把忠孝看作修持净明道的屋基和桥墩,正像不打好屋基就修房,不做好桥墩就架桥,房屋和桥会倒塌一样,不立忠孝作根本,净明道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无法修持。他之所以把忠孝作修持净明的根本,主要是因为“人道”为“仙道”的入门工夫和基础工夫;人道修好了,才有可能去修仙道。在他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仅在于人具有禽兽没有的忠孝德性。丧失了这种德性,“便不得为人之道,则何以配天、地而曰三才”。所以他径称净明道为“忠孝大道”:“入吾忠孝大道之门者,皆当祝国寿、报亲恩为第一事。”又称净明道是“学为人之道”:“此教法大概只是学为人之道。……所贵忠君孝亲,奉先淑后。”怎样忠君孝亲呢?一方面注重忠君孝亲的日常行为,即刘玉所说,对双亲“夏葛冬裘,渴饮饥食,与世人略无少异”( 以上皆见《玉真先生语录》)另一方面,特别注重思想上的忠孝修养,即其弟子黄元吉所说:“事亲之礼,冬温夏?,昏定晨省,口体之养”,只是“孝道一事耳。当知有就里的孝道,不可不行持”( 《中黄先生问答》,载《净明忠孝全书》卷六)此“就里的孝道”,即指思想上的修持。可见所谓忠孝立本,主要是指在思想上立下这个根本。
以上思想实源于陆九渊等理学家。陆九渊说:“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陆九渊集》卷二《与王顺伯书》,《四库全书》集部)强调为学必须“立本’、“知大”。“大”指天理,“此理即是大者”( 《陆九渊集》卷一一《与朱济道书》)“本”指具有天然良知的“本心”,立大、知本就是把体认了天然良知的本心立起来。可见净明道的忠孝立本与陆学有直接的思想渊源。
2.去欲正心
刘玉认为,人之忠孝德性,是人的良知,是人心本具的,不假外求。他说:“忠孝者,臣子之良知良能,人人具此天理,非份外事也。”“大忠大孝,根于天性。”既然如此,则修持净明,全在于存守自己心中之良知,使之不失,并得到发扬。但是这种良知,又常受外界尘事所引诱和己身私欲所蒙蔽,而常常有丧失的危险。刘玉说,蒙蔽忠孝良知的主要是两个怪物:一是“忿”,二是“欲”。“所谓忿者,不只是恚怒嗔恨,但涉嫉妒,小狭偏浅,不能容物,以察察为明,一些个放不过之类,总属忿也。……所谓欲者,不但是淫邪色欲,但涉溺爱眷恋,滞著事物之间……总属欲也。”他又称此二怪物是会作“内祟”的“魑魅魍魉”。正是它们,才使人心蒙昧,使忠孝良知不能发扬,为了对付这些“昧心天”的鬼物,刘玉提出了“去欲正心”的修持方法。这实际包含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去欲”,即“惩忿窒欲”;二是“正心”,即“正心诚意”。前句来源于《周易》的《经》和《传》,后句来源于《大学》,后来被理学家们用作道德修养的方法之一,刘玉也借用来修持净明道。这就要求修道者“平居暇日,存守正念”,“夙兴夜寐存着忠孝一念在心”;要时时作整理心地工夫,“力除恶习,克去己私”,保持心地不被“埃墨涂污其上”。为了达到以上要求,刘玉又提出“防微”方法。他说:“譬如恶木萌蘖初生时,便要和根铲却。若待它成长起来,枝叶延蔓,除之较难了。”即要将恶念消灭在萌芽状态。他还提出“慎独”方法,即不仅在大庭广众中谨言慎行,而且在个人独处时也一丝不苟,不做昧心事,“紧要处在不欺昧其心”,“要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内不怍于心”( 以上皆见《玉真先生语录》)以上这些方法,皆从儒家抄来,在儒家经典中都可找到出处。
3.净明境界
刘玉认为净明境界是净明道要求达到的理想境界和整个修持的最后归宿。他说:“何谓净?不染物;何谓明?不触物。不染不触,忠孝自得。”又说:“心如镜之明,如水之净。”(《中黄先生问答》,载《净明忠孝全书》卷六。)元吉解释说:所谓净明,“大概无别说,只要除去欲便是净,就里除去邪恶之念,外面便无不好的行检。……淘汰到无的田地,却是公心也。公能生明,所以曰:欲净则理明”。可见“净明”并不是指佛教那种不染一尘、不著一物的“寂灭”、“空无”,而是指所修的主体“忠孝”之“净化”。这是一种被宗教理念所“净化”,又为理学所“熏染”了的精神境界,它既是净明道之道,又是儒家的忠孝之道。
以儒家忠孝为修持内容和最后归宿,这在道教诸派别中可谓“仅此一家”。由此决定了它区别于其他任何道派的特点。首先,既以忠孝为根本修习内容,则对其余诸派之修习精、气、神或符术多有微辞,认为它们丢掉了忠孝这个根本,结果只能是枉费工夫,“到底只成个妄想去”,从而把修炼精、气、神和符术等摆在十分次要的地位。其次,神仙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以肉体不死为长生,而以不昧忠孝之本性为长生。刘玉说:“忠孝之道非必长生,而长生之性存。死而不昧(忠孝之心不昧),列于仙班,谓之长生。”(《玉真先生语录》)谓“真人”、“神人”的概念也变了。黄元吉说:“当知九霄之上,岂有不净不明不忠不孝之神仙也。”又说:“真者一真无伪,人者异于禽兽。净明教中所谓真人者,非谓吐纳、按摩、休粮、辟谷而成真也,只是惩忿窒欲,改过迁善,明理复性,配天地而为三极,无愧人道,谓之真人。”故刘玉称周、程、朱、张是“皆从仙佛中来”的“天人”。总括上述两点,又可得出一个总特点,即净明道的世俗气很重,仙气和鬼气较轻,这可说是汲取入世儒学所必然带来的结果。
总上可见,宋元时期所出现的几个新道派(还有真大道、太一道未叙及),皆以融合儒、释为特征,表明道教之融合儒、释较前更为深入。
远在道教新宗派产生之前,儒家方面即在北宋出现了融合释、道的新儒学,即所谓理学。理学的开山祖师是宋仁宗时的周敦颐,人称濂溪先生。他的代表作是《太极图说》(《太极图说》,载《周子全书》卷一,《四库全书》集部)理学家公认为开创之作,恰好就是融合释、道特别是融合道教的典型。该书是讲宇宙生成和发展规律的,由《图》和《说》两部分组成。但不管《图》也好,《说》也好,主要皆来源于道教。
首先,关于《太极图说》之《图》,其远源是唐代道书《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中之《太极先天之图》和五代道士彭晓所编《周易参同契》旧本中之《水火匡廓图》及《三五至精图》,近源是唐末宋初道士陈抟之《太极图》或《先天图》。这些,自南宋至明清,已有许多学者,如朱震、黄宗炎、毛奇龄、朱彝尊、王嗣槐等写过考辨文章,作了详细的分析与说明,可谓言之凿凿。
其次,关于《太极图说》之《说》,由两部分文字组成。前一部分讲宇宙本源和它的演化过程,后一部分讲人性的善恶和修养问题。他说:宇宙的本源是无极,由无极而生太极,再由太极分为阴阳,阴阳的一动一静而生出五行,然后“二(阴阳)五(五行)之精,妙合而凝”,遂产生出人和万物。这里的名词,太极来源于《易·系辞》,可谓出自儒家,而无极却来源于《老子·知其雄》章。其宇宙生成模式,由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实际又是《老子》的“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模式的翻版。后面讲人性善恶和修养问题时,也汲取了佛、道的“无欲”、“主静”思想。总之,理学开创之作的《太极图说》是融释、道的产物,所谓“粹然孔孟渊源”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继周敦颐之后的二程兄弟,是理学的奠基者,他们虽以卫正统,反佛、道著称,但他们所建立的理学体系中仍然偷运了佛、道思想。他们以理(天理)作最高哲学范畴,认为宇宙万物包括社会道德在内,都含藏于这个天理中,父子君臣之理,德性之知,都是天理所必然,人心所固有的。要认识它们,无须外求,只须内省即得。他们称此内省工夫叫“诚”、“敬”,只要人们静坐内省,就会豁然贯通,天理自明。这种内省工夫与禅宗的坐禅十分相近。另一方面,他们在讲人性时,又提出“性即是理”的命题,既然性即是理,为什么会有善恶之分呢?他们提出了“气禀”之说加以解释,说:“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二程遗书》卷一八,《四库全书》集部。)种说法则来源于五代道士杜光庭。杜光庭说:“人之生也,禀天地之灵,得清明冲朗之气,为圣为贤;得浊滞烦昧之气,为愚为贱。”(《道德真经广圣义》卷八)
集理学之大成的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也明反释、道,暗融释、道。他一方面汲取佛教禅宗、华严宗思想,常用佛教“月印万川”之喻来说明“理一分殊”,另一方面又受道教思想影响。如朱熹很推崇出自陈抟之手的《河图》、《洛书》,将二图置于《易经》之卷首,说:“《河图》、《洛书》便是天地画出底。”(《朱子全书》卷二六,《四库全书》集部)某于世传《河图》、《洛书》之旧,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义理不悖,而证验不差尔。”(《朱子文集·答袁仲机书》,《四库全书》集部。)又以邹!之化名作《周易参同契考异》,还为《阴符经》作校正,成《阴符经考异》。他在阐发周、程太极、理等范畴时,虽口头上反对老子“道生物”的观点,而实际所说却与老子“道生物”观点毫无二致。朱熹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主宰者,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朱子语类》卷一,《四库全书》集部)说:“太极动而后生阳,静而后生阴,生此阴阳之气。”(《朱子语类》卷九四)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太极图说注》,《四库全书》集部。)论其生则俱生,太极依旧在阴阳里,但言其次序,须有这实理,方始有阴阳也。”(《朱子语类》卷七四)种“太极生阴阳”、“理生气”、“气流行发育万物”的观点,与《老子》“无生有”、“道生一”、道生万物的观点,实在没有区别。总之,融合佛、道是理学家的基本特征,是从大量事实中得出的结论。
在北宋,除上述口头反对佛、道,暗里融合佛、道的理学家外,还有一批并不反对佛、道,也不讳言融合佛、道的儒学家,即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派。苏轼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辩才文》,《东坡后集》卷一六,《四库全书》集部)本人既和禅宗名僧契嵩,天台宗慧辩、元净等很交好,又性喜道教修炼术,作《龙虎铅汞论》,“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炼养”。他的胞弟苏辙一方面与僧徒交朋友,为慧辩、元净写塔铭;另一方面又信仰道教,自称:“心是道士,身是农夫。悟(误)入廊庙,还居里闾。秋稼登场,社酒盈壶。颓然一醉,终日如愚。”(《自写真赞》,《栾城后集》卷五,《四库全书》集部。)学派的黄庭坚、晁补之等都有类似的自况。
宋元时期的佛教徒主要是融合儒学,但也兼摄道教。南宋禅僧克勤曾用道教语言赞颂皇帝:“神霄真人降驾,长生帝君御极,神灵开旦,夷夏钦风……”“道超盘古,德冠羲轩,位永固于金轮,寿弥坚于劫石。时平道泰,天清地宁。一人高拱无为,万物各得其所。”(《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又用道家和道教的思想概念解释佛理,说:“道本无言”,“大象无形至虚包万有”,“启无为之化,行不言之教”,“融通万有而混成”。这些都表现出他深受道教的影响。元初禅僧行秀以融通儒学著名,人称“孔门禅”,但也兼融道教。他说:“儒、道二家宗于一气,佛家者流本乎一心。圭峰道:元气亦由心之所造,皆阿赖耶识相分所摄。”(《从容录·第一则》)引《道德经·谷神不死》章解佛理,说:“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绵绵若存。又曰:吾不知谁子,象帝之先。衲僧为言,绵绵若存,不可一向断绝去也。象帝之先者,空劫以前,佛未出世时也。”(《从容录·第一则》)
三、明清道教与儒、释
继宋元之后的明清,是三教融合进一步深化时期。三家各自融进对方更多的东西,使原有的个性大量泯灭,思想面貌彼此混同,以至难辨你我。具体表现是:三家完全消除了思想壁垒,原为某家独有的思想,竟成为三家共同的学问。理学家谈禅、谈内丹,佛教徒谈正心诚意,谈治国平天下,道教徒谈明心见性,谈解脱,已成为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无以名之,或可谓之“三教混融”。
这种混融现象,在道教方面表现十分突出。不少道士,借用儒家的性理之学以讲性命修炼(内丹),或采用佛教禅宗的参究法门以讲明心见性。甚至一些符派道士也大谈性理,或用大乘空宗思想超度鬼魂。这些都是以往时期所不见或罕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