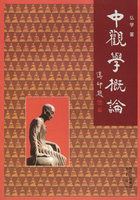明初道士王道渊是著名的内丹理论家,他师承南宗性命双修、先命后性思想,而以混融性命为其主要特点。他的内丹理论就颇具理学色彩。首先,他以理学家的“体用”之说阐述性命双修,说:“性者,人身一点元灵之神也,命者,人身一点元阳真气也。命非性不生,性非命不立。”“性乃为人一身之主宰,命乃为人一身之根本。……性应物时,命乃为体,性乃为用;命运化时,性乃为体,命乃为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方可谓之道,缺一不可行也。”(《还真集》卷中)体用之说,即来源于理学家。程颐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易传序》,载《二程集》卷三,《四库全书》集部。)次,王道渊虽主性命双修,先命后性,但却以炼心为修命的下手工夫。如何炼心?就是采理学家的惩忿窒欲方法。他说:“惩忿者,戒心也,窒欲者,止念也。戒其心,则忿不生,止其念,则欲不起。忿不生,而心自清,欲不起,而情自静。心清性静,则道自然而凝矣。”(《道玄篇》)里他提出以理学家的“惩忿窒欲”达到戒心、止念的目的。第三,在修性问题上,王道渊汲取理学思想更多。他袭用朱熹“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观点,将人性分为两种,说:“人之生也,性无有不善,而于气质不同,禀受自异,故有本然之性,有气质之性。本然之性者,知觉运动是也;气质之性者,贪嗔痴爱是也。”(《还真集》卷中)是说,人禀受于天的“本然之性”都是善的,只是由于气质不同,才使它有善有恶。不仅人类如此,万物亦然:“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此非无佛性也,乃形质之异也,人与万物之性同,人与万物之形异。”(《还真集》卷中)说:“其于人也,性有善有恶;其于物也,性亦有善有恶。何也?此气质之异也,非性之本然。”(《道玄篇》)是说,人的本然之性是善的,万物的本然之性也“无不皆善”,虎狼蜂蚁就具有父子君臣的德性,与人无异。平时所见人性之有善恶,那是所禀气质不同带来的,非天性之本然。以上这些说法,均可在佛教和理学家那里找到直接来源。为了证明人生之前就有一个天赋的本然之性(又叫“真性”或“人身一点元灵之神”)存在,王道渊又糅李翱《复性书》和禅宗“月印万川”之说以作喻,说:“性如空中之月,形犹地上之水。万水澄清,一月普明,万水浊浑,一月普昏,非月之有明有昏,乃水之有清有浊。人为圣为哲为贤,得气之清者也,人为愚为昧为恶,得气之浊者也。佛乃曰: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是也。”(《还真集》卷中。)思是说,人自先天所得之“真性”、“元灵之神”本是洁白无瑕的,只由于被气质之性污染了,常常昏浊无明,故修性之要在于清除上面的污垢,使之复其本来的真面目。此外,他在《道玄篇》中又借用许多儒家思想以阐道之玄旨,说:“君无臣不举,臣无君不主,君臣同心,天下莫能取。君视民如子,民视君如母,子母相亲,天下莫能语。我之于道,生之若母,保之若子,子母相守,长生不死。”“人于日用也,礼乐不可无也。有礼则心致于敬,有乐则身致于和。心致于敬,则百事齐之,身致于和,则百神安之。神安之,则气满于冲虚。”“天下治道有五焉,以仁布天下则民安,以义制天下则民服,以礼教天下则民敬,以智察天下则民守,以信亲天下则民立。此五者同出而名异,是以圣人体道若虚,用道有余。”“善忠者必善于孝,善孝者必善于忠。入则移忠孝于亲,为子之道尽矣,出则移忠孝于君,为臣之道尽矣。是故君与亲一而已,忠于孝亦一而矣,其善忠善孝者,天之道也。”“为人臣以道辅人主者,当洁己以奉公,上不闭恩,则君之德下流矣,下不闭言,则民之情上达矣。上下相通,则家国之道常泰矣。”如此等等,不必分析,即可见他所阐的道之玄义,已极大地儒学化了。
明初道士张宇初,被敕封为43代天师。他本以符咒术为其祖传的看家本领,但也随着时代潮流的演变,一方面兼修内丹,另一方面又“贯综三氏,融为一途”( 《岘泉集》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文章乃斐然可观,其中若《太极释》、《先天图论》、《河图原》、《辨荀子》、《辨阴符经》诸篇,皆有合儒者之言,《问神》一篇,悉本程朱之理,未尝以云师、风伯荒怪之说,张大其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岘泉集》条)际上,上述诸篇不仅“有合儒者之言”,而且很多内容只是理学家言论的改头换面。张宇初说:“太极散而为万物,则万物各一其性,各具一太极。……合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未分之前,道为太极,已形之后,皆具是理,则心为太极。……万事万化皆本诸心,心所具者,天地万物不违之至理也。”(《岘泉集》卷一。)说:“人道者心,收之则万殊一本,放之则一本万殊。物物各具一太极,莫非此心也。”(《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通义)盖心统性情,而理具于心,气囿于形,皆天命流行而赋焉。……是曰心为太极也,物物皆具是性焉。”(《岘泉集》卷一)有这些,都是周敦颐《太极图说》出现后,程朱理学家讨论最多的问题,张宇初将它们连思想带语言全部拿了过来。其《问神》一篇,张宇初又完全以二程言论证鬼神之非无。他说:“夫天积气也,地亦气之厚者,形而上者是也。?行形之内,即天命之流行也。以其流行不息,必有宰之者焉。程子曰,主宰谓之帝,妙用谓之鬼神。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二气之良能,盖阴阳之运迹不可见,而理可推焉,理之显微有不可窥测而神居焉。故虽圣人未始言其无也,特不专言之而已。”(《岘泉集》卷一)趣的是,张宇初还用佛教涅?解脱之说以超度亡魂,说:“经曰:三界众生本无轮转,真一道?本无生灭。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故曰: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还宿债。……只为息此一念,一灵妙有,亘古长存。盖由结爱为根,积想成业,故有种种受生,种种偿报,千生轮转,万劫苦恼,转转不息,罔自觉知。座下四众受度亡魂:我以非舌言,汝以非心听,向非言非听处,猛烈悟来,毕竟不落万缘,超出万幻,则三业六根,一时净尽……大众闻此法音,顿然解悟。”(《岘泉集》卷七)洋洒洒千余言,不啻佛教徒宣唱“法音”。
与不少道士结合内丹大讲性理之学的同时,又有一些道士大讲佛教的“参究”。明初全真道士何道全是其中之一。其门徒给他编辑的《随机应化录》,记录了他游历江、浙、淮、楚、山东、河南、陕西等地的言行,其中既有与道士、信徒及官吏等讲道的言论,又有与一大批僧人参禅论道的言论。兹举数例如下:
师至邳州佑德观,有秀聚峰和尚参师,问“念佛”二字?师曰:“何必远求,自己的佛如何不认?假如诸将西方佛来,却把你自家佛放在何处!汝不闻川老云:……身中自有真元始,何须心外觅天尊。儒云:吾身自有一太极也。”和尚再问曰:“请师开示念佛捷径法门,得见佛面。”师笑曰:“吾语汝,……且念佛法门有三等:一降魔,二观想,三参究。此三段俱不在念佛数珠上。”(《随机应化录》卷上)
这段话大意谓前两等念佛法门为根柢浅者所行,行之,不能见佛成佛,只有第三等“参究”,方能见佛成佛。他说:“参究念佛者,须择静处,节饮食,厚毡褥,宽衣结跏趺坐,竖脊调气,屏除杂念。然后将佛号轻轻举起,不在出声,默念一声至百声。如有杂念,重头再举,直至百声无间断。一声声参究意义:念佛的是谁?四大分张之时,念佛的归于何处安身立命?且参且念,时时不离。行住坐卧中参念,不可忘却穷根究本,直须要个明白。直至不参自参,不举自举。日久月深,猛然摸着自己鼻孔,认着阿弥陀佛。恁时一声,即登彼岸,胜似念千万亿佛名,数念珠耗气也。”(《随机应化录》卷上。)
师至东海大伊山古佛陀寺,与梁和尚语间,有铁牛和尚参师,拜求指个生死路头,教个出身之处。师曰:“有成有败是生死路头,无去无来是出身之处。……吾今直言与汝:若情忘念灭便是生门,意乱心狂便是死路。其心不与万法为侣,一性孤明湛然独照,此乃出身之处。”乃作诗曰:“不灭不生性湛然,无来无去出三千。要知这个翻身处,踏破虚空透妙玄。”(《随机应化录》卷上。)
师至静室,有僧聪都参师,问曰:“假如有一女子迎面而来,看为女子,看为男子乎?”师曰:“此是古语公案,要你自参自悟。吾若开解,难做功夫。”其僧再三请解。师叱曰:“看作女人著境相,看作男子无眼目。真性本无殊,著相生分别。背境向心观,自然万事彻。”师又叱曰:“学落花流水去。”其僧不语。师曰:“见如不见,焉知男女?心若无心,焉有罪福?大道不分男女,你别辨做甚!”(《随机应化录》卷下)
仅此数例,已可看出何道全对禅学是颇有研究的,如不看他的穿戴,会以为他是很有修养的禅僧。他曾作《三教一源》诗说:“道冠儒履释袈裟,三教从来总一家。红莲白藕青荷叶,绿竹黄鞭紫笋芽。虽然形服难相似,其实根源本不差。大道真空元不二,一树岂放两般花。”(《随机应化录》卷下。)他看来,三教本是同一藕根上的红莲、白藕与荷叶,同一竹根上的笋芽、黄鞭与绿竹,其宗旨与思想都是“不二”的,只是各家的穿戴不一样罢了。这大概也是当时三教状况的真实写照。
明中叶以后,道教趋于衰落,思想理论无所创新,但融合儒、释的步伐仍未停止。活动于明嘉靖、万历年间的道士陆西星,被称为内丹东派的开创者。他的内丹理论同样继续融合儒、释。首先,他主性命双修,阴阳双修,而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思想加以阐释,说:“性则神也,命则精与?也。性则无极也,命则太极也。”他认为:“所谓性,即无极也,所谓命,即二五之精也。”二者是人生所必具的:“人之生也,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二者妙合,而人始生焉。”故性命必须双修。但“性(即神)为命(精、?)之主宰”,“性定则神自安,神安则精自住,精住则?自生”。故其丹法是“自无为而有为,有为之后而复返于无为”,即从性功开始,经命功再返回性功。可见修性炼神为其丹法之重点。其次,陆西星仍袭用理学家“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观点,将人性分为自先天而来的本性和自后天而来的气质之性两种。他说:“夫性一而矣,何以有本性、质性之异?曰:本性者,自先天而言之,清净圆明,混成具足,圣不加丰,愚不少啬者也。质性者,自后天而言之,生于形气之私,于是始有清浊厚薄之异。”照他看来,这个来自先天的本性,是“清净圆明”,洁白无瑕的,任何人都“具足”无缺,圣人不会多一点,愚人不会少一点。那么,人为什么有贤愚、善恶之分呢?他认为,这是由于人在后天所具的质性不同的缘故:“性则水也,落于气质,犹水之入于泥淖中也。决而行之,但见泥淖而不见其水,泥淖岂能自行,水行之也,但水混于泥淖而不见耳。”因此他把清除这个由质性带来的泥淖作为修性的主要课题。第三,以遣欲澄神为清除质性泥淖的手段。陆西星认为,使人本性浑浊、元神不得清静的大敌是人欲。他说:“凝神之要,莫先于澄神,澄神之要,莫先于遣欲。《清静经》言:‘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易》曰:‘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所谓洗心,即澄神之谓也。周子曰:‘无欲故静。’所谓无欲,即遣欲之尽也。”(以上皆见《玄肤论》,《方壶外史选刊》卷下)心寡欲,虽为道家固有思想,亦为《清静经》的主旨,但此论“遣欲澄神”,难免融有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因素,其所引“周子曰”云云,亦已露其端倪。为了阐述“遣欲澄神”,他又引进佛教“真”、“妄”、“迷”、“觉”等说法:“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所谓心者有二焉:扰神之心乃妄心也,好静之心乃真心也。”他又说:“夫人之一心,本来无二,但以迷、觉而分真、妄。《金刚经》云:云何降伏其心?人生而静,天地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既有欲矣,则情随境转,真以妄迷,纷然而起欲作之心。”(《吕祖百字碑》卷上,《方壶外史选刊》卷上。)既有妄心,即惊其神,其神可得清乎?既惊其神,即著万物,既著万物,即生贪求;既生贪求,即生烦恼。烦恼妄想,忧苦心身,心可得而静乎?”(《玄肤论》,《方壶外史选刊》卷下。)要使神清静,既要遣欲,又要除此妄心。“以真销妄,妄尽真存,正觉现前,方名见性。”(《吕祖百字碑》卷上,《方壶外史选刊》卷上)见“遣欲澄神”、“以真销妄”是陆西星内丹理论的根本点,而这正是儒、释、道融合的产物。
活动于清乾、嘉时期的全真龙门派道士刘一明融合儒、释更突出。他以丹道解《易》,又将易学、理学融入丹道,使其内丹理论更具理学思辨色彩。
(一)先天真一之气
刘一明认为,道生天地万物是生生不息的造化之道,是道的顺行。但道不能直接产生天地万物,必须经过一个中介才能实现,这个中介就是“先天真一之气”。他说:“造化之道,生生不息之道。推其道源,盖自虚无中而生一气,自一气而生天生地产阴阳。阴阳再合,其中又含一气而成三体。三体既成,一气运动,阴而阳,阳而阴,于是万物生矣。”(《悟真直指》卷二,载《道书十二种》,《藏外道书》第8册)种观点来源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模式,所谓“先天真一之气”相当于道所生之“一”。刘一明认为,由道的顺行所产生的万物,终有死期,人也一样。欲求不死,只有修逆而行之的丹道,才能使人回复到未出生前的胎儿状态。因为胎儿乃是由“先天真一祖气”孕育而成,且只有此“一点祖气”,“别无加杂”( 《象言破疑·胎中面目》,《藏外道书》第8册。)而此祖气至善至纯,故“天地万物水火刀兵俱不能伤,七情六欲五贼四相俱不能近,究到实处,只一虚空而已”( 《象言破疑·胎中面目》,《藏外道书》第8册。)刘一明认为,人如回复到那种状态,就将与道永存。所以他既把所谓“先天真一之气”作为道生万物的中介,又把它作为修炼内丹的根本和最后归宿。因而他称“先天真一之气,为人性命之根,造化之源,生死之本”( 《周易阐真》卷首《先天横图》,《藏外道书》第8册)“即人生本来乾元面目”( 《会心内集》卷下《真正丹药论》,《藏外道书》第8册)故他说:“性命之道,始终修养先天虚无真一之气而已,别无他物。采药采者是此,炼药炼者是此,还丹还者是此……以道全形全者是此……长生长者是此。”(《指南针·百字碑注》,《藏外道书》第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