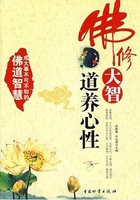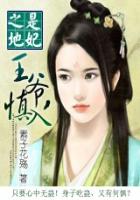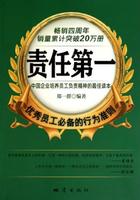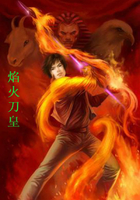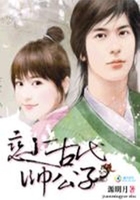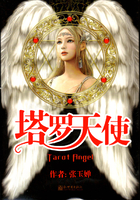这一时期,与道教融合儒、释同时,儒、释也融合道教,尤以佛教天台宗、密宗最为突出。天台宗创始人智及天台宗唐代中兴人物湛然在讲止观禅法时,汲取了道教气法及外丹、内丹。智说:“吐气之法,开口放气,不可令粗急,以之绵绵恣气而出。……次当闭口,唇齿才相拄著,舌向上腭;次当闭眼,才令断外光而已。”(《修习止观坐禅法要》)用止治者,温师云:系心在脐中如豆大……后闭目合口齿,举舌向腭,令气调恂。……所以系心在脐者,息从脐出,还入至脐,出入以脐为限。……正用治病者,丹田是气海,能锁吞万病。若止心丹田,则气息调和,故能愈疾。”(《摩诃止观》卷八)又说:“脐下一寸名忧陀那,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所治。”“用六种气治病者,即是观能治病。何等六种气?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嘘,六稲。此六种息,皆于唇口之中,想心方便转侧而作。”(《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认为:“金石草木之药,与病相应,亦可服饵。若是鬼病,当用强心加咒以助治之。”(《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止观》卷八讲“方术治”时,亦谈咒术。以上这些,虽难说全部来于道教,至少有一部分是取于道教的。湛然所著《止观辅行传弘诀》亦有类似叙述。他称调身、调息、调心“是三学之由”,谓“凡夫三法为始,初修圆观,名为圣胎,至初住位,名出圣胎,至妙觉位,名身成就,此即合调之位也”( 《止观辅行传弘诀》卷四。)该书卷八讲治病时,也讲咒术:“如治齿法者,第一本云,向北斗咒云,齿牙痛,北斗治之,痛差(瘥)自知,痛即差也。又以狗牙从阴地向阳地咒云:令人牙痛差,不差暴汝,差还本,痛即差也。如捻大指治肝等者,五指主五藏,故大指主肝……”该书卷十又讲道教外丹及五石、草木药等,说“天老曰: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食可长生。太阴之精名曰钩吻,入口则死。钩吻者,野葛也。若不信黄精之益寿,亦何信钩吻之杀人?金丹者,圆法也,初发心时,成佛大仙,准龙树法,飞金为丹,故曰金丹”。以上这些,皆可为天台宗受道教影响之证。
唐玄宗时开始兴盛的佛教密宗,在修行法方面与道教相似又相融。其“即身成佛”与道教“即身成仙”很相似。其经中所载的北斗、玄武、司命,司禄及四方之神,则是汲取于道教。
儒家也有调和道教的。唐德宗时的太子校书郎李观作《通儒道说》,认为儒、道同源,在儒为仁、信、礼、义,在道为道、德,“故二(指道与德)为儒之臂,四(指仁、信、礼、义)为德之指,若忘源决派,?茎而掩其本树,难矣”( 《全唐文》卷五三五。)
总上可见,隋唐五代的“三教”斗争虽很激烈,而融合也有较大发展。其中道教之融合佛教最为突出,几乎对佛教各宗派的思想都有所融摄(佛教宗派的涌现也与融合儒、道有关,此处未论),且其融佛已越过囫囵吞枣水平,而进入融会贯通阶段。这些都反映出此时期三教关系的特点。
二、宋元道教与儒、释
宋元时期“三教”斗争趋向缓和,融合呈现深入发展的局面。其主要标志,一是“三教一家”、“万善归一”的论调,在三家中长唱不衰;二是儒学在北宋出现了以融合释、道为特点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道教在南宋至元初相继出现了几个融合儒、释的新道派。
“三教一家”之说,大约始于南北朝,而形成三家同唱,蔚然成为一代社会风气,则始于北宋。北宋儒家中,虽不乏坚决排斥佛、道者,如孙、孙复、欧阳修、李觏等人,但大多数理学家则明反佛、道而暗融佛、道,且出现了以苏轼为代表的公开主张融合佛、道的蜀学派。至于佛、道两教中,倡言“三教一家、万善归一”者,可谓比比皆是。正是在这种“三教一家”的大合唱中,相继在儒家中出现了融合释、道的新儒学,在道教中出现了融合儒、释的新宗派,而且随着这一思潮的继续发展,这种融合在各家中不断深化。
(一)道教南宗的融合儒、释
道教南宗形成于南宋,而追尊北宋张伯端为始祖。张伯端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著《悟真篇》,打出了鲜明的“三教合一”旗帜。该书序言说:“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若有习漏未尽,则尚徇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要枢,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辞,《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仲尼极臻乎性命之奥也。”又说:“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奈何后世黄缁之流,各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歧,不能混一而同归矣。”因此,他在内丹理论中,力图使儒、释、道三家理论互相结合。他吸收儒家性命之说,主张性、命双修,吸收佛教禅法,充实修性内容。修命、修性两者缺一不可,步骤是先修命,后修性。但如只修命,不修性,就不能“回超三界”,“顿超彼岸”,“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源”。为了使人们重视修性,张伯端还写了禅宗气味很浓的诗歌词曲32首,作为《悟真篇》的外篇。其《三界唯心》诗说:“三界唯心妙理,万物非此非彼。无一物非我心,无一物是我己。”《即心是佛颂》说:“佛即心兮心即佛,心佛从来皆妄物。若知无佛亦无心,始是真如法身佛。……”《采珠歌》说:“不断妄,不断真,真妄之心总属尘。从来万物皆无相,无相之中有法身。……心若不生法自灭,即知罪福本无形。”由此可见,张伯端思想中的禅学成分是很多的。以此思想指导内丹修炼,自然将使佛、道融为一体。
张伯端“三教合一”的思想,与性命双修的内丹理论,为其后南宗四祖及其弟子们所共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所融儒、释思想不断被增益。南宗五祖白玉蟾继续高唱“三教合一”;“道释儒门,三教归一,算来平等肩齐”( 《鸣鹤余音》)“三教异门,源同一也。”(《道德会元》卷一《道法九要序》。)在与弟子们讨论心性修炼时说:“法法从心生,心外无别法。”(《海琼白真人语录》卷一。)说:“吾今则而象之,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知心无心,知形无形,知物无物。超出万幻,确然一灵。……故能三际圆通,万缘澄寂,六根清净,方寸虚明。不滞于空,不滞于无,空诸所空,无诸所无,至于空无所空,无无所无。……”(《海琼问道集·玄关显秘论》)中显然融进了佛教大乘空宗及天台宗止观思想。
南宗至元代后期合并入全真道,其门徒以全真道士身份继续融合儒、释。
(二)全真道的融合儒、释
金初,在中国北方相继出现了太一道、真大道和全真道等三个新道派,皆以“三教合一”为特征,尤以全真道最突出。
全真道由金初道士王?(号重阳子)所创(他的七个弟子也参与了创教)。创教时,即以读《道德经》、《般若心经》和《孝经》相号召,并组织了五个以“三教”两字冠首的教会以吸收道徒,一开始就表现出“三教合一”特色。它所融摄的佛教思想比南宗更显著。首先,在成仙信仰上,全真道不再追求“肉体不死”,只追求“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他们认为,人的肉体是要死灭的,人的真性或阳神则可以长存。王重阳说:“修行须借色身修,莫滞凡躯做本求。假合四般终是坏,真灵一性要开收。……”(《重阳全真集》卷一)评肉体长生的追求者,说:“离凡世者,非身离也,言心地也。……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重阳立教十五论》)处玄也说:“万形至其百年则身死,其性不死也。”又说:“真我者,人之性也,……无形之道也。”“无形之道则真也。”“伪我,则养身之道,则假也。”(《无为清静长生真人至真语录》)也认为养身为假道,不值得追求,只应追求养性之真道。旧道教认为,经过修炼,形、神皆可不死,故其信仰是肉体与精神一起长存。这是道教区别于佛教的根本点。现在全真道放弃了肉体不死的追求,表现了它与旧道教的区别,而与佛教追求的精神解脱(涅?)则大为靠近了。为了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乃视人的肉体为桎梏,遂大肆破斥肉体,否定人生。丘处机斥肉体为“臭皮囊”和“烂肉”:“一点如如至性,扑入臭皮囊,游魂失道,随波逐浪,万年千载不还乡。”(《銵溪集》卷五)一团臭肉,千古迷人看不足;万种狂心,六道奔波浮更沉。”“一团脓,三寸气,使作还同傀儡。”(《銵溪集》卷六)端认为人体“本是一团腥秽物,涂搽模样巧成魔”( 《水云集》卷上)王重阳等又斥人体为“走骨尸”、“骷髅”,“曾画骷髅警马钰,又作《叹骷髅》诗”( 《重阳全真集》卷一)谭处端说:“骷髅,骷髅,颜貌丑,只为生前恋花酒。”(《水云集》卷上)处机说:“子羽潘安,泉下骷髅总一般。”(《銵溪集》卷六)真道又斥人生为“苦海”、“火宅”,视父子、夫妻亲情为“冤业”。王重阳说:“儿非儿,女非女,妻室恩情安可取!总是冤家敌面仇,争如勿结前头苦。”(《重阳全真集》卷一)处端说:“茫茫苦海,逐浪随波,便宜识取抽头。恩爱妻儿,都是宿世冤仇。”(《水云集》卷中)似诗词,不胜枚举。可见放弃肉体长生,只求阳神解脱,其结果只能走上佛教所走的那条厌弃人生和凡尘的道路。
其次,在修炼理论上,与南宗先命后性,以修命为主相反,全真通主张先性后命,以修性为主。王重阳说:“宾者是命,主者是性。”(《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处机说:“吾宗惟贵见性,水火配合(指修命)其次也。”(《长春祖师语录》)牧常晁将这两种不同的丹法分别称为渐法和顿法,谓“渐法从命入手,顿法从性入手”。称从性入手的全真丹法为“释氏金仙之道”( 《玄宗直指万法同归》卷二。)点破了全真丹法最接近佛教的特点。从性入手的全真丹法,以明心见性为首务和重点,认为真性不离生,只为种种妄念所遮蔽而不能发明。故修丹的根本要求是打扫心地,清除妄念,要“把断四门眼耳口鼻,不令外景入内”,做到“心如泰山,不动不摇”。在十二时辰行住坐卧中,没有“丝毫动静思念”( 《重阳立教十五论》)一句话,要做到心地常清静。至此,“真性不动,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 《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尹志平说:“物欲净尽,一性空寂,吾教谓之清静。”但仅达这一步,尚未入真道,必须再进一步达到“寂无所寂”、“玄之又玄”的境界,性功才算完成(《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三)以上这些都可看出融合禅宗的痕迹。
应该指出,王重阳及其七弟子所创立的全真教的教义和内丹修炼理论,主要特点是融佛,儒家思想融入尚少。而在他们逝世后,其再传弟子们则不仅继续融佛,而且又大量融儒(主要是融合宋明理学)。如郝大通弟子王志谨继续融佛。他说:“修行人外缘虽假,不可不应。应而无我,心体虚空,事来无碍,则虚空不碍万事,万事不碍虚空。”“不著空,不著有,不执法相,不执我见……久久相资,融通表里,便是圣贤。”“起心无著,便是有著,有心无染,亦著无染,才欲静定,已堕意根,纵任依他,亦成邪见。无染无著,等是医药,无病药除,病去药存,终成药病。言思路绝,方始到家,罢问程途矣。”(《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
由南宗转入全真的元初道士李道纯,则不仅继续融佛,也大量融儒。他教人用禅宗清除念虑、幻缘的方法以修仙,说:“一切念虑都属阴趋,一切幻缘都属魔境。若于平常间打并得洁净,末后不被他惑乱。念虑当以理遣,幻缘当以志断。念虑绝则阴消,幻缘空则魔灭,阳所以生也。积习久久,阴尽阳纯,是谓仙也。”又说:“汝若不著一切相,则一切相亦不著汝,汝若不染一切法,则一切法亦不执汝。……至于五蕴六识,亦复如是。六尘不入,六根清静,五蕴皆空,五眼圆明。到这里,六根互用,通身是眼,群阴消尽,遍体纯阳,性命双全,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也。”(《中和集》卷四)采用禅宗“机锋”、“棒喝”的方法来讲道,《清庵莹蟾子语录》前四卷皆为这方面的记录。现仅举一例。他的一位弟子记曰:“师曰:‘井底泥蛇舞柘枝,窗间明月照梅梨。’作么生会?予拟议良久,曰:‘吹出窍中一曲,烁破眼里空花。’师曰:‘不是。’予又曰:‘脑盖撞开,惟有我眼睛突出,更无他。’师曰:‘较些子。’”(《清庵莹蟾子语录》卷一。)与禅宗后学一样,不用正常思维方式表现思想,偏用违反理性的东西去说道,由此可见其受禅学影响之深。另一方面,李道纯所受理学的影响也是很深的。他说:“古云‘常灭动心,不灭照心’,一切不动之心,皆照心也,一切不止之心皆妄心也。照心即道心也,妄心即人心也。‘道心惟微’,谓微妙而难见也,‘人心惟危’,谓危殆而不安也。虽人心亦有道心,虽道心亦有人心,系乎动静之间尔。惟‘允执厥中’者,照心常存,妄心不动,危者安平,微者昭著。到此,有妄之心复矣,无妄之道成矣,《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中和集》卷一)是用宋儒的“十六字心传”会合道教的心性修炼,其对十六字的解释和“危者安平,微者昭著”等语,亦全同于朱熹的《中庸章句序》。人谓:“儒学不能断生死。”李通纯回答说:“达理者,奚患生死耶?且如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原始返终,知周万物,则知生死之说。所以性命之学,实儒家正传。穷得理彻,了然自知,岂可不能断生死轮回乎!”(《中和集》卷三。)是将宋儒的“性理”之学等同于道教的性命修炼,其结果只能混淆两者不同的本质。李道纯又说:“(孔)夫子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夫子所乐者天,所知者命。故乐天知命而不忧,虽匡人所逼,犹且弦歌自娱”。他认为,这是夫子深得穷理尽性至命之学的结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金丹之妙也”( 《中和集》卷三)可见李道纯确是集三教于一身的人物。故他多方会通三教,使三教融为一体。他说:“道、释、儒三教,名殊理不殊。”(《中和集》卷六)们皆尚“静”,通“理”,主“中”,崇“虚”,在很多方面都能融通一贯。
元代另一全真道士牧常晁亦继续融合儒、释。他著《玄宗直指万法同归》以论三教义理不殊,谓“夫三家者,同一太极,共一性理,鼎立于华夷之间,均以教育为心也”。三家皆以“太极之道”化天下,“释氏用之以化天下,复本性;老氏用之以化天下,复元?;儒氏用之以化天下,复元命”。他认为:“儒氏养之以太极,用之以治天下;老氏养之以太极,用之以存形神;释氏养之以太极,用之以齐生死。”这是以儒家“太极”统三教,又以“三心”会三教。他说:“儒曰正心,佛曰明心,老曰虚心……设曰三心,实一理也。”他又以“中庸、真常、常住”通三教,说:“夫中庸,儒者之极道也;常住,释氏之极道也;真常,太上之极道也。因时有古今,道有升降,故体同用异也,非圣人命理之所以殊焉。”故他的结论是:“释即道也,道即儒也。……圣人之理一而已矣,非有浅深之间哉。”牧常晁依据“三教合一”思想,援佛入道,又提出:“戒定慧即精气神也。戒以养精,定以养气,慧以养神。”“吾自仙道而正性命,学佛道以广智慧。仙道不死,释道不生,不死不生,是为泥丸。”这里他把仙道等同于释、道的“泥丸”(涅?)。与此同时,他又引儒入道,即以儒家的性、命、理等概念解说道教的神?修炼。他说:“道在太极前谓性,性在天地间谓理,理之妙觉之谓神,神之虚灵合乎?,?之付物之谓命。《易》曰‘寂然不动’者,性之体也,‘感而遂通’者,神之用也。性于物无所不至,理于物无所不公,神于物无所不应,?于物无所不成。……本乎性,顺乎理,存乎神,?以生者命也。”(以上皆见牧常晁《玄宗直指万法同归》)
(三)净明道的融合儒学
净明道是在东晋道士许逊“孝道”信仰的基础上,经长期宗教衍变而于南宋时候形成的一个道派。元初的刘玉及其弟子黄元吉对它的教理教义又进行了一些更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