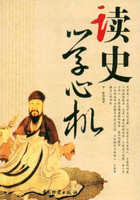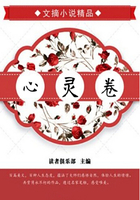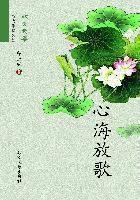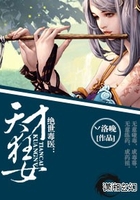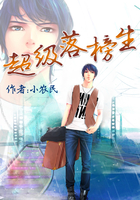隋唐至明清时期的儒释道关系,十分错综复杂,要全面加以研究介绍,非我之力所能逮。这里仅以道教为基点,着重介绍道教与儒释是怎样斗争与融合的,且在斗争与融合两个方面中,又以介绍道教融合儒、释为主。为了叙述方便,拟分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三个阶段来介绍。
一、隋唐五代道教与儒、释
三教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至隋唐,鼎立局面最后形成。隋朝一位隐而不仕的儒者李士谦说:“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佛祖统纪》卷三九)本意是评价三教价值,而客观上却给三教力量对比作了近似的描述,表明三家至隋代已大体势均力敌。面对三教的实际状况,隋唐统治者实行三教并用方针。但因唐王朝帝王姓李,为抬高皇室门第,认道教始祖李耳为祖先,故在唐前期的三教政策中偏重扶持道教,实行“老先,次孔,末后释宗”的政策。这种政策自然很受道教拥护,也可取得儒家谅解,但却与日益强大的佛教势力相矛盾,而遭到它的强烈反抗。故在唐前期,三教斗争特别是佛、道斗争异常激烈。除佛教与统治者之间,儒、释之间的斗争不计外,单是较大的佛、道斗争就有多次,如唐高祖武德七年的儒、道联合反佛斗争,太宗贞观十一年的释、道先后之争,高宗时期的多次佛、道大辩论,高宗、武后、中宗时期的《化胡经》之争,唐中后期的多次佛、道辩论等。其中武德年间的儒、道反佛,几乎引发唐高祖下令废佛。贞观年间的释、道先后之争,是唐太宗采取了棒打智实、流放法琳等强硬措施后,才迫使佛教就范的。至于佛、道之间的多次大辩论,也是双方唇枪舌剑,火药味十足。可见三教关系特别是佛道关系是很紧张的。这在三教关系史上,可谓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这种紧张关系,直到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王朝的衰落,才逐渐缓和下来。
大斗争促进了大融合。就道教讲,表现尤为明显。突出的是:在佛教大乘空宗和隋代天台宗、三论宗的影响下,道教在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个佛教色彩很浓的学派——重玄派。据一日本学者研究,重玄派上继太玄派、灵宝派,形成于隋代后期,而流行于初唐(砂山稔:《〈灵宝度人经〉四注札记》,载《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2期。)东晋尚书郎孙登“以重玄为宗”,可以看作是它的萌芽。其主要代表人物见于唐末道士杜光庭所著的《道德真经广圣义》,其中说:“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静,陈朝道士诸糅,隋朝道士刘进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黄玄赜、李荣、车玄弼、张惠超、黎元兴,皆明重玄之道。”(《道德真经广圣义》卷六。)见重玄派在唐初道士很多,是初唐最兴盛的道教学派。
重玄派道士的著作,目前所存不多,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初唐道士成玄英的《老子注》和《南华真经注疏》。《老子注》原本早佚,经近人蒙文通对散存于诸家《老子》注疏中的疏文,加以辑录校理,成《道德经义疏》,尚称完帙。这是现存重玄派最重要的著作。通过对它的分析,不仅可以展现重玄派的思想面貌,也可揭示其融合佛教的情状。
该书下面两段话,比较典型地体现了重玄派的思想:
玄者深远之义,亦是不滞之名。……深远之玄,理归无滞。既不滞有,亦不滞无。二俱不滞,故谓之玄。
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
这两段话,一说“一玄”,二说“又玄”。从两个层次上表述了它的思想。
“一玄”,或“一中之玄” 成玄英对玄字的解释,一曰“深远之义”,二曰“不滞之名”。以“深远”之义解玄,无疑是符合《老子》本意的。《老子》和许多道家书皆作如此解释,可说是它的本义。而以“不滞”(即不著名相)之义解玄,则非道家所有,而为佛教思想,可说是成玄英的创见。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将此二义合为一义:“深远之玄,理归无滞”,实际是将“深远”这个道家义,归并和融于“无滞”这个佛义之中。从而使他笔下的玄(实为道的表现形态)被抹上浓厚的佛教色彩。他说:玄是什么呢?“既不滞有,亦不滞无。二俱不滞,故谓之玄。”意谓“有”与“无”是“二边”,或两个极端,玄的本性是不滞著,不滞于任何一边;即他所谓的既不滞于“有”(有欲,有为等),又不滞著于“无”(无欲,无为等)。遣去二边,居于中道,这才是玄的本性。他称此为“一中之玄”,或“一中之道”。他认为只有这种不滞著于有、无的“一中之道”,才是老子之道,才是圣人施化之道。所以他说:“圣人施化,为用多端,切当而言,莫先中道。”他为此对《老子》章句作了很多解释:“为学之人,执于有欲;为道之士,又滞无为。虽复深浅不同,而二俱有患。今欲祛此两执,故有再损之文。既而前损损有,后损损无,二偏双遣,以至于一中之无为也。”“境智双遣,根尘两幻,体兹中一,离彼二偏,故无无为之可取,亦无有为之可舍也。”“体一中则得,滞二偏则惑。”“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后遣无欲者,此则双遣二边,妙体一道,物我齐观,境智两忘。以斯为治,理无不正也。”他认为双遣二边之后,就能体认出道的虚玄本质:“妙本非有,应迹非无。非有非无,而无而有,有无不定,故言恍惚。”当体认了道之“非有非无,而无而有”的本质后,就可得“虚玄极妙之果”( 以上皆见成玄英《道德经义疏》)
成玄英从《老子》中揭示出“不滞二边”的“一中之玄”,确是前不见古人的(成玄英的老庄注疏为重玄派之代表作,他之前的重玄派道士之书少见,姑以
其书为创始之代表)它虽与《老子》的某些思想有联系,但主要却是引进佛教“二谛”论和“中道”观的结果。佛教中观学派认为,因缘所生诸法,自性皆空;世人不懂这个道理,误以为真实。这种世俗以为正确的道理,谓之“俗谛”(或称“世谛”,“世俗谛”)。佛教理论家认为世俗的认识是“颠倒”的,而“缘起性空”才为真实,称为“真谛”(或称“第一义谛”)。要认识世间的真理,必须将此“二谛”联系起来,将被世俗颠倒了的认识颠倒过来,以“有”为非有、假有,以“无”为非绝对的空无,即非无,假无。这种非有非无、即有即无的认识,才是正确的认识,这就是佛教的“中道”观。这种思想为大乘佛教各派所尊奉。其后,天台宗的智据此建立空、假、中“三谛”及“三止三观”学说。三论宗吉藏则将它和“八不”(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结合起来,建立“八不中道”和“四重二谛”理论。其核心都是用“二谛”、“中道”这种否定式的思辨方法,以破除所谓的“执著”、“边见”,达到否定一切,“一切皆空”的认识目的。正如龙树所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中论》。)如吉藏所说:“借有以出无,住世谛破无见;借无以出有,住第一义(谛)破有见。故说二谛,破二见也。”(《二谛义》卷上)显然,上述成玄英的“既不滞有,亦不滞无”,“双遣二边”的“一中之道”,就是汲取上述佛教(主要是三论宗)思想炮制出来的。
“又玄”,或“重玄” 成玄英认为,“双遣二边”,得“非有非无”的“一中之道”,仅是体认道之初步,还不能体认出它的本质,因为住于“中道”,仍是“有滞”、“有著”。要体认“至道”“虚通之妙理”,还必须深入一步作“又玄”或“重玄”工夫。他说这原是老子的意思。老子知道“虽遣二边,未忘中一”,不得谓之“尽善”。因为“一中之玄”的价值,仅在于能遣去“有”、“无”二偏,有如药的作用一样,病治好了,药就没用了,此即“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药还遣。唯药与病,一时俱消”。所以成玄英在说了“一玄”之后,“恐行者,滞于此玄”,再犯滞著之病,故“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前以无名遣有,次以不欲遣无。有无既遣,不欲还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泯,此则遣之又遣,玄之又玄”( 以上皆见成玄英《道德经义疏》。)总之,所谓“又玄”或“重玄”,就是在双遣二边之后,不滞于“中道”,要把治二“偏”之“药”的“中道”一齐遣掉,即彻底不滞著。
成玄英遣有遣无之后又遣中的“重玄”思想,仍主要来源于大乘空宗和三论宗。吉藏《三论玄义》说:“夫有非有是,此则为邪,无是无非,乃名为正。……为息于邪,强名为正。在邪既息,则正亦不留,故心无所著。”又说:“本对偏病,是故有中。偏病既除,中亦不立。非中非偏,为出处众生,强名为中,谓绝待中。故此论云:‘若无有始终,中当云何有?’经亦云:‘远离二边,不著中道。’即其事也。”(《三论玄义》卷上。)见破除二边之后,不能住于中道,要“病除”、“药遣”,原是中道观的固有之义。值得注意的是,吉藏还在他的著作中讲“三重二谛”、“四重二谛”。《二谛义》说:“言诸法有者,凡夫谓有,此是俗谛,此是凡谛。贤圣真知诸法性空,此是真谛,此是圣谛。……次第二重,明有无为世谛,不二为真谛者,明有无是二边……不二中道为第一义谛也。次第三重,二与不二为世谛,非二非不二为第一义谛者……此亦是二边,何者?二是偏,不二是中。偏是一边,中是一边,偏之于中,还是二边,二边故名世谛;非偏非中,乃是中道第一义谛也。”(《二谛义》卷上)种“三重二谛”的论述形式和彻底不滞著的思想,对成玄英重玄之道“遣有遣无又遣中”的三翻式和彻底否定方法不无启迪。
至此,成玄英“重玄之道”的基本内容大致清楚了:先以“一中之玄”遣有遣无,继以“重玄之道”遣“药”遣“中”。从层次上看,是自“一玄”到“重玄”递进式两重;从逻辑结构看,则是遣有、遣无又遣中的三翻式,类似于否定、否定再否定。其中透露出一股十分强烈的否定一切,不染一尘,不著一物的空灵气质。
用具有这种气质的思想去解说《老子》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自然会被染上空无色彩。对《老子》的基本概念“道”的解说就是明显的例证。《老子》视道为万物之本原,它虽赋予道以“恍惚”、“寂寥”、“窈冥”、“玄同”等难以捉摸的性质,但却认为它恍惚中有“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即赋予其某种可被人们感知的实在。且肯定它是天、地之“母”,天、地、万物和人等实体都是从道中产生出来的。可见老子之道有着某种物质实体的属性。然而经过“重玄”化后的道则不同了,它不仅具有“虚通”性质,而且具有“假”、“空”性质。如说:“玄道妙本,大智慧源,超绝名言,离诸色象。”“夫至道虚通,妙绝分别,在假不假,居真不真,真假性齐,死生一贯。”“至道绝言,言即乖理,唯当忘言遣教,适可契会虚玄也。”“妙语诸法,同一虚假,不舍虚假,即假体真。”“怀道圣人,妙体虚假。”“复于真空,归于妙本。”成玄英笔下这种充满虚、假、空性质的道,与《老子》之道已大异其趣,很难想象能从其中产生出天地万物来,倒与佛教的“寂灭”、“涅?”很相似,这是带着假、空特色的虚无之道。
成玄英除从佛教汲取“二谛”、“中道”,建立虚无主义的宇宙观外,又从佛教汲取“无分别”、“无差等”、“八不”等思想,建立“心无分别”、“自他平等”的折衷主义方法论。他谴责常人所具的能分别真伪、善恶的“分别之心”,“分别之智”,宣扬不分是非,不辨黑白,“自他平等”的宗教理念,并广泛引用佛教“八不”思想以加强此理念。如论“物”、“道”关系时说:“悟即物道,迷即道物。道、物不一不异,而异而一。不一而一,而物而道。”论道的“希夷微”性质时说:“真而应,即散一以为三;应而真,即混三以归一。一三三一,不一不异,故不可致诘也。”“用此非无非有之行,不常不断之心”,作为“修道之要术”,要“量等太虚,无来无去,心冥至道,不灭不生”,才能与道长久,这些都充满着抹杀矛盾,折衷调和的强烈倾向。
用这种思想去分析事物(矛盾),自然只能抹杀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泯灭其应有的界限。成玄英在疏解《老子》中诸多矛盾范畴时,正是这样做的,把本来矛盾的事物说成“不殊”,将《老子》本有的某些辩证因素剔除净尽。如疏“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等句时,把本来对立的“善、恶”,“美、丑”概念,说成是没有分别的,其“分别”乃是凡夫“耽滞诸尘”、“执迷”的结果,谓“善恶源乎一心,忘者知其不殊,执者肝胆、楚越”。“不知诸法,即有即空,善恶既空,何憎何爱?”“唯当忘善恶而居中,方会无为之致也。”意即善恶并无分别,善即恶,恶即善。疏“有无相生”句时,谓:“有无二名,相因而生,推穷理性,即体而空。既知有无相生,足明万法无实。”意即有、无之本体都是空的,因而是没有区别的。疏“长短相形”句时,谓:“以长形长则无长,以短比短则无短,故知长短相形而有者也。”把《老子》长短相比较而显长、短的思想,变为“无长”、“无短”的同一。疏“高下相倾”句时,释“相倾”为“相夺”,谓“高下竟无定相,更相倾夺,所以皆空也”。用高下相倾夺而成空,以抹杀高、下之区别。疏“声音相和”句时,谓:“宫商丝竹,相和而成,推求性相,即体皆寂。”用佛教物无性相的观点,将有声音说成为没有声音(皆寂)。疏“先后相随”句时,谓:“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名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岂有今哉!既其无昔无今,何先何后?是有先有后者,三时相随,而竟无实体也。”以“今自非今”,“昔自非昔”等诡辩手法,抹杀今、昔区别,得出无昔无今、无先无后的结论,如此等等。不仅如此,成玄英还以佛教“性空”、“无差等”观点否定车、树及人身等的实有,谓“车是假名,诸缘和合,而成此车。细析推寻,遍体虚幻”,谓“若推此树,起自虚无,即空而言,树亦非有”,谓“善摄生之人,忘于身相,即身无身”,“圣人不执身为身,忘怀迷执,故能出三界。凡夫为执迷是非,心恒起灭,因斯迷倒,故入六道”( 以上皆见成玄英《道德经义疏》)要求道士“不执身”而“忘身”,这与道教“贵生”,追求肉体不死的根本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倒与佛教追求的“寂灭”解脱相吻合。故《道德经义疏》中用许多字讲述“三业清净”、“六根解脱”,就毫不奇怪了。至于《道德经义疏》中对违顺、毁誉、是非、荣辱、物我、境智、亲疏、祸福等诸多矛盾的解释,无不使用“性空”、“无分别”等观点,使之一一变为没有差别,“一味平等”的空无之物。
总括上述,可见成玄英的“重玄之道”,确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面貌出现在初唐道教舞台上。这是佛、道融合在道教方面的重要产物。它表明道教融合儒、释已开始突破照搬照抄的低级阶段。初唐道士李荣(与成玄英同时代)的《道德真经注》,武周道士孟安排的《道教义枢》以及隋代所出《太玄真一本际经》等书中,也有重玄思想,此不赘述。
除重玄派道士外,其他融佛入道的道士在唐代尚有不少。王玄览是其中的著名代表。他活动于唐高宗至武周朝,对佛、道“二教经论,悉遍披讨”( 《玄珠录》卷前王太霄序,见《正统道藏》第39册。)曾有著作多种,皆已失传,现仅存经人整理的言论记录《玄珠录》两卷,可概见其思想。该书讨论的问题很广泛,但从讨论的命题、思维方式,到语言文字,无不表现出浓厚的佛教(主要为唯识宗)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