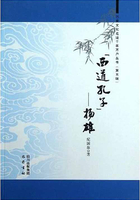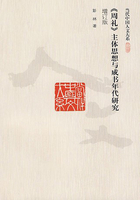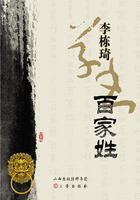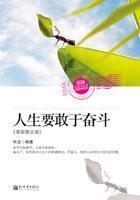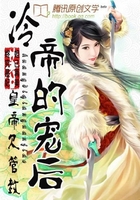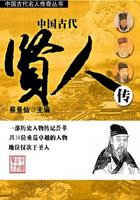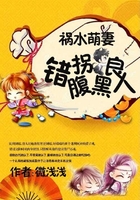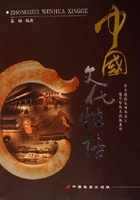清人针对宋人的以意逆志诠释所作的限定,是其汉学立场的产物。清代学者有意识建构汉学与宋学的学术对立,并逐步形成了汉学主流的学术范式。《四库全书总目》就是用“汉学”、“宋学”来描述清代学术发展,“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虽然《四库》馆臣主张“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但实际上“四库馆就是汉学家的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的汉宋之争,到了开四馆而汉学家全占胜利,也可以说是:朝廷所提倡的学风,被民间自然发展的学风压倒”。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显示了汉学视野中的以意逆志命题。宋人王质编撰《诗总闻》,把其特征称为以意逆志,这是宋人与清人的共识;但对这种以意逆志方法的理解与评价在宋与清人之间呈现巨大差异。宋人陈日强称:“其删除诗序,实与文公朱先生合。至于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真能寤寐诗人之意于千载之上,斯可谓之穷经矣。”《四库提要》则强调“日强《跋》称其‘以意逆志,自成一家’,其品题最允。……然其冥思研索,务造幽深,穿凿者固多,悬解者亦复不少。故虽不可训,而终不可废焉”。
宋人与清人的所论反映了其对王质《诗总闻》的评价差异,同时也显示了其对以意逆志命题、以意逆志方法的不同理解。虽有朱彝尊强调:“诗三百古序其来已旧,后儒以辞害志,如咸丘蒙高叟之辈。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学诗心法。孔子与赐商言诗意正同然。则知诗未有如孟子者矣。”其论《诗总闻》:“盖本孟子以意逆志之旨而畅所欲言……虽近穿凿而可以解人颐者亦多也。”还有王士禛认同宋人评判的“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真能寤寐诗人之意于千载之上,斯可谓之穷经矣”。但清代论者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显示的新观念是限制以意逆志命题所含方法观念的有效性。
严粲认为:“诗之兴几千年于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会孟氏说诗之法,涵泳三百篇之性情,则悠然见诗人言外之趣。毛郑以下且束之高阁,此书覆瓿可也。”因此,“集诸家之说为《诗缉》。旧说已善者,不必求异;有所未安,乃参以己说。要在以意逆志,优而柔之以求吟咏之情性而已”。“执诗之辞而不能以意逆志,固哉。说诗风人之旨远矣”。
严粲认可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显示的方法观念,并明确使用以意逆志方法说诗,宋人也是这样认识其方法特征的。宋人林希逸在《诗缉·诗缉原序》引“以意逆志”强调严粲“逆求情性于数千载之上”、“以诗言诗”特征。而《四库提要》高度评价严粲《诗缉》为“宋代说《诗》之家,与吕祖谦书并称善本,其余莫得而鼎立,良不诬矣”。则不用以意逆志描述其方法特色,突出其“凡若此类皆深得诗人本意。至于音训疑似,名物异同,考证尤为精核;非空谈解经者可比也”。
在批评宋学的同时,《总目》对汉学采取了明显的褒扬态度,推崇汉学的征实,把“考证精核”奉为正宗。在其看来,“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因而,《总目》对讲求文字、音韵、训诂、考证,力图恢复经书原貌和圣人原意的清代汉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四库馆臣突出“以意逆志”特色的《诗经》学论著,都是其视野中被批判的宋学特质的论著。
其评明沈守正《诗经说通》:“持论多茫无考证,故所引皆明人影响之谈。虽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拘牵,而纯以公安、竟陵之诗派窜入《经》义,遂往往恍惚而无著。”称明万时华《诗经偶笺》:“大旨宗孟子以意逆志之说而扫除训诂之胶固,颇足破腐儒之陋;然诗道至大而至深,未可以才士聪明测其涯际,况于以竟陵之门径掉弄笔墨,以一知半解训诂古经。”论明贺贻孙《诗触》:“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说,每曲求言外之旨,故颇胜诸儒之拘腐。而其所从入乃在钟惺诗评,故亦往往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不免失之佻巧。所谓楚既失之齐亦未为得也。卷首冠以四论。其第三篇论淫诗,第四篇论风刺皆为有见。第二篇论以意逆志是其全书之根本,而涉于掉弄聪明,全书之病即坐于是。”
《四库全书提要》不仅对呈现以意逆志方法特色的明代《诗经》学论著持批判态度,其论清人秦松龄《毛诗日笺》也是强调:“宗《孟子》‘以意逆志’之旨,多不依《小序》,因取欧、苏、王、吕、程、李、辅、严诸家,以及明郝敬、何楷、近时顾炎武之言,互相参核,而以己意断之。不专主《小序》,亦不专主《集传》。凡有疑义,乃为疏解,亦不尽解全诗,故曰《日笺》。王士禛《居易录》云:‘秦宫谕所辑《毛诗日笺》,所论与余夙昔之见颇同,其所采取亦甚简当。然大旨多以意揣之,不尽有所考证也。’”不仅批判以意逆志说《诗》的论著,还评价明颜廷矩撰《杜律意笺》的立场:“名曰《意笺》,盖取以意逆志之义。其讥伪虞注之草草,持论良是。然核其所解,与伪虞注正复相等也。”
这种解说包括《诗经》在内的诗歌作品,限制以意逆志方法的有效性,是汉学的产物,也是时代的主流。不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显示了其汉学立场上限制以意逆志方法有效性,而且清初阎若璩强调“以意逆志,须的知某诗出于何世与所作者何等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顾镇关注“故必论世知人而后逆志之说可用之”,显示了时代知识共识建构。王夫之主张“凡此类求通于诗意,推详于物理,所谓以意逆志而得之,虽尽废旧说而非僻也”,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服务于“以理审之,以意求之,以事征之,以文合之”的推理与实证相结合建构“考证精核”之学术目标。
正是在这种知识背景中,清代注释诗歌多宣扬方法。其中有不少主张以意逆志方式,但都强调得意难,其主张以意逆志是在知人论世的前提下展开。朱鹤龄认为:“义山之诗,原本离骚……原之耿介,能无怨乎?怨而不忍直致其怨,则其辞不得不诡谲曼衍。而义山一祖其杼轴以为诗,以故瑰采惊人,学者难以逆志。”因此提出“学者不察本末……此不能论世知人之故也”。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以为:“注而不笺,则非子夏三百篇小序之旨,又不得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义。”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主张:“以征典为注,达意为笺。……说诗最忌穿凿,然独不曰:‘以意逆志’乎?今以‘知人论世’之法求之,言外隐衷,大堪领悟,似凿而非凿也。”程梦星提出“以意逆志,有见则笺”,是将“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结合起来。清人笺释李商隐诗的方法,大致而言,是继承朱鹤龄的“论世知人”笺释方法而加以发展。而这样的笺释方法,到了程梦星时,更结合了“以意逆志”的解诗法,以补“知人论世”的不足。自此,“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成为这个笺释系统的主要方式。朱鹤龄、程梦星、冯浩等都属于这个笺释系统。这种“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相结合的笺释方式,正反映了清人将“诗史”与“比兴”合一的笺释观念。
清人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中的“意揣”、“吾意逆”的解释与私意、公论之说显示了语言变化、观念转变等因素对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影响,但学术转向是影响清代论者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关键因素。虽然与汉代赵岐具有共同的汉学立场,接受了己意以求的以意逆志命题语义;但在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背景中,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是放在孟子思想整体中限制其范围,在知人论世前提下限定其有效性。虽然与宋代论者同样主张反对私意,但在清代考据学的为学观念中,清代论者建构的是知人论世的诠释思想,而非宋学平心以待的诠释观念。
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转向使得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在知人论世框架中展开,呈现了汉宋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语义扩展方法基础上边界限定的新诠释方向。
二、文化转型与现代以意逆志诠释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研究中建构的是作为历史事件的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是在历史事件的基础上考辨其理论内涵与审视其历史价值。
孟子对“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是分别谈的,但二者实有密切的联系。……顾镇……王国维……这种推论和解释,是较为符合于孟子的原意的。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在理论上是可取的,但由于思想的局限,在在解释某些具体作品的时候,往往流于牵强附会和阶级偏见……
现代论者认同清代强调知人论世前提下以意逆志有效性的论说,接受了其在孟子思想整体中限定边界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方法。但同时,现代论者开始了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一个新的方向,那就是把以意逆志命题作为一种历史对象来加以认识,并在现代观念立场上加以批判。这种边界限定的诠释方式首先是因为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所属学科的转变。
现代学术体系中论说以意逆志命题,是从历史学学科开始的。以意逆志论题分布在传统学术体系之《诗经》学、四书学、诗文评等分类之中。“从中国传统文史哲不分的‘通人之学’向西方近代‘专门之学’转变,从‘四部之学’(经、史、子、集)向‘七科之学’(文、理、法、商、医、农、工)转变,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变的重要标志。”随着传统学术体系向现代学术体系转变,关于以意逆志的论说逐渐统一在现代学术框架中的历史学学科之中。
顾颉刚就是在古史研究的论题中关注以意逆志论题。他认为,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命题意义在于“有了客观的态度,才可以做学问,所以他这句话是诗学的发端”,强调“孟子能够知道‘尚友论世’、‘以意逆志’,对于古人有了研究历史的需求,确然比春秋时人进步得多了”。在1926年编入《古史辨》第一册的《论〈诗经〉经历及〈老子〉与道家书》一文中,顾颉刚仍关注“孟子会说‘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但他自己是最不会‘论世’和‘逆志’的”历史状况。顾颉刚关注历史的态度正是其在《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中所强调的,“我们对于国故的态度是‘研究’而不是‘实行’”。
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集中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论题中。陈中凡提到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观念背景:“1921年8月至1924年11月,任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对当时的学衡派盲目复古表示不满,乃编国文丛刊,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郭绍虞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强调:“当时人的治学态度,大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有很多帮助。”所谓“科学方法”,指的是论者所接受的西方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论。在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文化主流与学科建构背景中,20世纪初期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从传统《诗经》学、《四书》学与诗文评学科转向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
在整理国故的视野中,郭绍虞强调:“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即使对于昔人之说,未能惬怀,也总想平心静气地说明他的主张,和所以致的缘故。因为,这是叙述而不是表彰,是文学批评史而不是文学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
但以历史、客观、科学等话语系统叙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不仅是文学批评史之历史的说明、叙述,而且包含着文学思想之批评与表彰的价值评判。现代“科学方法”背后依靠着现代价值立场,客观科学不仅是诠释以意逆志命题的立场,也是批判以意逆志方法意识的标准。以客观、科学等术语支撑的标准成为衡量以意逆志命题意义的观念基础。郭绍虞的这种论说方式与论说话语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诠释以意逆志命题的基础,并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近半个世纪诠释的主流。
照他这种以意逆志,对于纯文学的了解,确是更能深切而不流于固陋。可是他这种以意逆志,全凭主观的体会终究不是客观研究的方法。
偏于唯心思想的孟子利用它来论诗,那就从科学的推断,变为不科学的主观的臆测,而是文学批评上也就起着不良的影响。
修辞上的夸饰是不能拘泥着看的。所以以意逆志的方法不能说有什么错误。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这是更重要的更客观的研究方法。
这种“以意逆志”的方法,虽不甚科学,虽然只是主观的探索,然诗人由热烈的感情之火所迸出来的诗句,是很容易言过其实的,“以意逆志”,确是刺探作者深心的好方法,同时也是认识诗的必需途径。……对小弁凯风的解释,还是很客气的“以意逆志”;对于其他各诗的解释,则完全走到“断章取义”的道上;假使硬说是“以意逆志”,那我们只有说是太不客气的“以意逆志”了。
现代论者以客观、科学为核心标准衡量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及其显示的方法。客观科学不仅是其处理孟子命题所显示的态度与方法,也是处理一切对象,包括文学在内的对象遵循的方法。因此,客观科学不仅成为建构以意逆志命题的方法(以意逆志作为孟子历史的产物凸现出来),而且是衡量以意逆志显示方法观念的评判标准(以意逆志方法被凸现主观臆测的不足),还是以意逆志命题内涵表述的基本话语(在主观、客观的语义场中言说以意逆志命题内涵)。
虽然认同孟子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结合的理论有效性,显示了清人论说的延续,但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说中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更凸现现代论者批判传统的文化选择。而这不同于清人否定宋儒去序言《诗》,批判其以意逆志方法误用,却并不否定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本身。因此,现代论者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显示的主观臆测批判也不同于清人强调孟子的本意是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统一。
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从传统学术体系中的《诗经》学、《四书》学、诗文评学科转向现代学术体系中的历史学科,这种从经学视野转向史学视野的学术转向也是影响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域中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重要因素;同时,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语言变化等因素也影响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但这一切因素是在文化转型的基础上产生作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在历史整体中限定边界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方式来源于文化转型。
文化转型带来了社会生活、学者身份、生存体验等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在知识层面上,开始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呈现了文化之整体知识系统和知识质态的全面切换。“由于中西知识谱系的整体切换,本世纪传统知识的研究主要是在西学之分科切域的目光下的肢解性研究,重心是用西学的逻辑视域、知识点和分析方法对传统知识作分析、甄别、确认、评价,实质是将传统知识‘翻译’为分析质态的西学知识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