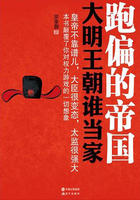《离骚》虽不难通读,但不易读透。严羽《沧浪诗话》云:“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
否则,为戛釜撞瓮耳。”
巫学给艺术带来狂怪直率的意绪,道学给艺术带来睿智玄妙的理念,骚学给艺术带来高洁绮丽的情思:此三者,屈原兼而有之。
用现在惯用的术语来讲,屈原的作品饱含着浪漫主义精神。然而,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不是寻常的浪漫主义,它不是对古典主义的反叛,它与西方的浪漫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它来自巫的怪想,道的妙理,骚的绮思,三者交融,以至迷离恍惚,汪洋恣肆,惊采绝艳,比寻常所谓浪漫主义更为浪漫主义。
人民怀念屈原,过端午,裹粽子,赛龙舟,本来与屈原无涉,后来都变成纪念屈原的风俗了。诚如李白诗《江上吟》所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中,唐勒除姓名外,一概不详。景差可能与宋玉同时,但未见有可靠的传世之作。一说《大招》为景差所作,但从王逸为之加注时起就有争议。《楚辞章句》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宋玉生活在顷襄王时,其传世之作,公认的大致可以说有《九辩》,真伪莫辨的有《楚辞章句》所收的《招魂》和《文选》所收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襄王问》计六篇。这六篇都是大手笔,除《招魂》可能为屈原所作外,另五篇的作者似非宋玉莫属,他人恐不足以当之。
宋玉景仰屈原,哀其志而慕其文。与屈原的作品相比,宋玉的作品格调略嫌卑弱,巫学和道学的成分较为淡薄,但自有其清新、细腻之妙。
前人对宋玉的品节和辞赋都有很高的评价,以为与屈原差可比肩。李白诗《感遇》四首之四云:“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感登徒言,恩情遂中绝。”杜甫诗言及宋玉者更多,其《咏怀古迹》五首之二有句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其《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郑侍御判官重赠》有句云:“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其《戏为六绝句》之五有句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今人对宋玉的评价,与前人对宋玉的评价相比,显然是减色了。
这是因为今人有什么新的发现吗?不是!宋玉依然故我,只是当代的风气和今人的心态都不古了。
(第八节庄的暴郢和入滇
怀襄之际有一位神秘的人物,他在楚国历史上一掠而过,如天马之行空。古人说他是剧盗或者是良将,今人则有说他是农民起义领袖的。无论古人、今人,都有怀疑他不止一个人,而可能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的。这位神秘人物就是庄。
最早记录庄其人其事的文献是《荀子》、《韩非子》、《商君书》和《吕氏春秋》,都成书于战国末期。《荀子·议兵》说:“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起,楚分而为三四。”《商君书·弱民》所记与此大同小异。《韩非子·喻老》说到庄曾“为盗”,“吏不能禁”。《吕氏春秋·士节》说到庄曾“暴郢”。这些零星的记载所能提供的信息是:官方称庄为“盗”,此其一;庄曾经在郢都作乱甚至造反,此其二;楚国一度因庄作乱而失去对地方的统一号令,以致有些地方各行其是,此其三;庄起事是在楚怀王二十八年齐、韩、魏合兵攻方城、杀唐蔑之后,此其四;以庄为氏,应是楚庄王后裔之氏于谥者,此其五。《荀子·议兵》又说:“齐之田单,楚之庄,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可见,庄以善用兵知名,此其六。
《史记·西南夷列传》另有一说,其文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者,故楚庄王苗裔也。
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有同有异,其文曰:“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滇王者,庄之后也。”前称“庄豪”,后称“庄”,显然是同一个人。参照其他文献,应以庄为正。
第一个问题———庄入滇的传说是否可靠?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曾“奉使南征巴蜀以南”。庄入滇的传说,应是他在巴蜀以南采集的。既然滇王自称如此,想来不会是杜撰的。滇楚之间,隔着一个夜郎。如果滇王不是庄的后人,那么,他们数典忘祖,偏要越过夜郎去冒请楚国的一位剧盗做自己的始君,就完全不合情理了。
第二个问题———庄入滇的年代。《史记》以为在楚威王时,唐人杜佑已在《通典》中指出其谬误,理由是从楚威王末年到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取黔中郡“凡经五十二年”,庄的寿命长得令人碍难置信。上文据《荀子·议兵》,指出庄入滇应在楚怀王二十八年以后,则《后汉书》以为在楚顷襄王时是可能的。
第三个问题———庄入滇的路线。《史记》说是“循江上”,《后汉书》说是“从沅水”。“循江上”,若不取道清江流域的五姓巴人方国,则必取道乌江流域的七姓巴人方国,这谈何容易!“从沅水”,即经由黔中郡,可绕过上述两个巴国,循沅水支流水西上入夜郎。
且兰在今贵州黄平一带,临水上游的阳河。且兰以西,改舟行为陆行,虽道路崎岖,但入滇尚称便利。
第四个问题———庄到底是剧盗还是良将?综理有关资料,应该承认他又是剧盗,又是良将,论行径是剧盗,论才能是良将。至于说庄是农民起义领袖,则全无所据。
第五个问题———庄入滇是否王命所遣?按,庄曾作乱暴郢,即使失败后降服了,也不可能俯首帖耳听从王命到深险莫测的云贵高原上去。唯一近情合理的解释是庄兵败后受楚师追击和围歼,不得不落荒而走,遁入夜郎,辗转至于滇国。庄断然不会对夜郎和滇国的土著承认自己是败逃的盗首,只会狐假虎威,冒称乃王命所遣之将军。
考证和论述庄的文章,迄今已有数十篇问世。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刘玉堂所作的《论庄其人其事》。
庄虽落荒而走,但对路线不是心中无数的。庄所走的是横穿云贵高原的一条先秦古道,其东端在楚国的郢都,其西端在摩揭陀王国的首都华氏城(今印度巴特那),也可以说,东起长江中游,西至恒河中游。这是南方的“丝绸之路”,比北方的“丝绸之路”早二百年左右甚至更久。有没有证据呢?有的。第一个证据是玻璃珠和石髓珠,第二个证据是古印度的商那阎的著作《政论》。
古代的玻璃珠或称琉璃珠,有色,半透明。“琉璃”一词始见于西汉,但据史树青考证,楚辞所谓“陆离”应即“琉璃”,其说成理。从湖南、湖北两省的战国楚墓和曾墓中,出土了许多号为“蜻蜓眼”的多色玻璃珠。这类玻璃珠通常为球形,少数为圆中见方的球形,个别为多角的球形,有孔。在每颗玻璃珠上,都有若干眼珠纹,每个眼珠纹都由一个圆点的蓝色套上一个或几个圆圈的白色构成,各个眼珠纹之间为朱色或绿色等。这样,外观就活像“蜻蜓眼”了。这类玻璃珠的装饰风格,与中国传统的装饰风格迥乎异趣,与西亚、南亚的同类玻璃珠则全然相像,而西亚、南亚的同类玻璃珠较为早出并且更为多见。古代中国的玻璃是所谓铅钡玻璃,古代西亚和南亚的玻璃是所谓钠钙玻璃。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所出的一颗“蜻蜓眼”是钠钙玻璃。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句践剑剑格上镶嵌的玻璃,以及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剑格上镶嵌的玻璃,也是钠钙玻璃。这就可以证实那些“蜻蜓眼”最初应是从南亚进口的,后来才有楚国仿制的。国外考古学界认为:“琉璃”可能是梵语vaidu-rya的音转,原指绿柱石之类有青、绿、紫诸色的宝石,借指外表类似这些宝石的玻璃珠。
“蜻蜓眼”虽集中在楚地,但零零散散地流播到了北方。东起山东曲阜,西至陕西大荔,都有“蜻蜓眼”出土,然而寥若晨星。
公元前320—315年间,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的大臣商那阎著有《政论》一书,其中说到有从中国运去的丝。这丝,从中国北方运去的可能性很小,因为那要在一个多边形上走完几条边线才能运到;从中国南方运去的可能性则很大,因为只要在一个多边形上走完一条边线就能运到了。蜀地虽则也产丝绸,可是直到西汉,蜀地出口到南亚的还只有麻布而没有丝绸,由此可知,摩揭陀王国的丝应是从楚国运去的。
从楚国到摩揭陀王国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海路,一条是陆路。走海路,至今无证据;走陆路,却有蛛丝马迹可寻。所谓蛛丝马迹,就是云南出土的石髓珠和玻璃珠。据张增祺研究,这些石髓珠和玻璃珠是从西亚经南亚进口的,年代最早的在春秋战国之际。上文曾谈到的句践剑和夫差剑都是春秋晚期的,但据后德俊研究,剑格上面的玻璃大概是战国时代才镶嵌上去的。侯古堆1号墓所出的“蜻蜓眼”,则无疑是春秋晚期的原物。由此可知,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或许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开通了。纵贯在今中缅边界两侧的横断山脉,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难于通行。直到20世纪60年代,马帮走山间小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从云南西北部到印度东北部,走上半个月也就到了。
西亚和南亚的玻璃珠,越过横断山脉,穿过云贵高原,运到了楚国,黔中郡的楚人自然知道有这条商路存在。到了黔中郡的庄及其部属,才会在知情人的指引下,走上这条不无风险的古道。
到现在为止,先秦中外文化交流的唯一确凿的物证就是上述“蜻蜓眼”玻璃珠,读者不难想见,其可贵也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