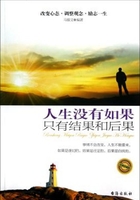古希腊只有三种乐器———两种弦数不同的竖琴和一种双管芦管,可以为唱诗者伴奏,然而不能合奏。明乎此,就不难了解楚国在音乐领域内是何等超轶绝尘了。艺术愈抽象,楚人就愈擅长。他们拙于叙事诗,而巧于抒情诗;拙于毫不抽象的雕刻,而巧于全然抽象的音乐。
先秦的十二律名见《国语·周语》,当然是周十二律。楚自有其十二律名,与周十二律名只有一个姑洗是相同的。
先前,礼与乐“相须为用”,如《通志·乐略》所云:“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到了楚文化的鼎盛期,礼崩乐坏之势已无可挽回。乐舞所娱的对象,不再以神为主了,在贵族中是以人为主,在平民中是神与人共之。《招魂》和《大招》所描写的,即以人为主;《九歌》所描写的,则为神与人共之。进入战国中期之后,轻松活泼的鼓乐和管乐、弦乐日盛一日,使庄严典雅的钟磬为之黯然失色。
楚文化很有开放性和创造性,楚乐舞也这样。《招魂》和《大招》说到的“赵箫”、“郑舞”、“吴歈”、“蔡讴”和“代、秦、郑、卫”等,都是楚人引进的异族、异国的乐舞。同时楚人发展了描摹楚乡风情、显示南国风韵的乐舞,即《涉江》、《采菱》、《扬荷》 (《扬阿》)、《劳商》、《激楚》等等。《激楚》在楚国宫廷乐舞中的地位,犹如唐代梨园的《霓裳羽衣》。《招魂》云:“宫庭震惊,发《激楚》些。……《激楚》之结,独秀先些。”“宫庭震惊”的原因,或许是乐声大作,令人不禁心动神摇吧!“结”同“髻”,是舞女的发式。演出《激楚》的舞女,发式特别时髦。从楚乐舞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说越有开放性就越有创造性。
《文选》所录传为宋玉所作的《对楚王问》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虽说“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毕竟雅俗兼备,是以各尽其欢。
楚人的舞态,如《九歌》所描写的,有“偃蹇”、“连蜷”之美,有“翾飞兮翠曾”之妙,虽可意会而不易名状。1941年长沙黄土岭战国楚墓出土彩绘漆奁一件,上有《小胥憩舞图》:“细腰舞女11人,莫不广袖长袍,或正在练功,或正在小憩。”湖北省歌舞团创作和演出的《编钟乐舞》,女演员多作“三道弯”身姿,模拟楚舞,可谓庶几近之。
(第七节屈原和宋玉
屈原,名平,后人多称其字,约生于公元前340年,约卒于公元前277年。屈氏在楚国曾是一个显赫的家族,春秋时代世选莫敖,战国时代渐趋衰微。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记,屈原早年受到了良好的正统教育,“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壮岁入仕,“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然而为佞臣所不容。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列,向怀王进谗,诬屈原贪怀王之功以为己有,怀王由此而疏远了屈原,乃至免其左徒之职。
秦大破楚于丹阳、蓝田之后,屈原受命使齐以修好。回郢都后,一再进谏,始则劝怀王杀张仪,继而劝怀王不入秦,怀王俱不从。顷襄王即位后,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掌公族子弟的教育。不久又受谗见斥。郢都沦陷以后,屈原流徙于江南,抱石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典范永垂。他爱国,也爱民。他爱自己所出生的乡国和自己所奉仕的君国,也爱号为九州之地的祖国。
他志洁行廉,抗“溷浊”之世,违“工巧”之俗。在古代爱国者之群中,屈原如木秀于林,至今为人们所崇敬。
屈原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丰碑长存。在博采南北民歌精华的基础上,他创立了从内容到形式都令人耳目一新的楚辞。在抒情领域内,屈原的作品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无来者。西汉末刘向编集屈原作品凡25篇,东汉初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记屈原作品正是25篇。晚于班固的王逸作《楚辞章句》,所录屈原作品也是25篇。屈原的全部作品虽不止此数,但25篇之外的都失传了。25篇之中,《远游》、《卜居》、《渔父》,近人多疑为非屈原所作。25篇之外,还有《招魂》和《大招》可能为屈原所作。
大致无争议的屈原作品是:《离骚》、《九歌》(11篇)、《九章》(9篇)、《天问》。
《离骚》是屈原的主要作品,后人或简称之为《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心雕龙·辨骚》评《离骚》和其他楚辞作品,其结句云:“……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司马迁之所论,重在思想;刘勰之所论,重在艺术:合而观之,大致就表里兼得了。
对于屈原的学术,我们不妨称之为骚学。
楚国本来只有巫学,自从楚文化进入鼎盛期之后,巫学才开始分流:其因袭罔替者仍为巫学,其理性化者转为道学,其感性化者转为骚学。楚国的强盛加剧了大国与小国的矛盾,贵族与平民的矛盾,以及国人与野人的矛盾,某些处在中间地位的有识之士谋求解脱,这是巫学理性化而为道学的历史背景,时当春秋晚期与战国早期之际。楚国社会的兴旺以至烂熟引发了双重危机,内有痼疾的消磨,外有勍敌的凭陵,贵族中的有识之士谋求拯救而不得行其道,这是巫学感性化而为骚学的历史背景,时当战国中期与晚期之际。
道学是上文已介绍了的,骚学则是本节所要介绍的。
从禀赋和素养来看,屈原实在是一位大巫。《离骚》足以证明,屈原熟知神话,深钦神巫,善作神游。屈原与一般楚国大巫不同的是,他把郢中巫学和稷下道学糅合起来了。《离骚》有云:“耿吾既得此中正”,“溘埃风余上征”。王逸《楚辞章句》注曰:“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与化游。”“真人”,在《庄子》中等于“至人”。
《庄子·田子方》云:“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稷下道家的作品《管子·内业》以为心内精气饱满,“乃能穷天地,被四海,中无惑意,外无邪菑”。能达到这个境界的,便是“真人”、“至人”,其尤“真”尤“至”者为“圣人”。
《离骚》和《九歌》、《九章》是抒情诗歌无可逾越的高峰,后人虽欲效之而终不能及。这是因为后人的才情一概不如屈原吗?
不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两千多年来难以数计的骚人墨客的才情难道个个不如屈原?答案在于后人没有屈原那样的郢中巫学根底和稷下道学根底,虽欲效之,只能是效颦、学步,因而终不能及。
古往今来,对于屈原的特立独行,有褒有贬,年代愈晚则褒之者愈多而贬之者愈少。
西汉的扬雄不以屈原自杀为是,《汉书·扬雄传》说:“杨雄……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沉)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反离骚》有句云:
“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
东汉的班固比扬雄更进一步,在《<;离骚>;叙》中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8云:“余观渔父告屈原之语曰:
‘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又云:‘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淈其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此与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异?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于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偏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孟郊曰:“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孙邰云:‘道废固命也,何事葬江鱼?’皆贬之也。而张文潜独以谓:‘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渔父由来亦不仁。’”
南宋费衮《梁谿漫志》卷5“《通鉴》不载《离骚》”条云:“予谓三闾大夫以忠见放,然行吟恚怼,形于色词。扬己露才,班固讥其怨刺。所著《离骚》皆幽忧愤叹之作,非一饭不忘之谊,盖不可以训也。若所谓与日月争光者,特以褒其文词之美耳。温公(司马光)之取人,必考其终始大节。屈原沉渊,盖非圣人之中道。区区绮章绘句之工,亦何足算也!”把屈原贬得最低的,就是这《梁谿漫志》了。
今人则不然,对屈原大抵有褒无贬。司马迁对屈原的政见和政绩已有溢美失实之辞,今人则更有爱之唯恐不足而褒之唯恐不高的,甚至以为屈原是伟大的政治家和重要的思想家。至于这位政治家在楚国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这位思想家有哪些理论贡献,就谁也说不清楚了。
屈原是旷世奇才,但不是通才;屈原是绝代伟人,但不是完人。
凡第一流的诗人都不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只是政治上的失意和思想上的造诣可能加大艺术上的创获。前人也明白这个道理,陆游作《读唐人愁诗戏作五首》,其三云:“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