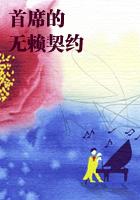塔塔先生的房间干净整洁,有条不紊,真是在太阳、月亮和星空下非常少见的。地板擦洗得干干净净,使你禁不住以为,伦敦的煤灰已经绝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塔塔先生的铜器,每一件都擦得亮堂堂的,跟黄铜镜子差不多。塔塔先生的家用器皿,不论大的、小的,还是不大不小的,都显得一尘不染,没有斑点,没有污垢,没有水渍。他的起居室像舰长的指挥舱,他的洗澡间像牛奶房,他的卧室四壁全是柜子和抽屉,就像一个种子商人的店堂,他那小小的吊床正好位于房间中央,微微地摇摆着,像是在呼吸一样。每一件属于塔塔先生的物品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地图和航海图有自己的位置,书籍有自己的位置,刷子有自己的位置,靴子有自己的位置,衣服有自己的位置,方瓶有自己的位置,望远镜和其他器械也都有各自的位置。每一件物品都随时可以取到。搁板、托架、柜子、钩子、抽屉,同样方便,也同样制作精巧,不占地方,又可以提供各种小小的空隙,储藏一些大小正好恰当的用品。他那套发亮的小盘子在餐具柜上排列得整整齐齐,哪怕有一把没精打采的盐匙混在中间,也会马上暴露出来。他的梳洗用品排列在梳妆台上,哪怕一根不修边幅的牙签在那里也会一眼就被人发现。他历次航海带回家的珍奇玩物也是如此。它们按照种类,用剥制、日晒、重新磨光,或者其他的方法保存着,其中有鸟、鱼、爬虫、武器、衣服、贝壳、海藻、禾本科植物,以及从珊瑚礁上采来的纪念品,每一件都陈列在各自的位置上,显得恰到好处,再合适不过。油漆和涂料好像始终藏在什么隐蔽的地方,每逢塔塔先生的房间里发现什么指印,马上可以用它们来消灭它。没有一条军舰会这么井井有条,干净整洁。在这晴朗的夏日,一个精致的遮棚吊在塔塔先生的花园上空,这是只有水手才会安装的。整个屋子给人一种即将开航的感觉,似乎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万无一失,花园也已经联结在船尾的窗外,浮在水面上,只要塔塔先生从墙角取下扩音喇叭,按到他的嘴上,用嘶哑的声音发出命令:起锚,小伙子们,拿出劲儿来,张开船帆!这整个屋子便会带着一切,在大海中乘风破浪地前进!
塔塔先生便在这只漂亮的小船上,尽他的主人之谊,他的作风与周围的一切完全一致。一个人不亢不卑、娓娓动听地介绍他的得意之作的时候,以幽默的口吻谈到它的滑稽的方面,总是特别引人入胜的。如果他天生是一个和蔼可亲、真诚纯朴的小伙子,同时又精力充沛,胸怀磊落,那么对他来说,恐怕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为令人倾倒的了。因此,罗莎(哪怕她上船时没有受到海军大臣夫人或者海上仙女的礼遇)看到和听到塔塔先生那么一半调侃、一半得意地解说着他的各种设计创造,自然觉得是一件无比的乐事。因此,罗莎在参观结束,这晒黑的水手彬彬有礼地退出舰长舱,把它移交给他的王后,举起那只搭救过克里斯帕克先生的手,向她致意,退出他的花园时,也自然觉得这个人真是可爱极了。
“海伦娜!海伦娜·兰德勒斯!你在那儿吗?”
“是谁在叫我?难道是罗莎吗?”于是第二张漂亮的脸蛋露了出来。
“是的,亲爱的!”
“啊,你怎么到这儿来啦,最亲爱的?”
“我——我也不太清楚,”罗莎说着,脸全红了,“我好像在做梦一样!”
为什么脸会红呢?因为这里只有她们两张脸,此外便是鲜花了。那么是给魔法豌豆顶上的仙境中的水果映红的吗?
“我可不是在做梦,”海伦娜微笑着说道,“如果我真的是在做梦的话,也让这个梦久一些吧。说真的,我们怎么会在一起的,而且这么近,这么意想不到?”
她们确实意想不到,会在P.J.T.附近那肮脏的三角墙和烟囱之间,在盐海中生长出的花朵中间相遇。幸好罗莎清醒了过来,于是便匆匆地把她们怎么会在一起的原因,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克里斯帕克先生也在这儿。”罗莎说着,迅速地结束了她的话,“你相信吗?很久之前,他救过他的命!”
“这对克里斯帕克先生来说并不奇怪,我自然相信。”海伦娜回答道,同时脸上也泛起了红晕。
(豆茎花园中多了一个红脸的人!)
“是的,但这不是克里斯帕克先生搭救别人。”罗莎说道,立即作了更正。
“我不明白,亲爱的。”
“这是克里斯帕克先生被别人搭救,不过那也是件好事。”罗莎说道,“他对塔塔先生真是赞不绝口,因为是塔塔先生救了他。”
海伦娜的黑眼睛热烈地望着叶子中间那张容光焕发的脸。她放慢了声音,更加关切地问道:“亲爱的,塔塔先生现在跟你在一起吗?”
“没有,他把他的屋子交给我了——我是说交给我们了。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
“是吗?”
“这好像是天下最精美的船舱。这好像——像——”
“像是一个梦?”海伦娜提示道。
罗莎微微地点了点头,闻了闻花香。
海伦娜沉默了一会儿,仿佛是在怜悯什么人似的(也许只是罗莎的幻觉),然后说道:“可怜的内维尔正在他自己的屋里读书,但是现在这一边的阳光这么灿烂。不过我想,还是不让他知道你在附近的好。”
“哦,我也这么想!”罗莎马上回答道。
“我想,”海伦娜继续有些犹豫地说道,“你告诉我的一切,慢慢地也应该让他知道,但是这样做对不对,我还没有把握。你去问一下克里斯帕克先生吧,亲爱的。你去问问他,你告诉我的事,我能不能把我认为应该告诉内维尔的部分告诉他。”
罗莎退回到房舱,进行了咨询。克里斯帕克先生认为,这可以由海伦娜自己决定。
海伦娜听到了罗莎带回来的答复,说道:“我非常感谢他。你再问问他,是不是等那个坏蛋对内维尔实施新的阴谋或者迫害时,让事情自行暴露,还是预先揭露他,也就是说,把他陷害我们的阴谋诡计事先调查清楚,我们怎么做最好?”
初级教士认为,很难对这一问题做出圆满的答复,在考虑了两三次,终于不得要领之后,他提议,不妨向格鲁吉斯先生请教。海伦娜同意了。于是他露出无所事事、出门散步的神态(只是装得一点也不像),穿过四方院子,走进了P.J.T.,提出了问题。格鲁吉斯先生坚决地表示,他的一般原则是,如果你能够出其不意,抢在一个土匪或者一只野兽之前动手,那就应该这样办。至于目前这个具体的事件,他坚决地认为,约翰·贾思伯就等同于土匪加上野兽。
征得这一意见之后,克里斯帕克先生便回到这儿,转告了罗莎,罗莎又转告了海伦娜。她正站在窗口,坚定地思考着一切,考虑着该怎么办。
“罗莎,我们可以相信,塔塔先生愿意帮助我们,是吗?”她问道。
“当然可以!”罗莎有些害羞地这样想道。当然可以,罗莎有些害羞地相信她几乎可以保证这一点。那么要去问问克里斯帕克先生吗?“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你的话跟他的话具有同样的权威,亲爱的,”海伦娜平静地说道,“你不必为这再去问了。”奇怪的海伦娜!
“你想想看,”海伦娜又考虑了一会,说道,“内维尔在这儿没有一个熟人,他在这儿根本没有跟谁谈过话。要是塔塔先生常来看他,公开与他来往,要是他肯拿出一些时间,不时地这样去做,甚至差不多每天都这样去做,那么一定会引起一些后果。”
“引起一些后果,亲爱的?”罗莎追问道,一边打量自己这位朋友美丽的脸,摸不清这是什么意思,“后果?”
“如果内维尔的行动真的受到了监视,如果他的敌人的目的真的是要孤立他,使他与一切的朋友和熟人隔绝,在寂寞中一天天地消耗生命(看来这就是你所听到的那个威胁),”海伦娜继续说道,“那么对方肯定会通过一定的途径与塔塔先生联系,警告他不得接近内维尔,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如果是这样,我们便不仅能够了解事实,而且还可以从塔塔先生那儿得知联系的具体情况。”
“我明白了!”罗莎喊道,马上又退回了房舱。
不久她那美丽的脸庞又出现了,脸色更加红润了,她说她已经告知了克里斯帕克先生,克里斯帕克先生把塔塔先生找来了,而塔塔先生——“他现在正在外边等着,因为也许你想要见他,”罗莎补充道,侧着半个脸向后面瞧了瞧,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不知道应该把脸朝着房舱内还是房舱外——声称,他愿意按照海伦娜的主意去做,而且今天就可以付诸行动。
“我衷心地感谢他,”海伦娜说道,“请你把这话转告给他。”
罗莎又变得有些不好意思,只得再度奔走于空中花园和房舱之间,带着海伦娜的口信钻了进去,又带着塔塔先生进一步的保证钻了出来,忸怩不安地站在她和他的中间,不过这可以证明,不好意思不一定就是出洋相,有时这也是一种惹人喜爱的表情。
“现在,亲爱的,”海伦娜说道,“我们得随时小心,目前的会面应该有一定限度,让我们就此分手吧。我听到内维尔在走动了。你要回去吗?”
“回特文科里顿小姐那儿吗?”罗莎问道。
“是的。”
“哦,我再也不到那儿去了。真的,自从那次可怕的会面之后,我再也不想去了!”罗莎说道。
“那么你打算到哪儿去呢,美丽的小姐?”
“说起这一点,我现在还不确定,”罗莎说道,“我还没有做出任何的打算,但是我的监护人会照顾我的。别为我担心,亲爱的。我一定可以找到安身之处的。”
(看来这是很可能的。)
“那么今后我就可以从塔塔先生那里听到我的玫瑰花的消息了?”海伦娜问道。
“是的,我想可以,可以从——”罗莎又有些不好意思了,向后瞟了一眼,没有说出名字,“但是在我们分别之前,请你告诉我一件事,最亲爱的海伦娜。请你告诉我,你完全相信,完全相信,我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亲爱的,迫不得已?”
“是的,他对你们的恶意报复都是我造成的。我不能接受他的任何条件,对吧?”
“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亲爱的,”海伦娜回答道,接着愤慨地说道,“我宁可看到你死在他邪恶的脚下,也不愿意看到你向他屈服。”
“那就让我太感激了!你会这么告诉你那可怜的弟弟,是吗?你会向他转告我的问候和同情吧?你会请他别恨我吗?”
海伦娜伤心地摇了摇头,仿佛这请求完全是多余的,然后温柔地朝着她的朋友吻了吻双手,她的朋友也向她吻了吻自己的双手。接着,她看到花草中间出现了另一只手(一只晒得黝黑的手),扶着她的朋友进了屋子。
塔塔先生在舰长舱像变戏法似的,只按了一下柜子门上的弹簧把手和一只抽屉的把手,便端出了各种饮食,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一眨眼的工夫,桌子上摆满了精美的蛋白杏仁饼干、闪光的甜酒,以及用巧妙的方法酿制的热带香料、美妙的热带水果果酱,等等。但是塔塔先生无法使时间停止,而时间是那么的冷酷无情,正在飞速地大踏步前进,使得罗莎终于不得不离开这个仙境般的地方,回到地面上监护人的家中了。
“现在,亲爱的,”格鲁吉斯先生说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换句话说,也就是现在你应该怎么办?”
罗莎只能以脸上的表情来表达歉意。她自己无计可施,也给大家带来了麻烦。至于计划,她目前所能想到的,只有一辈子住在弗尼瓦尔会馆,躲在许多级楼梯上面的那个防火地带。
“我有一个想法,”格鲁吉斯先生说道,“你们可敬的校长特文科里顿小姐到了假期,有时会在伦敦小住几天,以便扩大社会联系,如果有的家长住在首都,她可以跟他们见见面。因此我想,在我们找到办法以前,是否可以请特文科里顿小姐来跟你做伴,住上个把月?”
“住在哪里,先生?”
“这好办,”格鲁吉斯先生解释道,“我们可以在市内租一套带家具的房子,为期一个月,然后把特文科里顿小姐请来,把你托付给她,这样行吗?”
“那以后呢?”罗莎问道。
“以后嘛,”格鲁吉斯先生说道,“以后总不至于比现在更糟吧。”
“我想,可以这样暂时渡过难关。”罗莎同意道。
“那就让我们去找一套有家具的房子吧。”格鲁吉斯先生说着站了起来,“就我而言,昨晚的甜蜜情景正是我求之不得的,这种夜晚今后在我的一生中都不可再得了,然而这对于一位年轻的小姐来说,终究不是合适的环境。现在让我们出去碰碰运气,找一下带家具的寓所。再说,克里斯帕克先生正在这儿,马上就要回家,想必可以去找特文科里顿小姐,把我们的计划通知给她,请她大力协助一下。”
克里斯帕克先生欣然接受了委托,告辞走了。格鲁吉斯先生便带着他保护下的小姐,出去寻找住房了。
格鲁吉斯先生寻找带家具的住房的办法,就是跨过大街,跑到对面一幢窗口挂着块招租牌的房子面前,打量了一下,然后转弯抹角地绕到房子的后面,又打量了一下,结果没有开门进去,又对另一幢房子作了同样的考察,结果也是一样。他们的进展自然并不顺利。最后,他想起白扎德先生有一个隔了好几重的亲戚,曾经请求利用他在房客中的影响力帮忙介绍租户。这是个寡妇,住在布卢姆斯伯量广场南安普敦街,门口有一块铜牌,牌上用相当大的大写字母刻着她的姓氏,比利金,没有标明性别和其他状况。
身体虚弱和心直口快是比利金太太之所以为比利金太太的两大特点。她没精打采地走出了她专用的后客厅,看样子仿佛已经昏厥过好几次,只是因为现在有人要看房子,才不得不苏醒过来。
“先生,但愿你的身体很好。”比利金太太认出了客人,点了点头说道。
“谢谢你,很好。你呢,太太?”格鲁吉斯先生回答道。
“我也很好,”比利金太太说道,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呼吸有些短促,“从没这么好过。”
“我是这位小姐的监护人,她与一位年长的妇女想找一个体面的寓所,住一个月左右。太太,你有没有可以出租的房间?”
“格鲁吉斯先生,”比利金太太回答道,“我不能欺骗你,绝对不能。我有可以出租的房间。”
那神气似乎还在表示: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我送上火刑柱,但是只要我还活着,我就得说老实话。
“那么,太太,是什么样的房间呢?”格鲁吉斯先生问道,同时松了一口气。比利金太太显然有一种以柔克刚的能耐。
“这间起居室就是,不论你叫它什么,这其实是前客厅,小姐,”比利金太太说道,表示是在跟罗莎说话,“后客厅是我自己用的,我从不离开那里。在这房子的顶楼上有两间卧室,里面装着煤气灯。我不能对你说卧室的地板很牢固,因为它们并不牢固。装煤气的亲自告诉我,要使它牢固,除非把地板全部更换,可是一年一个租户,花这些钱不值得。煤气管是铺在地板上面的,这一点我也必须向你说明。”
格鲁吉斯先生和罗莎听了有些泄气,交换了一下眼色,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这样铺设的管道包含着怎样潜在的危险。比利金太太把手按在胸口,好像要减轻它的压力似的。
“好吧!那么屋顶想必是没有问题的吧?”格鲁吉斯先生说道,精神振作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