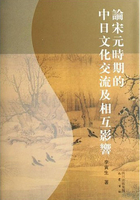对于贾似道的是非功过,暂时放置不谈,最令笔者奇怪的是,当年贾似道也曾是热血男儿,在忽必烈兵临鄂州城下之时,丁大全隐瞒军情可谓误国不浅,理宗曾准备听从丁大全的建议迁都以避蒙军之锋,而贾似道全力主战并亲自指挥取得了鄂州大捷。当理宗罢免权相丁大全,命贾似道出任宰相之后,贾似道的糟糕表现比丁大全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襄樊失守,南宋岌岌可危。为什么贾似道前后判若两人呢?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文天祥临危受命
夏日时节,南方的暑气很重,忽必烈下诏伯颜,认为“正值酷暑,如今我们已经扼住南宋的咽喉,可以暂时休整军马,待到秋高气爽在起兵不迟”。伯颜马上回奏道:“宋人凭借江海,作困兽之斗,现在虽然已经扼住其喉咙,但是如今不一鼓作气将其赶尽杀绝,很可能灭亡南宋的机会转瞬即逝。”忽必烈觉得伯颜所言有理,诏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阿术驻扬州,绝宋朝淮南之援。于是,伯颜分兵四出,一步一步收紧对临安的包围。其实,忽必烈对南宋“停战”的想法绝非因为天气原因,恰恰是因为蒙古内部统治不稳,他的注意力还大半放在北方,准备彻底平定诸王后再灭宋。伯颜一席话,使忽必烈决定先南后北。
一时之间,平时大读圣贤书,张口闭口都是仁义道德天理人心的宋朝各地官员纷纷降元,广德军、岳州、滁州、宁国府等州军皆投降,最终连镇守江陵的南宋京湖宣抚使朱禩孙和湖北制置副使高达也献城降元。如此战略大郡,不战而降,对南宋各地的文武守臣心理震撼极大,朱禩孙又发檄各部号召“归附”,于是“归、陕、郢、复、鼎、澧、辰、沅、靖、随、常德、均、房诸州,相继皆降”。本来,阿尔哈雅一支孤军守鄂州,元朝一直忧心江陵宋军会合军进攻。至此,荆南大定,元军再无后顾之忧。
为此,忽必烈手诏褒奖进攻江陵的阿尔哈雅,并授叛将高达为参知政事,召朱禩孙入上都面圣。可惜刚刚走到上都地界的朱禩孙因病而一命呜呼,无福见到新朝天子的龙颜。
元兵东下,“所过皆降”,唯独宋将李庭芝“率励所部,固守扬州”,并斩杀元朝派来招降的使者,时出金帛牛酒犒赏壮士,誓以死守,“人人感激自奋”。其手下姜才(原为孙虎臣前锋)更是频频出城与元兵交仗,屡败屡战,身先士卒,身中多创,仍带伤勇斗。
8月间,身为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诸军的张世杰率平江都统刘师勇和知寿州孙虎臣率宋军水军万余艘,列于焦山南北广阔的江面上。此前,他约张彦从常州率军趋京口(今镇江丹徒),约李庭芝统军出瓜洲(今扬州东南),准备三路并出与元军决战。结果,张、李二人皆因故失期,只有张世杰孤军与元军对阵。张世杰久处军旅,秉性忠勇,但军事指挥方面却属平庸之才,水战更是外行。为示必死之心,他下令以十船为一舫,铁索互连,沉锚于江,非有军令严禁起锚。如此,就给元军留下了最佳的火攻机会。
阿术登石公山眺望宋军水阵,立刻大笑道:“可烧而走也!”于是,阿术先遣元军善射者乘巨舰进逼,火矢雨发,宋军“篷樯俱焚,烟焰蔽江”,宋军“死战,欲走不能,多赴江死”。元朝张弘范、董文炳等汉人将领又舍命冲杀,张世杰最终不支,与刘师勇、孙虎臣二人分头败走。元军获宋水军“白鹞子”精舰七百余艘,杀伤宋军无数。
当时元军进攻的态势是,伯颜统主力直奔临安;阿尔哈雅攻湖南;宋都带等人攻江西并一举断绝宋朝东西纽带;阿术攻扬州方向,阻止宋军从淮东方向支援临安。
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风云变幻之时,宋廷把文天祥招至临安,任命他为兵部尚书。文天祥临危受命,立刻上书道:
本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乱,解除了各路藩王的兵权,建立都城,虽然足以消除诸侯尾大不掉之弊端,但现在国家危难,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沦陷,痛悔何及!如今之际应该将南宋境内分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地广人多,乃足以抗敌。齐心协力反抗元军,有进而无退,日夜疲扰元军,彼(元军)兵力分散,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机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退也。
疏上,“时议以为迂阔(迂腐而不切合实际),不报”,只下命文天祥知平江府。其实真正“迂阔”的并非文天祥,而是那些庸碌无为的朝中大臣。
然而在专制政体下,官场沉浮和筛选规律往往是黄金下沉,粪土上浮。宋朝最崇尚文官政治,最优礼科举出身的士大夫,这与其他朝代,包括待士苛刻寡恩的明朝,形成鲜明对比。但既然存在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养士三百年就不可能不是败政。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是个贪墨的大染缸,大多数士大夫经历官场的染色,只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蠹虫,他们贪污腐化有种,横征暴敛有能,奉承拍马有才,结党营私有份,钩心斗角有术,文过饰非有方,妒贤嫉能有为。高官们平日似乎是高视阔步,旁若无人,一旦稍有风吹草动,便立即显露出萎靡卑琐的鼠辈本色。
10月间,伯颜又把元朝大军分为三路,伯颜本人自统中路军,以吕文焕为向导,直取常州、平江(今苏州);阿剌军为右路,从建康经由溧阳等地进攻独松关(浙江安吉),张弘范、范文虎率左路军统水军经江阴等处由海路进攻澉浦(今浙江海盐)。元军兵锋所向,宋军不支,先前配合张世杰作战的孙虎臣在泰州战败自杀,张彦在吕城也战败,被捕后降元。元帅阿术攻扬州,“既筑长围,城中食尽,死者枕藉满道”,但守将李庭芝坚守不降。
血战常州
伯颜命大将阿塔孩为前锋军,猛攻常州。常州形势危急,宋廷派大将张全率两千精锐赴援,同时文天祥自平江也遣部将尹玉、麻士龙、朱华三人各率一千兵马共三千军士增援。结果,麻士龙首先遭遇元军,血战于虞桥、五牧(今常州东南)。关键时刻,宋将张全见死不救,一千将士全部战死,麻士龙浑身多处受伤仍力战不止,手刃元兵不计其数!麻士龙忽然停下了刀,然后仰天大笑,笑声令元军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这一笑令麻士龙身上的数道伤口迸裂,鲜血喷洒而出如泉涌,溅了身边包围过来的元兵一脸,元兵纷纷向四周退去,惊恐地注视着这个疯子一样的宋将。
麻士龙把大刀插在身边,面向南方,无限留恋地说道:“陛下,太皇太后,臣不能再尽忠报国了,陛下保重,臣麻士龙去也!”说完,麻士龙拔出腰刀,在自己喉咙处重重一抹,一个人缓缓地倒了下去。一直到死,他的脸,依旧是面对着南方。元兵见麻士龙已死多时,仍不敢靠近!
朱华一军驻扎五牧(虞桥以东),想掘沟堑筑鹿角抵拒元军,张全又不许。结果,元军很快赶至,双方激战,斗至傍晚,朱华身带重伤,仍然亲自指挥军队酣战,但终因孤立无援而被迫败走!
元军又分出一部绕出山后,直扑尹玉一部宋军,双方恶战,尹玉手下宋兵英勇,杀元兵千余人,打得难解难分。但是,张全所率二千精兵隔岸观斗,不发一矢相援,最终,尹玉部寡不敌众,不支败走。宋军争相奔至张全泊在河中的大船想搭船逃生,张全忙下令军士砍断扒船溃军的手指,张帆奔逃而去,“于是溺死者甚众”。
宋将尹玉见撤退无望,长叹道:“吾以一死报国耳。”下定必死决心的尹玉,迅速招集残卒五百余人,集合之后,忍饥挨饿,重新冲入战场与元兵激战,“自夕达旦,杀元军人马,委积田间”,尹玉本人虽力竭,仍手刃数十元军,最终伤重被俘。元军恨透了这位勇似战神的宋将,“横四枪于其顶,以棍击杀之”。尹玉部下宋军皆苦战而死,无一人投降。看到了这一切的伯颜微微叹息道:“中原多好汉也。自我蒙古大军伐宋以来,先有襄阳、钓鱼城之战,又有常州、陈墅血战,若不是汉人的朝廷不争气,我蒙古人安能赢得中原分毫!”
可怜,麻士龙与尹玉两位大英雄,皆死于元军之手。“余兵闻之号恸,相率夜战,死伤人马蔽田间,无一降者,全部壮烈牺牲,尸骨遍野,当地百姓拾骨集葬,称‘骨成堆’。清入关后,改为‘郭成墩’。原五牧有‘二忠祠’,虞桥有‘尹麻两将军庙’,俗称‘双庙’,今祠庙均已毁。”
元朝右路军一路凯歌,势如破竹,连克溧水、溧阳、东坝(江苏高淳)、四安(今浙江安吉以北)。元朝左路军也攻占江阴。大惧之下,陈宜中急忙在临安籍民为军(拉壮丁),召文天祥自平江入卫。
坐镇江西的大官、先前一直排抑文天祥的宋臣谢万石降元,其属下都统米立率众苦战,力竭被俘。元人看重这位英雄,派谢万石亲自去狱中劝降。谢万石厚颜无耻地对米立道:“你看我,权高位重,所任官职之多,在一张牙牌上都写不完,现在也向大元投附。你一个小小军将,何以不降呢?”米立凛然答道:“侍郎您(谢万石兼兵部侍郎)乃国家大臣,米立只是一名小卒。但我自思数世皆食宋禄,赵氏危亡,我有何面目苟生求活。加之我力战不支被擒,本应死国,与您这样的投拜之人不同!”谢万石惭愧,又不得不劝。米立凛然不屈,最终为元兵残杀。
伯颜率军包围常州,宋朝知府姚訔与陈炤等诸将全力固守。见招降不成,伯颜下令攻城。伯颜命元军架云梯、绳桥,指挥帐前军携赤旗奋勇先登,诸军见伯颜的旗帜已立城头,四面并进,蜂拥而上,迅速占领城头。姚訔在阵前指挥,与诸将士拼死力战,因寡不敌众,英勇战死。元军破南门而入,护国寺的万安、莫谦之长老率领五百僧兵,高举“降魔”大旗,杀向南门,由于孤立无援,五百和尚全部战死。常州城破,知府姚訔殉国。王安节、陈炤、胡应炎等率兵与元军巷战,亦因体力不支,先后阵亡。刘师勇转战至北门,乘乱突围,仅带八骑逃往平江。常州城破之后,常州百姓不愿受辱而纷纷自杀,一时间,城里的井中填满死尸,在树林中上吊的人两两相望。
兵临城下
常州之战结束一周之后,元军攻战独松关,守将张濡(陷害岳飞主谋之一的张俊的五世孙)临阵脱逃。由此,邻近宋军“皆望风而走”。不久,许浦、安吉州(今浙江湖州)皆为元军所破。眼前元军步步逼近,宋廷别无他法,故伎重演,派出柳岳为使臣,到无锡的元军大营见伯颜乞和。柳岳先是对元使被杀之事道歉,表示他们是“为盗所杀”,与宋廷无关。接着,柳岳哀求道:“嗣君冲幼,服孝未满,自古礼不伐丧。两国关系发展到今日这种地步,皆奸臣贾似道所为。”伯颜对柳岳的话不屑一顾,立刻反驳道:“汝国执戮我使臣(指拘郝经杀使者等事),大元才因此兴师来伐。钱氏(吴越)纳土,李氏(南唐)出降,皆汝国昔日所为。汝国得天下于小儿(指赵匡胤篡后周柴荣之子恭帝之位),亦失之于小儿(指当今的宋恭帝)。天道如此,尚何多言!”元人虽蛮横暴戾,此话却不无道理。
柳岳回朝复命,众臣皆长吁短叹,乱作一团。不久,宋廷下诏“追封吕文德为和义郡王”。那么谢太后何以把一族皆叛的死人吕文德追封为王?而且,先前数月,继吕文焕、吕师夔等人降元后,吕文德另一个弟弟五郡镇抚使吕文福也杀宋使降元,几乎整个吕氏家族皆归降蒙古人,且一路充当向导,为害日深。宋廷在吕文福叛变后,才下令抄没吕氏家族在临安的资产,怎么会忽然又追封吕文德为郡王呢?其实,此举也是事出无奈,宋廷还封没逃掉的吕文德之子吕师孟为兵部侍郎,想借此来打动吕文焕等人,幻想这些人为南宋向伯颜说几句好话,答应南宋的乞和。
慑于元军的屠戮,身在临安的南宋大臣之中有数十高官,皆悄悄逃离临安,甚至主管军事的签枢密院事文及翁和倪普也想一走了之。这两人先让与自己关系好的台谏官弹劾自己,好使得自己能被贬逐从而出走临安。结果,弹劾章疏未上,两个人就已经携家眷绝尘而去。
谢太后闻知此事,又悲又气,派人在朝堂上立大榜,诏示如下:“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宋恭帝),遭家多难,尔大小臣工,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内而庶僚叛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时读圣贤书,自许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亦何以见先帝!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其在朝文武官,并转二资,其叛官而遁者,令御史台觉察以闻,量加惩谴。”在谢太后的谴责声中,也泄露出南宋皇室孤儿寡母的无奈与悲怆。危亡之际,文天祥被任为“签枢密院事”,来收拾残局。
男人血性
至于潭州(长沙)方面,先前与文天祥一起响应勤王的李芾,以湖南安抚使及潭州知州的双重身份死守潭州。潭州军民在李芾率领下,展开了一场英勇的保卫战。数万元军兵临城下,而长沙能作战的军民只有三千。敌众我寡,危如累卵,是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有人劝他逃跑,李芾正颜厉色道:“我世受国恩,今逢国家危难,正思报国无门,很幸运如今有了用武之地,我以家许国矣!”
李芾的一席慷慨陈词,令在场之人无不动容。然而在远处的城楼上,不时传来军士巡夜的刁斗声;而在由北向南的驿道上,快马正传送着十万火急的塘报。那嗒嗒的马蹄声不仅使夜色惊悸不安,也足以使一个末日的王朝瑟瑟发抖。
李芾本来是一个文弱的儒生,他明白,在滚滚狼烟和刀光铁血面前,他的文化人格,只能归结于寂灭和苍凉,归结于一场无可奈何的悲剧性体验。他只能有这种选择。有时候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走向结局的过程。多少抗争与呐喊,多少谋略和鲜血,多少英雄泪和儿女情,把走向结局的每一步演绎得奇诡辉煌,令人心旌摇动而又不可思议。
李芾率潭州军民苦战苦撑,固守了三个多月。元将阿尔哈雅气急败坏,射书城中威胁,“速开城门投降,否则屠城”!宋军将士以箭雨回应。阿尔哈雅大怒,派兵掘挖潭州护城河河堤,待水半干后大竖攻城器具,指挥元兵拼死进攻。激战之中,宋军抛石发弩,一箭正中阿尔哈雅胁下,阿尔哈雅负伤之后“恼羞成怒、加紧督战”,手刃数名从城墙下撤回的元兵,催逼军士奋力攻城。“城中大窘,力不能支”。宋军诸将见形势危急,泣请道:“潭州城将不保,我们军将为国而死义不容辞,但城内百姓怎么办?”李芾双眼冒火,骂道:“国家平日厚养汝辈,正为今日!汝等只管死守,勿思其他,再有敢言降者,定杀不饶!”
李芾在城中弓箭用尽之时,令百姓将废箭磨光,配上羽毛,用以再射;盐尽,则将库中盐席焚毁,取灰再熬,分给军民食用;粮绝,则捕雀捉鼠充饥。有将士受伤,李芾亲自抚慰,给以医药。他日夜巡视城郭,深入兵民之中,以忠义勉励部属。元兵派人来招降,被李芾抓住,当场诛杀。
潭州坚守了三个多月,援兵不至,城池危在旦夕。农历除夕之日,李芾的参谋尹谷听到元兵已登城,乃积薪闭户,全家人坐在一起,举火自焚。邻居来救,只见尹谷正冠端笏危坐于烈焰中,全家老少葬身火海。李芾闻讯赶到,以酒祭奠,哭道:“尹谷真男子也,先我就义矣!”李芾传令,手书“尽忠”二字为号,决心与潭州共存亡。眼看城破在即,李芾端坐熊湘阁,令部将沈忠把他的全家老少集中在一起,积薪焚烧,沈忠伏地叩首,表示自己下不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