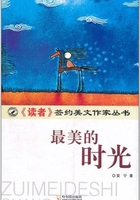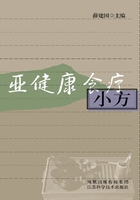从嘉和裴厚德离开了皇宫,便在金陵的街道上闲逛。从嘉问道:“厚德,你可知道些好玩的地方带我去。”裴厚德道:“郡公,您还是早些回去吧。”从嘉笑道:“刚出得家门便回去,这有什么意思,难道我出来就是为了散步么?”其实裴厚德当然知道从嘉离家的原因,毕竟他也能感觉到李弘冀凌厉的目光停留在从嘉身上时总含着恨意。而从嘉还小,有些事情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只得满心难过地去逃避。
裴厚德道:“郡公的意思小的明白,可是若是郡公在外面出了什么差池,小的可担待不起啊。”从嘉笑道:“现下国泰民安的,能出什么事。况且爷爷也不一定会过问这些小事。”裴厚德知道再劝也无用,也就不再多言。他们二人在街上随意走着,从嘉便听到有读书的声音。原来路边便是一个学舍,院门开着,院中一个教书先生正在给学生们上课。从嘉不由好奇心起,对裴厚德道:“咱们过去看看吧。”说完,不等裴厚德回答便走了过去,裴厚德也只得跟了过去。
从嘉走到了门口,却见那教书先生说了几句后,便坐在椅中看书,那些学生也坐在座位上读书。从嘉觉得无趣,刚要离开,却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将书立在桌上,却开始摆弄其它的东西。从嘉从未见过,心下好奇,又走近了几步,却发现那少年原来在玩一只麻雀。裴厚德低声道:“咱们还是走吧。”从嘉却觉得那少年玩得甚是有趣,不愿离开。那少年没有专心看书,一边玩着,一边还听着那教书先生的动静,便听到了裴厚德的话,不由一惊,向门口看去。哪知那少年这一分心,那只麻雀便从桌上飞走了。
从嘉见状,下意识地轻声道:“你的鸟飞走了。”这下子闹了这样的动静,便惊动了那教书先生,他先是走到从嘉身边上下打量着。从嘉一怔,忙解释道:“我路过这里,不过是……是好奇才来听听,没……没有别的意思。”那教书先生见从嘉不过是五岁左右的孩子,又见他回答时虽然有些不知所措,但却也不像作伪,也就不再多问。接着又走到那少年身侧,厉声道:“又是你不认真读书。”那少年瞪了从嘉一眼不再答话。从嘉不解,心道:我好心提醒他一声,他为什么怪我呢?从嘉哪里知道,那少年定是要受到先生的处罚的。
裴厚德却知道从嘉得罪了人,拉了拉从嘉的衣袖,示意他离开。从嘉尚未回答,却见那少年伸出手来,那教书先生拿出戒尺责打。从嘉不由“啊”的一声低呼,这才明白那少年为什么责怪自己,不由得满心歉意,便对裴厚德道:“咱们也需得给这个少年解释清楚了再走啊。”裴厚德无奈,只得陪他在那里等着。
不过多时,便已近午时,学舍便散了学。那少年便走到从嘉身边,没好气地问道:“你怎么还不走啊?”从嘉也不介意,反而很抱歉地道:“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先生会责怪你,我……”从嘉一时也找不到道歉的话,不知该怎样说。那少年倒是一惊,他心知这件事是他做得不妥,不过是随意发泄两句,没有想到从嘉竟这般真诚地道歉,心里反倒有了几分歉疚。那少年又上下打量了从嘉几眼,见从嘉相貌甚是清俊可爱,话语也给人如沐春风之感,不由心中好感大增,道:“没事,是我做得不对,不怪你。”
从嘉道:“那先生一定是很生气的了?”那少年笑道:“没事,先生下午大概便不记得了。”从嘉一怔,道:“可是他打了你,他为什么这样生气呢?”那少年见从嘉神态天真,也不由一怔,道:“是因为我不好好念书啊,这不也很正常么?”那少年见从嘉仍是不解地看着自己,觉得这人甚是有趣,不由对他感到好奇,问道:“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会来这里?”从嘉道:“我路过这里,便随便看看。”那少年点了点头,问道:“你没上过学吧?”从嘉奇道:“噫?你怎么知道的?”那少年笑道:“难道这还看不出来么?”
两人又闲聊几句,那少年道:“行了,我该回家了,若是再不回去,爹娘又该说我贪玩了。”从嘉却觉这人知道很多自己不知道的事,不舍得离开,便道:“你家在哪?不知我们顺不顺路啊?”那少年也觉从嘉甚是可爱,见他如此说,也有心留他,便道:“你若无事便到我家吃饭吧,反正下午我还是要来上学的。”从嘉甚喜,对那少年也很有好感,又是孩子心性,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便道:“好啊,那麻烦你了。”裴厚德刚要开口相劝,从嘉便道:“厚德,你在这附近等我好了。下午我们便一起回去。”裴厚德知郡公素来任性,再劝也是没用,更何况那人也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是小孩心性,并无恶意,想来也无事,便道:“那公子早些回来。”从嘉点了点头,跟那少年一起离去。
路上从嘉便不断地问他上学舍的趣事,那少年便有声有色地讲述着自己和同学如何偷着玩、如何作弄先生等等。从嘉从未听过这些事,羡慕地道:“你们上学真有意思。”那少年道:“也不是吧,你刚才也看到了,你要玩还得小心先生的戒尺呢。”从嘉听了不由得脸有惧色,须知从小他的亲人大都对他万分疼爱,而教他读书的冯先生更是对他毕恭毕敬,他从未知道做错了事情还会受到这样的惩罚。那少年见状,心下的好奇更多了几分,便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啊?没上过学也就算了,怎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从嘉道:“我……我爹爹是有钱人家,大概我还没到上学的年龄,也就很少在外面走动过。”那少年道:“我看你也有五岁了吧,不如也到先生那去上学如何?”从嘉喜道:“甚好,可是不知道爹爹同不同意。”那少年见从嘉同意,喜道:“你爹爹怎会不同意。”他哪里知道从嘉便是安定郡王,就连这次也是偷着出来的。
说话间,两人便已到了那少年的家门口。那少年道:“到时爹娘要是问起,便说你是我的同学。还有今天的事不要跟爹娘说了,省得他们又说我不好好读书。”顿了一顿,又道:“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嘉知不便相告真名,想到自己很羡慕那些归隐山林的隐士,又想起自己将《渔父》这首词题在那幅画上时便用了“钟山隐者”这个号,便道:“我姓李,名钟隐。”那少年见他半晌不语,笑道:“怎么连自己的名字也需要想半天啊?”从嘉不知如何回答,便不再答话,问道:“那你呢?”那少年道:“我叫段居真。”
从嘉随段居真来到家中,见这房中的陈设虽然简单,但倒也干净。段居真的父母已经备好了饭菜,听段居真说从嘉是他同学,便也热情款待。段居真和从嘉都只随便吃了几口饭,便一起跑到后院去玩了。段居真所说所玩都是从嘉闻所未闻的东西,段居真不由问道:“你什么也没听过,那你在家都干些什么啊?”从嘉道:“不过是读书填词,练字作画,听曲抚琴罢了。”段居真道:“那听起来确不是很好玩。”
两人玩了一阵,便已近未时,段居真道:“好了,我要去上学了,咱们一起走吧。”从嘉点了点头,跟他一起离开。两人从对方那里听来的都是些从来没有听过的新鲜事物,都很不舍离开。段居真问道:“明天你还能来玩么?”从嘉扫兴地摇了摇头,道:“怕是不能的了,我这一次出来便不怎么光明正大。”段居真也感扫兴,想了半晌,提议道:“不如今天下午我不去学舍了,咱们一起玩可好?”从嘉也是小孩子贪玩,拍手笑道:“好啊,好啊。”但随即又道:“可是你这样做不好吧?”段居真笑道:“我都没说什么,你还管我么?走吧。”说完便拉着从嘉,想要跑到郊外去玩。
从嘉和段居真来到长江边上,这时已近冬日,长江水位下降,他二人便在江边沙滩上戏水,直到夕阳将这江水染成红色,他们才离开。
两人刚一进金陵城,便有一个二十一二岁的青年横剑拦在他们面前,喝道:“六弟,你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家出走,就不怕家里人担心的么?”那青年正是从嘉的大哥李弘冀,而裴厚德也站在了李弘冀的身侧。从嘉见到李弘冀,便脸有惧色,低声道:“大哥,我……”李弘冀不等他说完,便喝道:“有什么话回家再说,跟我走。”说完便拉着从嘉要走。段居真见李弘冀态度很是不好,而从嘉也像是很怕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从嘉只得对段居真挥了挥手示意一下,裴厚德也跟在他们的身后离开。
路上,从嘉小心地问道:“大哥,你怎么来了?”李弘冀道:“你还问我,自然是皇上让我来找你的。”从嘉一怔,道:“爷爷也知道了么?”李弘冀道:“那还能不知道?皇上现在在太子宫,你还是想想回去怎么解释的好。”说完,又是那凌厉如剑的目光盯着从嘉,似是在警告他不可乱说话。从嘉不敢再接话,点了点头。
李弘冀带从嘉进了宫,便独自一人回府去了。从嘉回到太子宫,李已在厅中,李景通和钟氏也在那里。李见到从嘉回来,似是放了心,满脸欣喜的神色。李景通却先喝道:“重光,你怎么如此任性!居然这个时候才回来!你知不知道皇上很担心你!”从嘉低着头,轻声道:“孙儿只是出去玩玩,没有想到会惊动爷爷。孙儿知错,请爷爷降罪。”说完便跪了下来。李却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走到从嘉身侧,将他扶起,笑道:“重光,你别紧张,朕没有说过要怪罪你啊。”顿了一顿又道:“朕只是担心你,下次出去,一定要跟家里人说一声,知道么?”
从嘉从爷爷看到自己平安回来的欣喜中,看出了爷爷的担心,不由得心下甚是歉疚,低声道:“爷爷,孙儿再也不敢了。”李景通插口道:“父皇,对重光太过宠惯怕是不好。”李不去理会李景通,对从嘉道:“重光别怕,朕怎么舍得处罚你呢?”接着又满怀爱怜地抚了抚从嘉的头,笑问:“可吃过饭了?”从嘉摇了摇头,道:“还没吃呢。”李道:“那便跟朕一起用膳好了。”说完吩咐宫人传膳。从嘉心道:这时天色已黑了下来,爷爷竟还没有吃饭,想来必是担心自己连饭都没有顾上吃,不由心下感动,更觉得不该如此任性。
饭后,从嘉来到太子宫,见到李景通和钟氏,躬身行了一礼,低声叫道:“父王、母亲。”李景通摆了摆手,道:“重光,你知不知道今天皇上很是担心你啊。现在天气已经凉了,可是皇上一听到你一声不响地出去了,竟急得满头大汗,立即下令让弘冀派人去找。就这样,皇上也是不放心,在屋里踱来踱去,焦急地等待着,见到有侍卫回来,忙上前询问是否有你的消息,若是没有,皇上也只得对那些侍卫吼几句,又立即让他们去找,从上午到你回来都没顾上吃饭。若是你还没有回来,皇上怕是要亲自去找了。”
从嘉听了,知父母也定是像爷爷一样担心,想到这眼中竟已有泪光,满心的内疚和惭愧。从嘉退开两步,跪倒在地,说道:“父王,从嘉不该让这么多人担心,从嘉知错,请父王责罚。”钟氏柔声道:“重光,地上凉,你先起来吧。”从嘉见钟氏眼睛红肿,泪痕未干,知她定是哭过了,更觉得自己做的不该,说道:“母亲,从嘉既然做错了,自当受到惩罚。”李景通道:“你既知错,那你想让我怎么罚你?”从嘉道:“全凭父王做主,从嘉甘领罪责。”
过了半晌,李景通轻叹一声,将他扶起,说道:“皇上都不责怪,我还怎忍心责罚呢?”其实李景通当时一来是确实生气,二来也是怕皇上怪罪从嘉,才出言呵斥,也并没有真的想要责罚他。钟氏道:“重光,你也不必自责了,既然知错,下次不要这样了便好。”顿了一顿,又道:“现在也不早了,你早些回寝宫休息吧。”从嘉点了点头,躬身行了一礼,转身离去。
从嘉回到寝宫,刚要坐下来休息,就听有宫人禀报道:“皇上驾到。”从嘉忙躬身行礼,道:“参见皇上。”李摆了摆手,道:“不必多礼了。”又见从嘉似乎心情不大好,便问道:“重光,你父王责怪你了么?怎么好像不高兴?”从嘉忙道:“不,没有,父王没有责罚我。”顿了一顿,又轻声道:“爷爷,对不起,是从嘉不好,让您担心了。”李笑道:“没事,朕从来都没想责怪你啊,你这样说,倒像朕是来问罪的了。”从嘉道:“私自出去本来就是从嘉的错,就算爷爷怪罪也是应当的。”
李叹了口气,道:“重光,你是个听话的孩子对不对?”李这话问得突然,从嘉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道:“我……”李道:“朕相信你是一个乖孩子,不会无缘无故的离家出走,对不对?”原来白天之时,李心中挂念从嘉,没有多想,而从嘉回来后,便越想越觉不对,这才前来询问。从嘉听了,更是不解,半晌之后,李见从嘉仍不回答,便道:“告诉朕,你为什么一声不响地离开皇宫?”从嘉道:“孙儿是贪玩,才要出去玩玩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李如何能信从嘉这句话,说道:“重光,不用怕,有什么原因直说就是了。”
从嘉固然对李弘冀心存恐惧,记得他的警告,但他更能感到事情似乎比他理解的严重得多,虽然他对大哥不是很明白,但也不敢乱说,只得道:“真的没什么,请爷爷不要追问了。”李能看出从嘉一定隐瞒了什么,道:“重光,你可知道欺君是何罪过?”从嘉一怔,低下头去,不再回答。李见状,早已猜到必是弘冀找过从嘉,甚至警告过从嘉。李又轻叹一声,说道:“罢了,你不想说,朕也猜得出。”
李见从嘉还是低着头不说话,便笑道:“本来出宫去玩一玩应当是一件有趣的事,怎么这样愁眉苦脸的?”从嘉听出李的关切之意,忙道:“没有啊。”李笑问:“那么,跟朕说说,宫外好玩么?”从嘉听李这么问,也来了兴趣,笑道:“宫外好玩得很,我在宫外认识了一个朋友,他还约我跟他玩呢。”说着,轻轻摇了摇李的衣袖,道:“爷爷,我可不可以常到宫外去玩啊?”李笑道:“当然可以了。不过下次出去至少也要让宫人转达一声,记得早些回来便是了。”从嘉高兴地拍手笑道:“爷爷真好。”李微笑着看着从嘉可爱的样子,心里说不出的喜爱,暗自想着,若能体察民间冷暖对于为君必是十分有益的。
从嘉见李半晌无语,问道:“爷爷,你在想什么呢?”李回过神来,随口道:“你刚才说你在宫外认识了个朋友,什么人啊?”从嘉道:“他叫段居真,在城里的一个学舍上学。孙儿偶然遇到了他,跟他甚是投缘,他还想邀请我跟他一起上学呢。”李道:“哦?是么?那你想去么?”从嘉不过是随口说说,没有想到李竟有同意的意思,不由一惊,说道:“孙儿怕爷爷和父王不同意。”李笑道:“朕怎么会不同意呢。正好朕也不想让你跟冯延巳过多的接触。”从嘉心下不解,他哪里知道冯延巳、冯延鲁、陈觉和魏岑合称为“四凶”,再加上查文徽就是“五鬼”,在官场上没有什么好名声。
李也不多作解释,说道:“关于冯延巳可日后再说。你到民间去上学不是正好可以常出宫去玩么,还可以常跟你那个朋友玩了,不好么?”从嘉喜道:“太好了!”随即又道:“可是不知道父王是不是赞成。”李道:“你父王那儿,朕去告诉他。你明天带个随从出宫去就可以了。出宫玩玩也就是了,上学舍的事不必太当真。记得在外面小心些,早些回来。”顿了一顿,又道:“你是安定公,大概也没有人敢为难你,但若是真的有什么意外,朕允许你调动京城的侍卫。”从嘉没有想到不用去跟父王说,这么容易便可以出宫去玩,听了这话,不由心下大喜,抱住李……笑道:“爷爷,你真的太好了。从嘉谢过爷爷恩典。”李将从嘉抱起,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笑问:“除了好呢?”从嘉略一思索,笑道:“还是好。”李哈哈大笑,与从嘉闲聊几句之后,便回了寝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