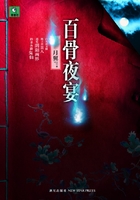一舞跳完,裴厚德早已看得呆了,从嘉赞道:“你的舞跳得真好看。”那少女也并未看见自己舞姿,只是从嘉那美妙的琴声仍响在耳畔,心中竟有了几分异样,随口道:“是公子琴弹得好,我不过是随着琴声起舞罢了。”从嘉道:“姑娘不用过谦了,你的舞步优美曼妙,是我生平从所未见。”那少女听了从嘉的夸赞,满脸红润,心里喜滋滋的,不好意思地将头转开,轻声道:“公子亦精于音律,还请公子指点一二。”
从嘉想了半晌,道:“不过,大概是鞋底太硬的过,脚步就显得不够轻盈。”那少女听了沉吟不语,从嘉又道:“若是能只用足尖跳舞,我想身法便会更加摇曳多姿了,宛若荷花盛开之状了。”那少女点了点头,便有一些失望,从嘉安慰道:“能跳成这样已经不错了,不过就是舞鞋的问题罢了。”那少女心想:原本以为可以创作一支轻慢优雅的采莲舞,却终还是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裴厚德见那少女还是不很开心,便道:“你跳得真的很好,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的舞步呢。”那少女听从嘉和裴厚德都在夸赞,也就相信这新编的采莲舞确是甚好,便道:“你把这首曲子教给我吧,到时候我再自己练习。”从嘉点了点头,便开始教那少女弹奏这首新曲,那少女亦善歌舞,很快便学会了这首曲子。接着,又是从嘉弹奏,那少女起舞。荷塘中,风吹水声,荷花摇摆,岸边上,琴声清婉,采莲曼舞,这样的巧妙和美的景致当真是难得一见。
从嘉和那少女直练到太阳偏西,天色渐暗,那少女才道:“不早了,我该回家去了,不然爹爹会担心的。”从嘉点了点头,道:“在下也是时候离开了,姑娘,后会有期。”微微躬身道别。那少女走开两步,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停滞了,心道:我们真的可以“后会有期”么?怕是今日一别,日后再难相见了吧。她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因一句客套话,有这样的怪想法,只是心中又多了几分伤感。
那少女忽然想起,还未问从嘉的名字,便转过身去,道:“公子,相识一场却还不知道公子叫什么名字呢。”从嘉道:“在下姓李,名钟隐。还未请教姑娘芳名?”那少女默默将他的名字念了几遍,这才意识到从嘉也在问自己姓名,便随口答道:“小女子姓冯,小字香邻。小女子贱名,不劳公子记着。”虽是这样说着,心里却在想:像他这等清俊公子,若是能记住有我这么个人,也是我的福分啊。但随即又想:他会记得我这个乡下女子么?就算记得,又能怎么样,怕也还是后会无期了吧?
这样想着,泪水竟不自禁地流了下来,那少女忙转过身去,快速跑开,生怕被从嘉看到了这泪水。可是自己越是这样跑,就越说明自己会放不下他。那少女心里明白,从嘉虽是一身粗布长衫,但是他身上那若隐若现的紫檀幽香,举止间高贵儒雅的气度和那曲精妙婉转的采莲曲,都显示着他的出身,自己是无论如何都配不上他的,他这一去,必是要将自己忘记的,如果自己再这样陷下去,大概也只有忧郁一生了。
裴厚德一直看着那少女离开的身影,直到夕阳将这粉色的影子掩埋,他也未回过神来。从嘉用折扇在他肩头拍了一下,笑道:“还在想着她么?”裴厚德这才回过神来,但还是并未听到从嘉的问话,便随口道:“少爷,我们要去哪里啊?”从嘉想了半晌,道:“去渡口。”裴厚德点了点头,应了一声,但随即感到不对,惊道:“什么?去渡口干什么?”从嘉道:“我要渡江。现下正是夏天,若是往南走岂不是更热,况且我也很好奇江北有什么景致。”其实从嘉尚未答话时,裴厚德便想到从嘉要到江北去,听从嘉这么说,更是生怕自己阻止不了,心下甚是着急。
裴厚德忙拦住从嘉,道:“少爷,这万万不可。少爷在江南玩玩也就是了,到了江北万一遇到了什么意外怎么办啊?”从嘉笑道:“江北亦是我大唐的国土能遇到什么意外啊?”裴厚德一时无言反驳,便道:“再说若是让皇上知道了,小的可承担不起啊。”从嘉道:“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我们去过江北啊。而且你平日听我的命令,父皇就算责怪,也怪不到你啊。”裴厚德知从嘉这话既是说若是皇上怪罪,他一人承担;同时又说明了自己应当听从他的命令。但虽是如此,裴厚德如何能放心,站在当地犹豫不前。
从嘉笑道:“你若是不肯去,那我一个人去好了。”裴厚德更加不可能让从嘉独自前往,忙上前将他拉住,说道:“少爷,这怎么成呢?小的求您别再任性了。”从嘉并不将他甩开,只是笑道:“你可不要忘了君臣之礼啊。”裴厚德跟了从嘉多年,知从嘉决不会因此怪罪自己,竟是并不放手。从嘉无奈,便道:“这样吧,你去京城把段居真叫来与我们同行。”裴厚德知道这已是从嘉做的最大的让步了,只得道:“好吧,小的这就去办。”从嘉叮嘱道:“切记不可以惊动其他任何人,包括从善,若是让旁人知道了,我决饶不了你。”裴厚德点了点头,便跟从嘉一同去了金陵城。到了城门口,从嘉便到城边的一个小茶馆中喝茶等待,裴厚德则进城去找段居真了。
到了夜晚,从嘉、裴厚德、段居真三人才来到江边,此时船只早已停渡,三人便在江边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下来。第二日清晨,从嘉对段居真道:“段大哥,还记不记得我们一起在望江楼玩。此刻我们谁都不着急回家了,不如再去望江楼,下午再渡江吧。”段居真也觉在望江楼上赏景甚是有趣,便笑道:“甚好。”
夏日的长江,两岸连绵的峭壁上已满是翠绿的颜色,江水在山间奔腾着,虽是在下游,亦是壮阔澎湃,在楼上,也能清清楚楚地听到江水拍岸的声音。此时江水正盛,正是游赏长江的时节,来望江楼览胜的游人也格外的多。从嘉于往来的文人墨客讲论文章,作诗填词,或是与段居真、裴厚德二人在窗边欣赏长江的壮丽风光,只待到太阳偏西,才到渡口,乘最后一趟船渡江。
三人到得滁州城外,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三人正打算进城,却听见隐隐有兵器相交之声传来,从嘉不由心下好奇,说道:“咱们过去看看吧。”裴厚德却担心会有危险,劝道:“算了吧,少爷。咱们还是赶紧进城吧。”段居真却是跟从嘉在一起玩耍多年,关系甚好,从来都不愿拂了从嘉的兴致,再加上自己也是好奇,又自认武功不弱,当不会有事,便道:“没事,一起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吧。”裴厚德见段居真也这样说,便不再劝阻,跟着一起向声音来处走去。
却见不远处的一个林子里,一个三十一二岁的黑衣青年左手抱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子,右手执剑正在跟十几个兵刃各异的汉子打斗。再走近几步,却见那青年浓眉大眼,剑眉入鬓,眉宇间透着英气;而那女子虽然头发微乱,脸色惨白,眼睛紧闭,但也可看得出是一个清秀绝俗的美貌女子。
那青年本来武功不弱,但要保护那女子,再加上对方人多,便也受了几处伤,落了下风。从嘉知再这样打下去,那青年定是不敌,不由心下担心,问段居真道:“你能帮帮他们么?”段居真不答,凝神看着这些人的招式,过了半晌,才道:“我想我和那青年联手,当是不难取胜的。”说完,便拔出腰间悬着的长剑,上前相助。那青年见有人前来相助又惊又喜,向段居真看了一眼表示感谢。段居真点头示意了一下,又道:“把那女子交给我家少爷吧。”那青年点了下头,段居真便挥剑拦在那十几人面前,那青年抽出身来,执着剑退开了数步,伸手轻轻一送,将那女子推到从嘉身侧,说道:“帮忙照顾一下我妹子。”从嘉道:“你放心吧。”那青年又举剑上前相助。
段居真和那青年武功都不弱,不过数招,那十几个汉子自知不敌,便只守不攻,想找机会收手。段居真见状,向那青年示意了一下,那青年会意,和段居真一起收剑跃开。那十几个人也立即收手,领头那人向段居真喝道:“你是什么人?干什么多管闲事?”段居真一怔,这才意识到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答,只得道:“你们十几个人打一个,不是有违江湖道义么?”领头那人道:“你少管闲事,是他先杀了我们的人,我才来寻仇的。”
那青年听了这话竟也并不反驳,说道:“你们这些强盗强抢民女,我路见不平出手相助,这才失手伤了人。你们若是有本事报官便是,到处追杀我算什么本事!”那青年亦是所言非虚,这十几个人确是强抢民女的强盗,自然不敢报官,只得一路寻仇,那十几个人听了这话,竟没有一个人想得出如何回答。从嘉见状也知两方人都是所言非虚,他素来仁义,又少接触江湖之争,听到竟还涉及人命,不由心下不忍,但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化解,只是用责备的目光看向了那青年。还好那青年的注意力全在那几个强盗身上,并未注意到从嘉的眼神。
段居真听了两人对话,也明白了事情原委,也有心化解这仇怨,想了一下,便对那领头的强盗道:“你们为何不老老实实地做点儿活,为什么一定要做强盗啊。”那领头人道:“你小子算什么东西,敢来教训我们。”段居真道:“那请各位想一下,杀了他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众强盗以义气为重,一路追杀报仇,竟也从未细细想过,听了这话,都是一怔,均想:是啊,杀了他不过是图惹祸事罢了。
那青年见众强盗不答,也不想多生事端,便微微躬身,说道:“在下失手伤人,并非有意得罪,况且这位姑娘也伤得很重,咱们的仇怨还是不要算得好。”领头人深知自己万万不能敌得过段居真和那青年联手,想了半晌,便道:“这件事先暂且不说。”说完,便将手中的钢刀指向了从嘉,喝道:“但是你凭什么多管我们的闲事!”从嘉一惊,退开两步,过了半晌,才道:“我不想你们再伤人。”顿了一顿,又道:“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做强盗啊?”
领头那人见从嘉不像寻常人士,更是没好气地道:“废话!你将身上的钱都给了我们,看看你是乐意饿死,还是乐意劫道!”从嘉听了这话并不恼怒,反而心生同情,问道:“你说你们是在家没有饭吃,才落草为寇的?”那领头人道:“还是废话,若不是这样,谁乐意做这种玩命的买卖啊!”从嘉甚是诧异,大唐富庶繁华,他从来没有想过北方竟有连饭也吃不上的人。从嘉还未回答,那青年便叹道:“唉,北方便是这样,连年征战,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从嘉见那青年神色间又是感慨又是叹惋,同情之意更增,说道:“厚德,把你身上的钱都给了他们吧。”裴厚德一怔,道:“少爷,那我们……”从嘉却并不想这么多,只是觉得这些人甚是可怜,有心相助,因而不等他说完,便道:“先给了他们再说吧。”裴厚德便将身上的钱都给了众强盗。从嘉说道:“你们回自己的家去吧,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若是钱还有多的就分给其他的贫民吧,在下在此谢过。”说完躬身一礼。
那些强盗都是面面相觑,本来自己这方就是技不如人,就算是被对方教训一顿也说得过去。而那领头人刚才也只是想向讨个说法,万没想到从嘉竟会慷慨解囊,一时间竟没有一个人反应过来,都怔怔地立在当地。那青年也是一惊,心道:我这一路南来,也见过很多富家子弟,也没有一个人会出手相助,更何况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公子可真是仁义之人啊。想到这,不由心下暗暗敬佩。
众强盗怔了良久,领头那人才道:“公子仗义疏财,救我家乡数十人,我等感激不尽。”说完躬身一礼。从嘉忙躬身还礼,道:“在下不过略尽绵力,江北百姓流离,江南却笙箫歌舞,在下深感惭愧,不敢当啊。”那领头人听从嘉语气甚是真诚,不禁感叹,富家子弟中,竟也有如此良善之辈。他怔了一下,不再答话,心知今日已是无法报仇,便将手中钢刀指向那青年,喝道:“最好不要让我再碰到你!否则,我们决不留情!”话中还是满含愤恨,其实他也并不是不想报仇,而是眼见从嘉诚心相助,自己也不好得罪,再加上段居真和那青年都武功甚强,自己数人万万不是对手,也只好作罢。
说完,那领头人又带众强盗面向北方单膝跪倒,说道:“兄弟,我等无能,未能给你报仇。不过这却能换来乡里众人的性命,你当能含笑九泉了。”说完,站起身来,一挥手,示意众人跟自己离去。
那青年扶着那女子靠在一棵树上,向从嘉躬身一礼,道:“多谢公子救命之恩。”从嘉躬身还礼,道:“不敢。”那青年看得出来从嘉眼中略含责备之意,知他还在怪自己出手伤人,便道:“在下当时不过是救人情急,出手失了分寸,事后也深感后悔。想不到却还给公子添了麻烦,真是过意不去。”从嘉听那青年这样说,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得点了下头,又见那女子靠在树边昏迷不醒,便问道:“她怎么样了。”
那青年道:“她被那些人打伤了,可是我既要逃避那些人的追杀,又没有钱去给她请大夫,只能这一路都为她运功疗伤了。”从嘉听了甚是担心,忙道:“那她现在还好吧?我们赶紧进城吧,到城里再给她找个大夫。”那青年点了点头,伸手将那女子抱起,跟从嘉等人一起进城去了。
几人进了滁州城,便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下来。段居真身上还有些钱,倒是够了房钱和药费。从嘉便让裴厚德去请来了大夫,为那女子把脉开药。那青年让店小二去将药煎好,放在桌上,又把那女子扶起,将手抵在那女子背心,为她疗伤。过了半晌,那女子才醒了过来,见自己正靠在那青年怀里,从嘉等陌生人又站在一旁,便满脸通红,忙坐起身来。那青年起身,将药碗端了过来,说道:“妹子,来喝点药吧。”那女子微微一怔,说道:“大哥身上不是也没有钱么?怎么还为我买药啊?我不要紧的。”
那青年笑了笑,说道:“傻妹子,当然是你的身体最重要了,药既然买了,你总不能让我倒了吧。”那女子点了下头,将药喝了,还兀自不放心地叮嘱道:“哥,不要再乱花钱了。”那青年笑道:“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跟我一起到街上去讨饭的。”那女子扑哧一笑,不再接话,只是轻声说道:“哥,我累了,我想睡一会儿。”那青年点了下头,示意从嘉跟自己一起离开房间,又轻轻掩上了门。
夜色四合,清澈的月光照进房中。从嘉无心入睡,坐在窗口,任由清冷的光洒满一身。已经一年多,没有好好在家里待过了,其实他也一直很想家。从嘉自己心里也在奇怪,待在家里的时候,他想离开,想要那种仗剑江湖的自由,可是自己过了江,离开了江南竟多了几分以前从未有过的思念。
除此之外,刚一踏上江北的土地,便遇到了汉国那些连饭都吃不上的百姓,从嘉不由自问:难道给我‘一壶酒、一竿纶’,我就可以‘万顷波中得自由’了么?那些穷苦百姓有的不就是我所想要的自由么?可是他们那个执竿携酒、风花雪月,又有哪个泰然自若、恬淡自得了?从嘉忽然一下认识到自己小时的想法果然是天真,也终于明白了,爷爷那句“重光,你真的认为渔父的生活是这样的?”的问话是什么深意。事情绝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即使到了现在自己也不见得明白了“隐士生活”的真谛,《渔父》这两首词不过只是自己心中向往的一个美好境界罢了,或许这种生活永远都不可能属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