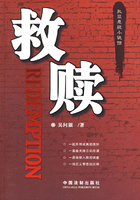翟让看官吏拿着委任状来了,没办法了,想想,不如就去,见机行事吧。翟让当法曹,常常趁着巡夜偷偷打开监狱门放人。时候长了,有人上报了,就把翟让抓起来。太守一查问,翟让如实报告,就把翟让判了死刑,填进牢狱。翟让做法曹时,结交了很多手下的法吏,都对他好,这一天,一个姓王的打开牢门,问翟让,你想咋办?翟让说,我落到这个地步,还能咋办哪,牤牛掉进井里,力再大也使不上啊。姓王的说,有你这身好武艺,咋能在这里头等死哩,翟让就连夜跑了。翟让连夜跑到家,这时候,家里人听说他坐监了,一帮徒弟就聚起来,正要去劫狱救他哩,他正好跑出来,家里也藏不住人,跑吧,往哪儿跑?听说瓦岗寨是个好地方,逃难的都往那儿跑,芦苇多沙岗多,水流多,便于打仗。翟让就跑瓦岗寨,那儿先有了很多逃难的人,那些人虽然都仇恨官府,可是会武艺的不多,大家就推翟让为首领,扯旗造反了。”
这天下午,一群孩子被他的诓儿迷住了,一直到天黑都没有割一棵草。很多孩子回家都挨了吵,甚至挨了打。也是从这时候,孩子们知道了他会嗙诓,开始听他嗙诓,说洋气点就是听他讲故事。
村里的孩子知道了他会嗙诓,下午放学到地里割草,就去他看地的地方。等草割得差不多了,就跑到他看地的庵子前,缠着他嗙诓。那个时侯,冢前村几乎所有十几岁的孩子都因为听嗙诓回家晚挨过爹娘的吵打。后来队长还在劳动中间歇的时候,把他喊来在田间地头嗙一段,让干活的男女劳力解解困乏。
再后来黑椹嗙诓就成了冢前村的一大骄傲。
07
黑椹嗙诓在孩子中出了名。后来听他嗙诓就成了冢前村孩子们必不可少的功课。嗙诓也成了黑椹生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当然,很多大人也喜欢听嗙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靠嗙诓打发寂寞无聊的日子,同时也给听他嗙诓的人带来快乐。这时候,他已经没有顾忌了,他嗙诓的内容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黑椹嗙诓在冢前村风靡了二十多年,让村里很多人都迷恋。
黑椹嗙诓的盛大场面与说书唱河南坠子相比也不相上下。冬天,在生产队的牛屋里,一到吃过晚饭,就聚满了人,等着听黑椹嗙诓,听他嗙“三国”,嗙“水浒”,嗙“西游记”等等等。其内容用古往今来、天南地北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每当这时,年老的,年轻的,小孩子(除了几个寡妇老太太,剩下的都是男性),有的坐在地铺上,有的坐在麦草(喂牛的)堆上,有的坐在干土(用来垫牛圈的)堆上,有的坐在自己带的马扎上,有的干脆席地而坐。
牛屋里除了牛粪和麦草的气味,还有烟味。黑椹爱抽烟,他抽的是“喇叭筒”,也就是自制烟丝再用废纸卷成一头粗一头细的烟卷,因为那样子很像唢呐,人们就叫这种烟卷“喇叭筒”。他因为有气管炎,到了冬天就咳嗽,抽烟的时候更是咳嗽不止,嗙诓只好停下来。孩子们总是迫不及待地等着听后边的故事,就对他说:“老椹爷,别吸了,嗙吧。”
他还是止不住咳嗽,等咳嗽停了,说:“不吸了,不吸了,一吸就咳嗽。”
到了深夜,大部分孩子都走了,没有媳妇的年轻人一看没小孩了,就喊:“老椹爷,嗙个孬诓儿吧,提提神。”
他就嘿嘿地笑笑,那笑声里充满了神秘,说:“那就嗙个孬的?”
很多人都呼应:“嗙吧,都等着听哩。”
“那就嗙个老公公跟儿媳妇吧。有一个老头,老是想找儿媳妇的事,就对老婆说:跟你老提不起来劲儿,我看儿媳妇不错,你看她能愿意不愿意?老婆说:今儿个下午不是要挂辣椒嘛,你就给她递。她站在板凳上,你站在下边,等着挂完了,她下来的时候,你就趁势把她拉到怀里,她要不动,这事就成了。老头按照老婆说的去做,果然成事,心里美滋滋的。回到自己屋里就对老婆说:跟你说的一模一样,我一把她拉到怀里她就不动了,我啥话没说就把她弄倒床上日了,真不错。那我问你,你怎么说得这么准哩?老婆说,当年你爹就是这样把我给日了。”
黑椹嗙完是一阵坏笑伴着一阵咳嗽,接下来是听的人一片哄堂大笑。那是最原始的关于性的段子,也仅仅能满足一下耳朵,耳朵还得把这些信息转换成另一种信号才能与性联系在一起。而没有过性经历的年轻人,想到的最爽的感受就是**了。
因为这些孬诓儿,让冢前村很多男孩子接受了最初的性启蒙教育。
到了夏天,人们就聚集在村中间的溜风口,黑椹就盘腿坐在为他准备的柳圈椅子上嗙诓。因为场地的开放,男女老少都有。这时候黑椹是不嗙孬诓儿的。很多时候讲“三国”、“水浒”,一段接一段,吊起人们的胃口,今天听了明天还想接着听。
黑椹因为嗙诓,吸引了村里很多人,特别是半大男孩,没事了总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跑到他的小屋里,听他嗙诓。这时候,大雨把黑椹家的土院墙冲成了一堆土。晚上,老远就可以看见小屋里有没有灯光。
有三个特别喜欢听黑椹嗙诓的男孩,一个是郑大力,一个是郑三明,一个是李二强。这仨人儿也是天天搅到一起的死党。他们几乎天天都去黑椹的小屋里缠着他嗙诓。
孩子们从开始听黑椹嗙诓,就开始喊他“老椹爷”了,其实那时侯他才五十来岁,还算不上老。后来年轻人也开始喊“老椹爷”,再后来“老椹爷”几乎成了他的名字。
一次, 黑椹嗙一个“扒灰头”的诓,郑大力问:“老椹爷,啥叫扒灰头呀?”
黑椹想了想,说:“比方说吧,你娶个媳妇,叫你爹日,你爹就是扒灰头。”
黑椹说完,嘿嘿嘿地坏笑了一下,问郑大力:“知道了吧?我说这个人就是个扒灰头。”
郑大力又问:“啥叫日呀?”
黑椹又嘿嘿嘿地坏笑了一下,说:“这就给你说不清了,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那可是一件特舒服的事情。”
郑大力就说:“既然舒服,那谁舒服还不一样?娶个媳妇叫爹日也没啥不好吧?”
黑椹一阵哈哈大笑,说:“这小子孝顺,回头我给你爹说说,是个好儿子。”
郑三明说:“老椹爷,那不中吧,再孝顺也不能娶个媳妇给爹吧?咱村还没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媳妇给爹的。”
黑椹再一次哈哈大笑,说:“小兔崽子,我给你们说不清,等你们大了就懂了。”
08
“文革”初期,曾经有一阵不让黑椹嗙诓。李怀生对他说:“黑椹我给你说,现在全国都在闹革命,你可不能瞎胡嗙惹事。”
黑椹笑笑,说:“中中中,我可不敢瞎胡说。”
后来,村里开展大辩论,把经常说媒的张媒红辩论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她和四家地主富农的男主人被划成了“黑五类”。不过村里也就开了几场批斗会,让这些“黑五类”头上戴着用报纸做的高高的圆锥形帽子,胸前挂一个用纸箱片做的牌子,牌子上用毛笔写着“地主×××”“富农×××”“寄生虫×××”字样。
批斗会第一次开得很热烈,支书李怀生带头喊口号,“打倒地富反坏右”“打倒寄生虫”……后来真的有人动手打倒了张媒红,接着又有人打倒了四个地主富农。平日里无怨无仇的革命群众群情激愤,把几个“黑五类”打得一塌糊涂。李怀生这时候也害怕了,这样打下去还不打死人哪,就急中生智,拿着一个广播筒尖着声喊道:
“停停停,都停住。”
革命群众这才停住手,张媒红和几个地主富农都弄得鼻口出血,衣服也烂了,张媒红的竖条棉布褂子前襟已经被几个男性革命群众撕成碎片撒了一地,她虽然已经五十多岁,可露在外边的两个**又大又白,一颤一颤的,很多男性革命群众听着支书说话眼睛却盯着张媒红的两个大**。
黑椹在乱成一片的男性革命群众中显得很瘦小,一忽儿就被挤到外围。他这时候想着这几个“黑五类”谁也不坏,也没有打他们的理由,可一些人发了疯一样打人。
他自言自语道:“这是弄啥哩,这是弄啥哩?”
这时候支书的喊声响起来:“都停住都停住,咱闹革命不能打人,只能文斗不能武斗。今天就到这了,回来啥时候再斗再敲铃集合,散会吧。”
李怀生说着偷偷地瞥了一眼张媒红的**,但他马上把眼光移走了。他是支书,不能因为多看几眼女人的**影响自己的光辉形象。
正在兴头上的革命群众有点意犹未尽,好不容易情绪才稳定下来。男性革命群众无所顾忌地盯着张媒红的**看。
黑椹也已经看了好几眼张媒红的**了,他这时发现张媒红其实还是很有女人味的。因为没生过孩子那**都那么大岁数了一点也不虚。看的眼热了,他恨不得上前抓住吃几口。
张媒红的丈夫李拴柱一点也不袒护老婆,他站在那里像没事人一样。黑椹走过去,小声对他说:
“你还不把衣服脱下来给她盖上。”
李拴柱说:“我才不管她哩。”
黑椹小声嘟囔了一句:“靠,屌人,自己老婆受了屈都不管。”
黑椹说着自己脱掉衣服送到张媒红面前。
李怀生说:“你屌黑椹瞎嘟囔啥哩?回吧回吧。”
几个“黑五类”已经从地上站起来。张媒红两只胳膊环抱着已经不存在的衣服前襟,脸上沾满了血,浑身都是土,两只肩膀一耸一耸的,她在抽泣。看见黑椹送过来的衣服,她两只胳膊放开,一抡推开黑椹的衣服,大声说:“看吧,都看吧,我还要啥脸面哪?”
李怀生说:“李张氏,你这是干啥?对大队做出的决定不满意?快点回家吧,回来啥时候再开会再通知你,你一定要积极配合,好好接受革命群众的教育,开好批斗会。”
黑椹还是强行把衣服给张媒红披上。李拴柱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张媒红脚下生风一样往家走,黑椹也紧跑慢赶地跟在后边,李拴柱却不紧不慢地走在后边。
李怀生看黑椹跟过去,就大声说:“黑椹你**跟恁紧弄啥哩?有点革命觉悟没有?”
黑椹放慢脚步,指指前边,“衣服……”
李怀生说:“日他姐,就你屌能。去把你的衣服拿走赶快回你自己家,别乱掺和。”
到了张媒红家里,李拴柱坐在堂屋当门有点得意。这下可翻身了,平日里都是他听老婆的,现在老婆成了“黑五类”,自己地位就提升了,再不用下厨屋做饭了。**,也该让她伺候伺候老子了。
张媒红钻到套间里换好衣服才出来。她对李拴柱说:“都啥时候了,你还不做晌午饭?有你这种人吗,老婆成这样了连屁都不敢放。”
李拴柱站起来,把身上的英雄气概都表现出来:“老子不做饭了,你黑五类寄生虫威风啥哩?从今往后你得给老子做饭,伺候老子。”
张媒红一听就蔫儿了。她现在是黑五类,是寄生虫,再不能在男人面前威风了。
黑椹在一边不忿,对李拴柱说:“在外边装装样子还中,到家了你还瞎摆啥了?快点去做饭吧,看她被斗了一晌,满脸都是血。”
李拴柱这个平日里像软蛋一样的男人这时候牛了起来,他拿着黑椹的衣服往他脸上一摔,气势汹汹地说:
“你**不是驴吃圪针多扎一嘴?俺两口子的事你瞎叨叨啥?我看你是没安好心,快点拿着你的屌衣裳滚蛋。”
黑椹拿起衣服没敢多说就走了。这个**拴柱跟一头公牛一样胡乱抵人,还是不惹他为好。
接下来的几场批斗会,都是闹哄哄地瞎吵吵一阵完事。李怀生控制得很好,没有再出现打人和撕碎张媒红衣服的局面。后来慢慢也就过去了。
黑椹曾经偷偷跑到过张媒红家好几次。他非常怀念她的两个白**,就像怀念大辫子姑娘的身体一样强烈。但他一听到李拴柱歇斯底里的喊叫就被吓跑了。后来有一次趁李拴柱不在家跑过去坐了一会,与张媒红说了一会话,有几次走到她身边都想把手伸出来去碰碰她的**,最终却没敢去碰,更别说摸了。
张媒红好像看出了黑椹的心思,只催着他快走,说:“你赶紧走吧,要不拴柱回来了又该骂了,我都叫他骂怕了。”
黑椹心里不想走,又怕拴柱回来给他玩下不来台,就说:“那我走了,你想开点,别把这事放在心上,你也没犯过啥大错误,不就是说个媒嘛,很快就会过去了。”
黑椹渴望亲密接触张媒红的激情被逐渐熄灭。从他看见她的**开始向往,开始是怕李拴柱,过了一段时间李拴柱不厉害了张媒红又恢复了威风,他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招惹张媒红了。这事最终除了张媒红的两个**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清楚的痕迹,再没有任何值得回味的细节。
闹革命的高潮在冢前村并没有持续太久,黑椹嗙诓也并没有停几天。那时候人太无聊了,虽然村里有宣传队,后来还有了电影,但很多时侯晚上还是没事干,几个人聚到一起听他嗙诓还是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