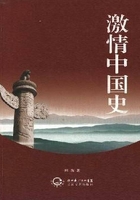在县文联,我与高雁讨论了吴赛男的《厮杀在考场》,我们的统一认识是,小说从语言、结构、立意等方面都不错,也很有可读性,但就目前长篇小说市场的的疲软,一个无名作者的作品要出版困难很大,只能走自费的路子。
我说,吴赛男很有潜力,又是第一部,你看县文联能不能想点办法,帮助帮助她。
高雁笑了,说你还不知道县文联经费有多困难?
其实说之前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无奈地摇摇头,说不难为高主席了,我再想办法吧。
中午吃饭的时候,高雁要叫人陪我,我坚持只叫了我在县委组织部的街坊、同学张建兵和吴赛男。
张建兵与我和李书相一样,也是一起听老超爷的故事、一起手淫过的死党,他如今已经是县委组织部组织科的科长了。今天叫他,我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出书也。在饭桌上,我把这个记忆中我从来没有夸奖过的铁杆朋友大肆夸奖了一番之后,很直接地将筹集出书经费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他。
我说张科长,据我了解,你在柳青县的威望之高,声誉之大,超过县长,尤其在社会各界的关系,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加上组织部的影响力,你在柳青县说句话那是响当当的,是吧?
张建兵忍住笑,黑着脸说,大作家,你想说啥就直接说吧,别假惺惺地在那说假话了。
我说,我说的都是真话,真心话,怎么叫假惺惺?不过下边这件事,也只有你张科长能办成。
我把书稿拿出来,说,这是赛男第一部长篇小说,自费出版需要两三万的经费,你得帮这个忙。
张建兵拿着书稿翻了翻,没说话。我说你表个态呀。他说我试试吧。
我知道他欣然接受了任务,故作沉稳地说,高主席,赛男,咱们敬张科长一杯吧。
吃过饭,高雁为我在宾馆安排好房间,吴赛男陪我说话,他借故忙走了,临走给我使了个坏坏的眼神,我明白他那眼神的意思。
我们继续讨论出书的事情,吴赛男说要知道出版这么难我就不写了,辛辛苦苦写出来得不到稿费还得自己拿钱出,爱好文学这成本也太高了。再说了,你让人家张建兵替我化缘,我怎么还人家这个情啊?
我说赛男你别管了,我跟张建兵的关系村里谁不知道,他为你出书帮忙化点缘也是应该的,村里能出个女作家也是全村的荣耀。你就别有啥顾虑了。回头咱再卖点书,如果卖得好了还能赚点钱呢。
她摇摇头,说谁会买俺一个无名作者的书?
我说你可别这样说,以我预测,很多教师都会喜欢你这本书,你就等着签名售书吧。
吴赛男叹了口气,说三哥,让你做难了。
我说哪用得着这么客气。又说,你把电子稿发给我,我回去给《殷都晚报》副刊部的编辑说一下,在晚报上连载一下,多少能挣点稿费,最主要的是能扩大影响。
吴赛男嗯了一声,说三哥你睡一会吧,喝过酒困吧?你睡你的,我看会电视。
我说我不困,说会话吧。你要困了就回去歇会,晚上吃饭再叫你。
她往床上一躺,说大热天的我跑啥呀,又不怕你。
我说那是那是,你想睡就睡会。
而心里,却是波涛汹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睡也睡不着。
次日一大早,我与吴赛男坐上了去吴赛娜家的长途汽车。这是我很久的心愿,有些迫不及待。
见到赛娜的时候,我的心反而平静了。我是以她妹妹赛男的男朋友的身份被介绍给她丈夫的,这是走进了她家见到那个比她大近二十岁的丈夫之后吴赛男随口介绍的,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看到赛娜也愣了一下。
赛娜生了三个孩子,都是姑娘。她们依次相差三岁,楼梯一样站在我们面前,瞪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看着我和吴赛男。来往少,她们对她们的小姨很陌生,更别说我了。
赛娜的身体已经膨胀得找不到当年的身影,脸上倒是没有皱纹,头发有些凌乱,衣服也很随便。她见到我的一刹那,眼睛里似乎闪过一道亮光,但那亮光如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平静所淹没。
等到她丈夫和孩子都走了,她说,怎么会是你?
我说,我不见你永远难安心,就来了。
她说,也不打个电话,好有个准备。
我说,是我不让打的,怕一打电话你不让我来。
赛男说你们别光说废话,好好说会话吧。她去了院子,给我们留下了空间。
我说,不说废话,好好说。
我们相对而坐,互相瞟一眼,躲开,再瞟一眼,再躲开,竟无话可说。
好久,赛娜说,你家里都好吧?嫂子和孩子都好吧?
我回答说都好。然后再次陷入沉默。我突然怀疑,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山村妇女,究竟是不是那个我魂牵梦绕的赛娜?
在赛娜丈夫的兄弟与孩子们的叔叔声中,我煎熬般的吃过了晚饭。然后被安排在一个空旷的房间睡觉。夜里,在蚊子轰炸机一样的盘旋中,我无法入睡,就反复地把二十年前的赛娜跟眼下的赛娜进行比较,比来比去,我发现了时间的魔力。
06
从赛娜家回去,走到山路的时候下起了大雨,塌方的石头把路给堵住了,我们的汽车被困在了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大雨一直下,路一直不通,人们都心急如焚。我和赛男并肩坐着,一路无话。
眼看着天黑下来,车已经堵了足足十个小时。两顿饭都没吃了,很多人都在说饿,有的孩子干脆喊起来:我饿,我饿。
幸好赛娜让带的有蛋糕、饼干,中午时我们偷偷吃了几口。车上饥肠辘辘的人如果看见我们手里的蛋糕或点心,肯定会露出虎视眈眈的眼神,保不准谁会张口索要甚至还会伸手抢夺;还有那些饥饿的孩子,他们少气无力的喊声让人不忍听闻。
在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赛男拿出部分蛋糕、饼干堵住了几个孩子的喊声。我附在她耳朵上说这路不知道啥时候能通,咱自己也得留一点吃的。她说听着孩子喊吃不下去。
堵车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除了吃不上饭填不饱肚子,排泄也是一个大问题。雨下个不停,女人们打着伞在哗哗的雨声中顾不得矜持,走到离车很近的地方就开始作业,泄光在所难免;男人们相对有些优势,下了车靠着车拉开裤子拉锁就可以释放。
赛男下车方便后回来就对我说,真想当个男人,多方便啊。
夜间十点多,雨停了。车里的空气很闷,加上人们十几个小时不停地释放的气体,还增加了一些异味。有人睡着了,有人在小声说话,有人下车在外边站着。赛男说下去站一会吧。
我们在黑暗中走到一个山洼的一棵树下。她问我你是不是很失望?我摇摇头,说本来就没希望,失望什么。她说赛娜的形象,她的形象你想都想不到吧?其实她收拾收拾还是很有韵味的,她已经无心打扮了,她的生活态度很消极。
我叹口气,说,农村嘛,都是这样,时间不饶人哪。
雨后盛夏的山中空气有点凉,赛男突然偎在我怀里说,哥,我有点冷,抱抱我。
黑暗中,我伸出双臂抱住她,她的身体更紧地贴着我的身体,我感觉到了她的体温,凉意不觉消散。良久,不知道是我主动还是她主动,我们吻在了一起,后来我们的手也开始动起来,在对方的身上用力地抓摸。
哥,你要了我吧。
我不说话,更紧地抱住她,双手在寻找她裤子上的拉链。她不停地叫着我,哥,哥,哥……
就在我拉开拉链的时候,我眼前突然出现了赛娜,她臃肿的身体,凌乱的头发,幽怨而深邃的眼睛。
我迅速地推开赛男,低沉而坚决地说,不,我不能。
那一夜,我们相拥在车上而眠,一直到天亮。雨停了,路很快就通了。到了柳青县,我没做停留,马上坐车回殷都市。
当晚,我把晚报副刊编辑刘建兴和另外一个写小说的文友贾成约出来喝酒洗脚,顺便把吴赛男小说连载的事情说了,还讨价还价地把稿费搞定。
刘建兴说回头你得让作者来一趟,让我见见,看是什么天仙美女把李秘书长迷住了。我说可不敢乱说,是我妹。
你姓李,她姓吴,是表妹吧?哈哈……刘建兴的一阵坏笑让我无法申辩。
贾成也起哄,说平时你抠得不得了,才舍不得请我们洗脚呢。
我不再辩解,这事越辩越说不清。
因了那个晚上,很久我都没有与吴赛男联系。这天,张建强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一躺。我兴冲冲地给吴赛男打了个电话,说估计出书的经费张建强解决了。她当然很高兴,说三哥的面子真大。
我们到了张建强办公室,才知道他是要推掉这件事。他把书稿和五千元钱交给我,说江峰,赛男,真对不住了,有点特殊原因,这事一时半会弄不成了,我个人也没太大的实力,这五千别嫌少,也算是对赛男的一点帮助吧。
我不去接书稿和钱,瞪大眼睛看着他,急得恨不得上去把他撂倒,说这算哪回事?你吐出去的吐沫又咽回去了?跟我也搞这一套?还算不算男人?
张建强说你说啥都行,反正我是弄不成了,真想让我办,最少得等一年以后。
我从他手里拽过书稿和钱,气冲冲地走了。说赛男咱走,懒得跟他这种人说话。
赛男难为情地看看我,又看看张建强,说建强哥我们走了。
吴赛男跟上我说,三哥,你对张建强太那个了吧,人家还拿了五千块钱,也算帮忙了。
我气极败坏地说,还不是怕影响他的仕途,误了他当官,那他当初别答应啊,这不是涮人吗?
吴赛男说人家不是说有特殊原因嘛,别生气了三哥,我请你吃串串香。
吴赛男的劝解让我勉强收起我的余怒,一边掏出电话一边说,把高雁也叫过来。
高雁的手机却关机,办公室没人接。我说赛男叫给你们学校许文魁校长吧,他是我师范的同学,当时关系还不错,就是这些年联系少了。
吴赛男说我给他打电话,你给他说吧。电话接通,许文魁一听是我,马上表示火速赶来。
我提出叫许文魁,也是有目的的,但这个目的不能给吴赛男说,说了怕她接受不了。
因为有许文魁,我们放弃了串串香,找了个比较像样的饭店。我们两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有说不完的话,碰不完的酒,不知不觉都喝高了。酒喝高了话就靠外,我很顺溜地就把那件事说了出来。
他一听,就痛快地说,好,我们学校出了个大作家,我们还不知道,出书经费的事情我给老一说,无论如何都得解决。
我说就是嘛,说到底也就是一个高价学生的赞助费,你们一高财大气粗,这点小事算啥。
吴赛男趁许文魁出去,对我说你真是为了我出书啥关系都用,你不知道我们学校老一,扣得葛朗台一样,根本没戏。
我说你不懂,我会想办法让他们解决,你等着吧。
07
吴赛男出书的事情,影响到了我和老婆的团结。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天在我与许文魁通完电话之后,刘玉秀说李江峰,你有点过分了啊,你看看你这几个月都在干啥,为了一个吴赛男,跟张建强耍横,这又跟许文魁发脾气,我看你是当年没娶她姐姐为妻,这会想从她这里找回初恋。
我愣在那里,看着醋意大发的刘玉秀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讪笑了一下,想讨好她。
刘玉秀说李江峰,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你不想想,你一个下岗职工,说是市作协的副秘书长,要啥没啥,人家凭啥听你的给她出书拿钱?再说了,你自己想出作品集都没见你行动过,为别人的事看你上心的,恨不得把自己卖了。
我说为自己不是不好意思嘛,为别人没人说闲话。
刘玉秀摸摸我的额头,说不烧啊,怎么净说胡话。没人说闲话?你脑袋被驴踢了吧,傻子也能看出来你对吴赛男好得没边,你说别人会怎么想?
我马上申辩说,刘玉秀我给你说,我们可是啥都没有啊,你别乱说,更不能乱想。
你说的话鬼才会信。刘玉秀说完就忙去了,把我撂在那发了好一阵呆。
我对许文魁信誓旦旦的表态抱很大希望,偏偏就没有想到他那是酒话,我不光高估了我自己,也高估了他这个副校长的能量,忘了他根本就没有话语权。电话里他告诉我,老一说出书这钱不能拿,学校这么多教师,谁出书学校都拿钱那还不乱套。
我无计可施,只能在电话里把他说的老一臭骂了一通,放下电话胸中难平,却又被老婆一顿教训。
我站在小卖部的门口,看着夕阳西下,突然感觉一阵寒意。我对着里边说刘玉秀我出去转转,心里堵得慌。
刘玉秀说堵得慌是自己找的,好好想想吧。
我沿着洹河漫无目的地转悠,洹河水在逐渐暗淡的夜幕中变得亮起来,那波纹也变得诡秘起来。不觉已是冬天,脑海里无端地就响起了《大约在冬季》的旋律。
不就是钱吗?我想。而钱我一向是不看在眼里的,不放在心上的。这么多年能够坚守文学,坦然生活,就是因为不为钱所累。
我得挣钱!我突然冒出了这样的念头。老婆说得对,我自己的作品集还没出呢,也需要钱。等我有了钱,专门搞一个出版基金,帮助没钱出书的文友实现夙愿。这样想的时候,我开始谋划出版基金使用的具体细则,比如资助的作品必须是纯文学的,作者应该有较大的潜力,还有,作者的的经济条件不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