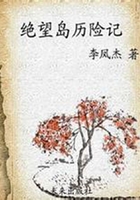就在我兴致勃勃地为我的出版基金使用方案进行思考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一看号码,是高小非,跟我特别铁的一个文友,以前在殷都县教书,前些年去省会应聘做了记者,这几年家庭经济建设搞得不错。电话里他说要请我喝酒,还有廖主席、刘建兴、贾成等。
我心想真是时候,正郁闷得不知所措,有人陪我喝酒,简直就是正想瞌睡别人给了你一张舒适的床。
我回到小卖铺骑上自行车,飞也似地向约定地点驶去。
饭店是我们文友聚会经常去的一家,叫仙客来,6号包间。我们之所以把聚会地点选在仙客来,不光是距离文联不远不近,最主要的是好吃实惠,饭店名字也好,我们一来,都成仙客了。6号包间最初是廖主席选的,他喜欢6,说6是他的吉祥数字,后来只要我们去仙客来,只要6号没人定,老板娘总是把6号留给我们。
我进了包间,发现除了廖主席没到全到了,酒、菜也已上齐。我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宾席旁边的位子上,与大家一一握手,大家嘴里说着些荤话涮话,气氛很是热闹。
我说各位公公都还活着呀,天冷了,小心冻着啊。公公是长期以来我们相互之间的戏称——我们都以贬低他人性能力的低下而产生快感。
我的问候马上得到了回应,有人说,我看李公公这几天吃胖了,头上都是肉了。
又有人说,我看李公公嘴唇好像特别湿润,是不是练吹箫了?
贾成说李公公这段时间泡妞呢,据了解还是个写小说的。
刘建兴说李公公还能泡妞?泡也是干着急,啥事干不成,人家姑娘还不被他急死。
我乖乖地吃了他们的招,坐在那里不说话光喝水。高小非问我又有什么新作,我说正在写一个长篇小说《文人》,这一段时间却写不下去,没心情。
贾成插话说他光顾给什么吴赛男出书跑赞助了,哪有时间写啊。
我有点气急败坏地说,跑鸡巴球赞助,都泡汤了,到现在才弄了五千块钱,还差得多呢。
高小非说这事不能急,得慢慢来。
我说急也没办法,我的一个在组织部的街坊同学都答应全包了,找三两个乡镇党委书记很容易就解决了,偏偏我们县委书记掉进去了,估计得判几年,全县涉及到六十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人心惶惶,这事他一推六二五,自己掏腰包出了五千。又找了作者学校领导,副校长是满口答应,老一却一毛不拔,这事又没弄成。
说话间,廖主席来到,寒暄后在主宾席就坐,酒局开始。喝白酒的人倒上白酒,喝啤酒的人倒上啤酒,喝饮料的人倒上饮料,白酒啤酒饮料都不喝的人倒上茶水,然后在廖主席的倡议下共同举杯相碰,一起畅饮。
廖主席夹起一块猪耳朵说,大家都喜欢吃猪耳朵,还喜欢吃猪蹄,我琢磨了个课题,让科学家培育一种猪,身上一边长猪耳朵,一边长猪蹄,隔一段时间割掉一茬,停几天再长出一茬。
大家都说这是解决猪耳朵猪蹄稀缺的好办法,一头猪两只耳朵四只蹄子太少了。还有的说干脆让猪再多长几个胃,也把猪肚的问题解决了。
接着又讨论贾成的小说写得越来越好了,一连在几家大杂志发表,越来越有名气了,这样发展下去他的生活将会有大的改观,最少能结束单身生活(媳妇五六年前因为他写作把家里搞得一穷二白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有了老婆两个人一起买套房子,也可以安居了。
对这样的话题贾成并不热衷,他轻描淡写地说,我现在多自由啊,想咋地咋地,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饥,背着笔记本,走到哪写到哪,爽死了。
贾成算是漂在城市的文人。当初因为爱好文学没考上大学,只能回农村种地。他种着地仍然不忘文学,继续搞创作。1988年,为婚事发愁的贾成因为文学终于搞到一个老婆,把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这应该是他迄今文学给他带来的最大的收获。但后来老婆还是受不了他痴迷文学不顾家庭建设的做法,跟一个乡镇企业的业务员跑了,把他自己扔在家里继续对文学走火入魔。后来父母相继去世,他干脆把几亩地转包给邻居跑到市里,租了一间小房子,买了个二手笔记本电脑,专事写作。一个年近不惑的男人,独自漂在城市,又没有固定收入,很不容易。而贾成天天乐呵呵地很开心,只要有饭局,他每叫必到,当然他从来不买单,大家也不让他买单。
饭局一直持续到夜间十点多,大家才依依不舍分散。高小非与我同路,我骑车带他,到了家门口,我们谈得还不尽兴,他又要请我洗脚。我当然乐意,遂驶向洗脚店。
那一晚,我与高小非谈了很多,后来不知不觉就说到了我们合作的事情。这种合作我虽然心里不舒服,但最终解决了吴赛男出书的经费问题。
08
我与高小非的第一次合作,我躲在柳青县宾馆里没出面就拿到了五千元。当然,我也付出了劳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说服吴赛男把柳青县一高的问题提供给我们的高小非记者。吴赛男开始是真不愿意说学校的问题,她说我这样做不是成内奸了吗?我说你还把自己当成学校的顶梁柱了,他老一这么不仁义,你出书连一点都不支持,还说了一大通不是人话,你还护着他。反正都是学校的钱,让他花点活该。
吴赛男说要是让人知道是我干的,我以后还怎么在学校呆啊。
我说只要我不出卖你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就这样,我把柳青县一高乱收费的情报搞得一清二楚,然后模仿学生家长的口吻写了一封举报信,高小非就拿着这封信去学校采访了。学校老一不光像孙子一样给高小非陪笑脸作解释,还叫上教育局分管副局长、三个副校长、三个教导处领导陪高小非记者共进午餐。饭后,学校老一像做贼一样给高小非包里偷偷塞了一个红包。几个小时,高小非就把别人口袋里的一万元钱搞回了自己包里。他到了我蛰伏的房间,把信封里的钱一分为二,塞给我一份,说怎么样老兄,快吧?我接过钱,没说话,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事后,我多次想,自己作为一个柳青县人,不能给家乡做贡献,但最少不能给家乡找事。常言说好狗护三村,而我做的这叫啥事?我他妈的连条狗也不如,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反过来又想,那些人为了利益不顾法规条例,乱收费增加学生家长经济负担,收拾收拾他们也该。
虽然抵触高小非的做法,而且内心总是受着做小人的煎熬,但还是抵制不住迫切筹到经费的诱惑,又与高小非合作了几次,很容易就搞到了三万块钱。
干完最后一次,我对高小非说,兄弟,今后我再也不参与此类事情了,我受不了那种负罪的煎熬,但我还是非常真诚地谢谢你。
高小非笑笑说,我知道江峰兄清高不凡,但这就是现实,这样最少比去求人化缘舒服一些。换了别人,我也不会这样合作。
我苦笑了一下说,我清高不凡?算了吧,清高不凡只能算文人的装模作样了。
高小非揽着我的肩膀,说老兄别这样,社会上对文学包括文人还是很看重的,作家的社会地位还是很高的嘛,你看看网上,文学网站还是最热闹的。
我说,当然,最少咱自己得看得起自己。
为了不再影响我和老婆的团结,为吴赛男出书的事情我只有转入地下,筹钱的事肯定不能告诉刘玉秀,跟吴赛男一起去省城出版社也只有说谎去开会。她因为忙于生意,并不与我斤斤计较,我们也就相安无事。
在等待出版社审书稿的时候,我有机会静下来,再次走进老超爷的世界,继续写《文人》。支持我的老婆知道我写作便不再打扰我,我可以一个人躲在家里,沉浸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坐在电脑前用键盘抒发我对老超爷的理解。
这时候,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尘嚣离我远去,没有欲望的诱惑,没有功利的侵扰,没有灵魂的躁动……我如一头思想的牛,静卧在自己的领地反刍生活;我如一匹刚刚经过鏖战的战马,伫立在战场之外回忆驰骋;我如一只孵蛋的母鸡,伏卧在自己的岗位上释放体温……我的灵魂在无限的空间自由地飞翔,我的思想在想象的草原上疯狂地奔跑,我跟随着我的主人公的情绪,或笑,或哭,或平静,或激动……
在没有白天黑夜的创作中,两个多月转眼即过,二十多万字的《文人》终于完成。敲完小说的最后一个字,我把双手交叉抱在后脑勺,扭动了几下有点不舒服的脖子,把一条腿翘在电脑桌上,闭着眼睛发了好一阵呆,然后脱得一丝不挂,跑到卫生间去冲澡。卫生间没有暖气,也没有浴霸,喷头里流出来的热水不足以把卫生间的温度提升上来,我冻得有点发抖,站在热水下不敢挪动半步,强忍着寒冷把自己洗了一遍。站在镜前刮胡子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头发像蒿草一样荒长,有点像印度电影《流浪者》里那个拉兹;眼窝深深地陷下去,周围有一圈黑黑的眼晕;脸两边也凹下去,颧骨显得格外突出,嘴好像向外凸了很多。
看着尖嘴猴腮的自己,我不禁一阵心酸。仅仅两个多月,自己就成了这个样子——尽管写作对自己来说是一种享受,而精力的透支与摄入营养不够对身体的伤害显而易见。这时候我又想到了作品的命运——写作过程中我顾不上去考虑她能不能发表或出版,完成后我不能再不去考虑她的去向,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谁愿意得不到报酬还要自己掏腰包去出版,当然更不愿意让她躺在电脑里睡大觉。
如果不是手机上的时间提醒,我根本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我走出楼道,一阵寒风裹着雪花吹来,从脖子里钻进身体一些雪粒,刹那就让我浑身透凉。我放弃了骑自行车的打算,步行着向外走。大街上,已经有了一些积雪,被汽车碾压得黑乎乎硬梆梆的。街道两旁的树的枝条都被雪裹了一层包衣,白花花地在风雪中招展。庆祝元旦的彩灯悬挂在线杆上,被风雪吹打得失去了鲜艳。
我突然想起来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去店里看看老婆?似乎并不迫切,虽然已经有些日子没有与她见面,更不用说亲热了,但现在我更想找一个人交流,倾诉一下自己两个多月来的感受与体验。找谁聊聊呢?廖主席?上午九点这个时候,他一般会正忙于工作,办公室人会很多,不行。刘建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再说报社编辑部的大办公室也无法单独交谈。想来想去,只有贾成了,他也许在睡觉,把他叫醒会打扰他的好梦,但我与他之间没有那么多讲究,想啥时候找都没问题。
我一边缩着脖子走一边掏出手机,打通贾成的手机,他却挂断了。这家伙在干啥坏事呢,连手机都不接?我想。准备再打过去,他发来了信息:我在北京,来签中篇小说《我的月亮》的影视改编权,已定,八万元,后天回去请你喝酒。你的长篇写完了?
我马上回信息祝贺他。如此重大而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因为大家知道我埋头写作,怕打扰我而没有通知我。我为贾成高兴,他终于翻身,可以用这笔钱买个房子安居乐业了。这样想着,我感觉风雪也不那么寒冷了,漫天翻飞的雪雾,在我眼里生动起来。我嘴里不由发出一连串喂哟喂哟的喊叫,那声音在冰天雪地里挣扎着,一点点在空中弥漫。
09
邻近春节,我与吴赛男去省城出版社把包销的一千册书托运回柳青县。出版社很意外地对她给予照顾:总印数三千册,作者包销一千册,按照书定价的五折计费,余下的两千册出版社负责发行,亏赢与作者无关,如市场销售好,再加印作者按比例领取版税。
这是出版社一个领导对吴赛男关心的结果——这个出版社领导与她一个大学老师(一个文学评论家)是好朋友,就在出版社审过书稿确定出版的时候,她意外地碰到了大学老师,他一句话,就改变了原来商定的全部自费意向。
在印刷厂仓库,吴赛男一拿到撒发着油墨气味的新书,就抱着我激动了好一阵。她说我得怎么感谢你啊!
我说跟我还客气,说什么谢啊。我拿起一本书,说你得给我签个字,将来成名了这书就升值了。
她说你说吧,你让我签多少本我签多少本。
这本书最后的结果,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包销的一千册书,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跑了几家单位与企业,基本卖完。且不说后边销售得怎么样,能不能拿到版税,这一千册已经赚了些钱。吴赛男把原来交的一万多元和赚的近一万元都交给我,说三哥,我的书能出版我就满足了,这钱都应该给你。
我把原来交的书款留下,赚的钱还给她,说,赚的钱是你的,你辛辛苦苦写的,也算是报酬吧。回头卖得好了你还可以拿到版税。
最初为吴赛男筹集的三万元钱,最后没有用到,这让我有了底气。我的那部《文人》,已经给了一家有名的出版社,能得到出版社认可,本版出版拿到版税当然更好,即便不能本版出,也有现成的经费在这放着,我根本不用担心这部作品出版的问题了。
在柳青县呆了两天,又回去看了看爹,才回到殷都。这时候大街小巷已经年味十足了,学生们放了假,开始在大街上玩耍嬉闹,一些小学生开始在河边或广场点炮和玩摔炮,清脆的炮声和隐隐的火药味在空中飘散。很多人都在忙着购买年货,商场的促销更加热火朝天。我背着我的牛筋包,走在年味浓厚的大街上,感觉生活真是绚烂多彩而充满魅力。心里不禁激动起来,哼起了那首曾经风靡全国的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