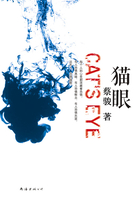天早早就黑了,饭桌边坐满了大人,除了我爸和大伯,都是大学生。他们好像都不做正经行当,其中一位是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在县城街道福利五金厂生产削铅笔用的小刀;另一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在小队里记录粪水的桶数;而二伯研究的是古典文学,在海里抓鱼摸螃蟹。
其实我爸1952年也接到去人民大学上学的通知,只是银行的领导不肯放人,被截留在了漳州。这件事对我太重要了――不然我要到哪里去投胎呢。
桌上有煨刀豆,烤豆干,炖芥菜,还有煎鹅肝清蒸溪鱼。那些溪鱼下午我们到家时二伯刚从溪里拎回来,二伯把它们放在桶里,倒上清水,让它们游给我看。见到我,那些鱼眼睛瞪得圆溜溜的,和葱姜一块躺在盘子里了,还是不肯闭上眼睛。桌子正中是一大盘的烟鹅肉。真香啊,香得喉咙都颤抖起来。这些菜都是大伯做的。大伯说,家里这只大公鹅真好,十五六斤,肥瘦正合适,正好下高粱酒。地上摆着一队高粱酒,58度的。
在酒桌上,二伯是老大,大伯是老大的老大。我就站爸爸身边,我觉得自己只不过比老大们矮了几个头而已。
大学生们突然对我的酒量发生了兴趣。我当然没喝过酒。华东师大的从航空学院的手里接过酒瓶倒了满满一杯,坏笑着递给我。我接过酒杯,一仰头倒进了肚子里。呀,脑袋里立刻丁丁当当开起了铁匠铺。我赶忙捂上耳朵,跑到墙边,把右边耳朵抵在了黑黑的墙上,好像在听隔壁的人们说话。大学生们把嘴张大了,很礼貌地望着我。我堂伯方昌禄就是在那面墙的另一边把最后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大脑。他的母亲被保安大队乱枪射杀在他的身边。那几间房子都被烧光了,只剩了后背一面墙。
二婶进来了,说,你们这群大人啊,跟小孩子没两样!
她装了满满的一碗烟鹅肉,拉了一只小板凳让我坐下来,吃。吃完了,又装了一碗。我问她为什么不吃?她说,吃过了。见我望着她干裂的嘴唇,她下意识地伸手把嘴挡住了。这时,院子里那只母鹅叫唤了两声,二婶笑了:“你知道母灰鹅为啥要咬你屁股了吗?”
我点点头,打了个饱嗝。公鹅肉香啊。
爸爸他们三兄弟坐成一排,望着我笑。
见我酒后没有什么过于异常的举动,比如走路如在浪里行舟,或者面如熟螃蟹当场吟诗一首,大学生们有点纳闷,开始研究起我的酒量来,因为意见不统一,有人提议用实验验证一下,叫我再喝几杯。二婶一听,赶忙把我拉到隔壁找三堂哥和堂弟玩。
三堂哥大我两岁,堂弟小我一岁,他们盯着我的嘴巴,表情非常认真。原来,他们一块鹅肉也没吃到,一人只分到了半只鹅爪子。烟鹅肉香啊,香味排着队从我嘴里涌出来。后来我再也没吃过鹅肉,因为一见到鹅肉我就忍不住要想起当年他们兄弟那两张表情认真的脸,怎么也吃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