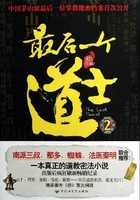我不知道多年以后大婶抚摸着大堂哥的那坨大龟背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反正我是看一眼难受一次,不是滋味。有人说,都怪他是个小地主,小地主还需要什么正面形象呢。
其实贫下中农的日子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我小时候是个人民公社社员,就生活在贫下中农当中,对他们的生活状况有彻底的了解:贫下中农只不过是有资格处在亢奋之中而已,比村里的牛好不了多少。在领袖的眼里,我们都是数字,是可以随手涂抹掉的。
如果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让绝大多数的人民无法过上正常生活上,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天上的乌鸦见了,也要愤怒得叫上两声的。
眼看着屋顶一天一天矮下来,二婶心里渐渐怕起来,她开始担心自己哪一天会扛不住了,她不知道怎么是好。这时,二伯从南京跑回来了。这是1962年春节。此时二伯已经不是一个劳教犯了,他是个重工业工人,在南京民生砖瓦厂,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产砖块和瓦片。
因为家庭的原因,二伯的古典文学功底足够的深厚,上南京大学时经常在学报上发表文章。陈中凡先生一眼就看上了他,高兴坏了――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寂寞高手在老年时终于找到传人的那种喜悦。可是大四时“反胡风”,他被隔离审查半年。他跟胡风有关系吗?没有。他跟北风倒是能扯上点关系,他是南方人,最怕刀子一般的北风。他把陈老师审阅过的论文交班长代管,班长却用自己的名字发在了南大学报上。高教部长何其芳眼前一亮,毕业后把他要去了,当个人秘书。只是很快发现文非其人,又将他退了回来。班长是个党员,胸怀坦荡,他承认自己是贼,要求把稿费退还给二伯。二伯不肯要,他说,那钱是脏的。陈老师要求二伯扩大研究层面,再写一篇论文。于是,他写了80万字的《第三代文学史》,把唐、宋、明、清的文学串了起来。陈先生把它推荐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定好了,要出。二伯正在信里和被监督劳动的我爸盘算大笔稿费的去路,不想却被开除公职押送南京石佛寺农场劳动教养。
本来毕业时陈先生要求校方把他留作助教,当局不肯,陈先生也不退让,他说那就别分配,我留作个人秘书,薪水本人承担。陈先生面子太大,当局只好就近把他分配到了南京市27中。没想到一年多后就成了右派了。
陈先生的大儿子竟然是石佛寺的党委书记,万幸。陈书记听他父亲的话,安排给二伯的工种是夜间在长江边捕鱼,但没有任务定量――数字化管理会害死人啊。二伯会抓鱼,当然会吃鱼,因此大饥荒的时候他居然没有和夹边沟的同类们一道,灵魂儿飞到天堂学习小鸟。那时我爸爸就在鱼米之乡的海澄饿得全身浮肿,差点被黑白无常拉走。
三年后,教养结束,农场想把他留作财库,可他心里还想着他的古典文学,没有接受。结果却被安置进了砖瓦厂,成了重工业工人,每日模仿牛和马,从清晨到深夜。
还好,重工业工人是可以回家过年的,十年了,该回家了。师娘取出500元的存折,陈先生说,尽管用,但必须留下返回金陵的费用。
二伯只要了100元,回到家后,他用剩款买了粮票寄还给老师。那时候,粮票比性命值钱。
他再也不回南京去了,他要奉养母亲也就是姑婆,他要和二婶结婚。二婶不识字,二伯认识很多很多的字。他写信告诉陈老师,自己必须和她结婚,因为恩情,恩情比泰山重很多。这年二伯34岁,二婶31岁。他们一起生活了14年,直到1976年5月,二伯肺癌去世。这14年里,他们养育了三个孩子:我堂姐,三堂哥,还有堂弟。二婶心情很好,据说,跟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黄连也能吃出甜味来。
陈先生受不了了,当即把粮票退回,回信只有八个大字:“诲尔谆谆,听尔渺渺。”信纸上有些水痕,不知是不是泪水。从此断绝交流。
小时候二伯和我说话,说着说着偶尔会望着眼前的空气发呆,眼里放出光来,蓝幽幽的。长大后我明白了,原来“心如死灰”的“灰”不是灰色的,是蓝色的,蓝幽幽的,像我夜里走山道时跟在身后的磷火,不声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