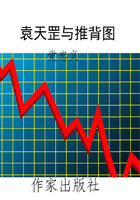当时经过几场大变故,烟霞的人心已有所松动,“大眼”家人下过狠手后也觉得不该把事做绝,于是叫人传过话来:“‘大眼’说了,如果肯正式娶她为媳妇,她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不想我奶奶站了出来:“不行!祖宗的家法不可废!一个不贞的女子,怎么能进我方家的门!”
“大眼”接到回话,当晚就把自己也挂到了屋梁上,和大伯不同的是,大伯吊的是手腕,她是自己水葱一样嫩的脖子。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传统文化!我奶奶一句自以为正面的话就毁了一对活生生的年青人!花儿刚刚要开放!所以我看到人家架着一副端正的嘴脸大谈弘扬传统文化和宗法制度时总是手痒,忍不住要从王朔的挎包里摸出板砖迎面拍去!
事情闹大了,赔钱了,报官了,大伯被关进了监狱。不久,抗日战争开始了,小日本的飞机时不时飞到县城的上空,边绕圈边拉下炸弹来。于是,大伯和大批罪犯一起被押解到龙岩继续坐牢,直到日本兵拖着膏药旗逃回日本。
出狱后,他到县城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干果店。因为他的经历比较复杂,不知不觉,县城的名厨师们都围到了他的身边,由他做东,天天变着花样煮东西下酒,瞎聊。这一吃,把他吃成了个苏东坡,嘴刁,会吃也会做。后来到了八十年代,天气转暖,他把自己吃的经验发挥了出来,每日做上几样早菜出售,因为品味极佳,所以供不应求。虽然他只取蝇头小利,但足以帮助一家人的生活。他甚至为下一代盖起了三间新房,在人生的最后几年,终于真正成了家庭的支柱。当然,这都是后话。
当年他把自己吃成了苏东坡,往事也渐渐在心中淡了色彩,于是也想到了祖宗的教训,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坐过牢,在云霄找一门好亲事是不现实的了,所以家里花钱到隔壁县买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这就是我的大婶。这年是1947,北方战事大起。
大婶姓李,叫梧桐,长得很漂亮,一张脸像十五的月亮。大婶家里很穷,穷人家的女儿只不过是父母眼里的财物,可以用来改善生活。她们家门前有棵梧桐树,每年初夏都会满树红花开放得恍如神话世界。只是没有凤凰来栖,传说中的凤凰都跟和尚一样,不交穷朋友的。
大婶嫁给大伯,也算是跳出了穷门,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一年多后,她生下了我大堂哥。大堂哥眉清眼秀,因此虽然家计渐渐困难,全家上上下下还是心生欢喜。大堂哥出生不久,解放了,换了山河。
二婶也姓李,巧合的是,她的名字竟然叫凤凰。她是广东潮州揭阳人,1943年,为躲避日本军队跟着母亲逃到了云霄,被我姑婆收养。那年她12岁。姑婆说,现在是女儿,长大了也许是媳妇。姑婆终身未嫁,二伯打小就过继给了姑婆。
因为门框上挂着“光荣烈属”,而且仇人遭了报应,所以刚解放那段时间,全家人都觉得阳光颇温暖,甚至把出走多年在海边当庙祝兼乡医的我爷爷接回了家。
可是,贫穷像一只秃鹫,翅膀宽大,拖出的影子终于严严实实地覆盖住了我们的家。1950年年底,土改,改得很彻底,只留下了两间卧房和一间厨房。姑婆、二婶一间,大伯、大婶一家人一间,二伯和我爸爸如果不睡在灶口就得睡在锅台上。二伯当时在县贸易局当干部,赶紧去找农会干部理论。农会干部不识字,不喜欢讲道理,非常厌恶读书人,于是话语间发生了磕碰。农会干部手里有枪,正想抓典型竖立威信,立刻上报,以破坏土改罪逮捕入狱。关押半年多后,群众大会讨论通过,无罪释放,交由群众管制劳动。
本来我家经过几场浩劫财产已经消耗殆尽,只剩几间自住的房子,不想这年二十八亩的方家公田恰好轮到了我们家。田地当然被没收,帽子也扣了下来,地主,没有有关领导同意,不得随意走动。农会干部顺便把“光荣烈属”的牌子扛走了。没有了“光荣烈属”,院子里的阴影果然浓重了许多,每条砖缝都渗出寒意来。家里人都劝二婶回潮州去,她母亲也希望她回家,回家就不是地主了。可二婶说,不,我愿意当地主崽。她说,姑婆有恩于她,她要照顾我姑婆。那年她十九岁了,喜欢自己拿主意。她喜欢我二伯。
大婶入我家正好不足三年,就差了几天,所以光荣地成为了我们这个地主家庭中惟一的贫下中农,不用低着头在村里来去,能分到和别的贫下中农一样多的口粮。
这一件事充分证明了土改干部们工作态度的极端认真严谨。长大后我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发现**德国的官员们也是如此的认真严谨刻板,他们没有脑子没有良心从不思考,他们像机器一般顺从上级,他们麻木、不负责任,不由得默然良久。
万幸的是1952年恢复高考,二伯赶紧去考。他说,云霄的天太黑了,我要跑得远远的,我不信天下的乌鸦都是黑的,我就不信找不到睡觉的地方。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抗战期间蒋介石当过校长的国立中央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虽然改名南京大学,但庙还在,和尚也还是那些和尚,磁性依然不减。因此秋天一到二伯就赶忙收拾行李到南大中文系报到了。在南大,他碰到了金陵四大才子之一陈中凡先生,陈中凡是陈独秀的得意门生,陈先生把他当成了宝贝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