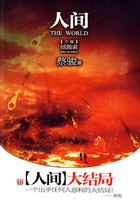我和阿克最后一次来这儿,应该是六月份的事儿,那时候我手里的楼盘刚刚折腾出去,狠狠赚了一大笔,阿克说要来庆祝一下。那次打了个通夜,三倍的价钱。不过,谁手里正好有那么一大笔钱,谁都不在乎,我手底下那几个售楼小姐都说拿钱拿得手都软掉。当时我还怂恿阿克从她们中捞一个得了,免得有状态了还得往外跑。
不骗人,阿克是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这几个字很吓人,比完美主义还要吓人,完美无非是让自己挑不出毛病,理想这件事就很难,因为理想经常变,比如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做个画家,再后来想当歌星,上大学时就想当作家,现在,是想当个亿万富翁,也许,在别人看来,对我来说傍个有钱人来得划算,但是,这不是我的理想,所以,尽管有很多机会,但我迟迟不肯出手。不过,我这种理想还不能称为理想主义,与阿克的不同。阿克谈过无数个女朋友,在他看来各有各的好处,她们每一个身上都有让他迷恋的地方,但是,谈来谈去,他都跑掉了,在他看来,她们都不够好,接触常了,发现有的性格不合他胃口,有的庸俗,有的自命清高,有的头发开叉,有的不爱干净,有的不知道斯皮尔伯格,还有的竟然问他袭人姓什么,还有的告诉他相对论的发明人是富兰克林,这都让他难以接受。有个他认为比较理想的,阿克连求婚戒指都准备好了,竟然后来发现有颗假牙。这是在她高潮时头从床边耷下去大张开嘴被阿克发现的,当即就疲掉了。不过,我从他的发现中得了好处,他把那个戒指送给我了,我劝他留着以后用,应该用得着。他说算了,免得一看见就想起那颗假牙。既然这样,我就算帮他吧。
现在,这个戒指就戴在我的无名指上,在我睡着时阿克发现它在闪闪发光。
上次是我买单,也就是说,这次轮到阿克了,所以,这一觉我睡得特别甜。榨干别人口袋一直是我的最高理想,只是,美国两房都等着奥巴马救命了,我更没有好办法,只好天天泡澡。稍有积蓄,还不太惧荒年。就榨口袋这回事,阿克比我强,上次他点了两个单,为掏我口袋,甘愿搭上小命。之后还倍儿精神,说他现在很自信,能到这里当个小弟了。阿克说这话的时候那个自称Mark的年轻人正搂着我的腰。阿克说完朝他看了看问,怎么样,我这姊妹味道还不错吧?
我给他叫阿克,他私下管我叫法拉我,当着别人的面就称我为我姊妹或我姊妹,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我猜他也喜欢我给他取的名字,那是攻无不克的缩写,因为有次他向我吹牛,说三层茧子的东北大娘他都搞得定。其态之下流卑鄙,其语之畏琐淫荡,凡一切开化之人皆为此掩面不及。
我们这个城市,近年来东北人、四川人、湖南人、云南人,几乎全国各地的人都往这儿蹿,等土著们明白过来钱都让别人掏去后行动起来,爱花钱的人也变得贼精了,个个感叹钱不好赚。赚钱很难,花钱却容易得很,阿克说钱都让Kapa这种老板赚跑了。
算起来,我认识阿克,可能有三十多年了,因为据我母亲说,阿克小时候最爱干的事情就是给我倒土裤。说我们发小,又很娇情,因为我刚上小学,阿克已经上初中了,但走的路线一样,他上的初中我也去了,他后来到市一中上高中我也紧接跟上了,后来他到石油大学学财务我也跟上了,连老师都没换几个。毕业后阿克到证券所,我到房开公司售楼。住处相距不到五百米。因为这个,阿克就完全有资格在我面前充大:你屁股上的青胎记没去几天,就敢跟我拉架势?或者:你姓侯的侯会写了么,保不定又添上竖了,嘿嘿!要不,见了街边的花就大喊:法拉我!法拉我(我曾经将flower念成法拉我)!最要命的是他用这个来表示恐慌:啊!哥,我屁股流血啦!呜呜。
我曾怀疑过阿克有玻璃倾向。我们工余经常坐在青岛路西段的某一处路崖石上看人,我是看美女,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很让我嫉妒,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帅哥,那时候青岛路那个证券交易所还没搬迁,阿克有个同事经常进进出出,在我们脸前晃晃悠悠,现在他具体的样子要不翻阿克的相册只记得他留了下稍长的头发,很高很瘦。他经常一出门就被我盯上,然后我看着他一直沿青岛路北侧向东走,走过与五台山路交叉口闪进人流我才拿回眼来。阿克几乎从未说起这个人来。所以,除了他样子让我着迷,我对他一无无知。除了他,可阿克一一评判在我们面前走过的像样子的男人,优缺点面面俱到,当然,只是阿克想像中的。有次我说他男人有什么好看的,得瞧那些姑娘。那时候青岛路这个路段几乎能看到品种最齐全的时尚女郎,这些人下午在美容院和时装店间闲逛,一擦黑猫进附近几个大酒店等待客人挑逃,那时候她们的日子对我来说相当神秘。阿克看了看我,一脸茫然地说:姑娘有什么好说的。由此我断定,他有玻璃倾向。所以,当我越来越大直到足解风情之后还是感觉阿克非常安全。后来有一阵这种感觉有波动,因为阿克恋爱了。阿克带着那个卷头发姑娘到我办公室,说要请我吃饭。不几天后见了我神秘兮兮地说,知道嘛,哥是男人了!我说你本来就是,虽然有点问题。他一边蹬开自行车后撑腿一边泄气地说:小屁孩,我就知道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走啦!
有段时间,我很有问问阿克他那个男同事的冲动,因为我断定他算得上我的初恋。后来没问是因为我严肃地想了想,又感觉不是。当然,是不是初恋都可以来一腿,关键环节我突然觉得在阿克同事里挑一个,有损我的尊严。我得找一个他不认识的。所以这件事儿,没见影就先黄了。
我身上有很多特质,最明显最强悍的就是对金钱的渴望。刚开始我想,我得好好干,争取三个月内,给自己买辆赛车,一定得阿米尼的。那时候房开公司还是建委下属的实体,一年开不了几处盘,还都是商业用房。提成也少。不过,我的愿望还是很快就实现了,实现了才发现,不如原来想像的好。后来我又想,我得好好干,买下百大那套最贵的时装,后来又实现的时候想时装也就那么回事,最贵的衣服居然也有跑偏的线头。再后来我想,我要买个房子,奋斗了好几年,产权也放开了,自由买卖了。拿钥匙捅开门往客厅里一站,早先想酝酿的兴奋荡然无存。这真让人泄气。我说给阿克,那时候阿克正走马灯似的换女朋友。阿克说:啐,这种事儿就跟泡妹儿一样,战线一拉长,什么神秘啊激情啊都扯蛋,啥都不新鲜了。这是我第一次听阿克用新鲜两个字。后来他就频繁使用了。说我这个不新鲜,那个不新鲜,后来他一次大叫“法拉我”时,我也说,啐,早不新鲜了。他怔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