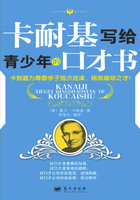要不,还是Kapa吧。
阿克说。
阿克打电话的时候大概有七八点钟,晚上,我在浴缸里。本来没怎么想出去,但阿克叫了,不好让他打单,再说我也很久没去Kapa了,有两周我了吧。
阿克是我的朋友,很亲密的朋友。我说他是我亲密的朋友的时候经常有人会问,亲密到什么程度,我只好说无可奉告。这倒不是我有意要保留什么,而是有些细节,我懒得说,真的,工作已经很辛苦,留些力气干别的吧。我无意知道别人些什么,我自己的,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无所谓。再过几十年,我们都要在地球上消失,没有什么是非知道不可的,同样,也没有什么值得保留。我的意思是,我和阿克,是很亲密的朋友。
阿克会开车来接我,这样,他就得先往床头柜那儿靠一下,放下听筒,还得翻过身仰躺在床上伸一下懒腰,然后再蜷起来眯上会儿,期间会伸出一只手,满床上找底裤或睡衣,当然,这些东西通常不在床上,它们有时候在浴室,有时候在卧室地板上,当然,有时候在客厅或走廊,总之,除了它们该在的床,将出现在阿克家里一切能出现的地方。阿克也知道这个,但是,总要找摸一番,这是他的习惯。等他进行完这个,会起来到厨房倒杯水,也许这杯水要现烧,所以,在这期间,他还得回到床上呆一会儿。等他喝完水,还要洗漱,要出门嘛,总要打扮一下,阿克很注意自己形象。另外,他还得费大约五分钟找车钥匙,一般它在厨房里。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吹头发、化个淡妆、画指甲,全身涂上柔肤蜜,还要在肘部膝部后臀部先来一点爽肤水。等我一切收拾停当,弹到肩部一点香奈儿N号时,阿克正好可以敲到我的门。
我刚才做的那些事,阿克也了如指掌,要不,就称不上亲密。
我和阿克一起下楼,钻进车里。Kapa很近,也就二十分钟车程。当我们步入大堂,早有一个收拾得白净利落的服务生心照不宣地对我们笑笑,引领我们到包间。三楼灯光暗下来,橙色和紫色交杂的光束让人想入非非,当然,常来这儿的人,也没有什么好想的,就这么回事儿呗。一上三楼,阿克停半步和我并排,小声问我:在不在状态?阿克一边说,一边轻轻在我腰上拍几下。我笑了笑,没告诉他。等点完单,服务生出去,我挪到阿克身边告诉他,我说我在不在状态,跟你说了你也不信,我一女人,又没法验证。阿克往后一闪说,别蒙大了,要不我还经常想着你,你早成铁板老姑娘了。知道吗?阿克板起上身说,就这样,哎呀,也就我呀,你看你还像个女人嘛你?人哪,阿克仰靠在沙发背上感慨地说,生活中,不能缺了情色。真的,我试过。情色!懂吗?这个很重要。我不说再活多少年就消失之类的话,咱们犯不着自己别扭自己,是不是?你看,你都三十多啦,我也眼看就挂四。没几个好年头喽。我说你甭说的跟真的似的,照你,什么时候啊那是?我们上次来,你照那劲头,老还早呢,杨老八十多还能生儿子呢,你还早,想就想吧,甭整真理,我最听不得这个。阿克打开大灯,说闷死了,节目没开始呢就这么省电。我告诉阿克刚洗了澡,很乏。阿克说,要不,咱先眯会儿。
零七年底,我和阿克在Kapa包间内,我有些乏。我把脚搭上沙发扶手,头枕着阿克的腿眯了一会儿。那时候外面已经灯火通明,这个以盛产石油闻名的城市,天一黑,猫了一天的人们马上睁开眼从床上跳起来,走进黑蒙蒙的夜色,活力四射,配合着早早亮起的霓虹灯,各自打捞属于自己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