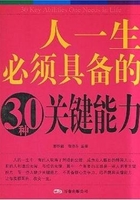不知不觉,我在稻镇住了九个月了。
来稻镇之前,王颂跟我打赌说我过不了三个月就想回来了。
我问他赌什么?
他问,“你想赌什么?”
我想起他桌上的水晶球,“我不跟你赌,你肯定输。”
王颂大笑道,“就赌我桌上的水晶球。赌不赌?”
我说,“赌就赌!”
我来稻镇,就是王颂开车送我的。他有一辆跑车,最快能开二百七十九码。不过他从没开到二百七十九码过,“现在哪条路给你开二百七十九码?”
这是很让人郁闷的事:路很好,很宽,很多,就是不让你开快。
王颂的跑车只能窝囊地藏起一半动力在路上小跑着。王颂也无所谓,谁能说这不是一辆跑车?
来稻镇的路上我听了一路约翰列侬的摇滚,是他遇枪击前灌制的最后一张碟片。绝版。我很怕王颂开车听列侬,列侬的摇滚我这样不爱动的人听了都要摇起来。
我们摇摇晃晃就像春天出去旅行,晃着到了稻镇。我下了车,把背包拿下来,王颂从车窗里递给我一样东西,“喏,拿去。”
我一看,不是他的水晶球吗?问他,“你真给我了?”
他说,“什么时候想回来了给我打电话。”
我认识王颂很久了,十年?十一年?先是我爱上了他,等我决定算了的时候他又爱上了我,就这样扯来扯去地过了很多年。再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要是早几年,听了他的话我还会感动一下,现在我只能承认我心里装满了东西,这些东西阻碍了我向外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以致,使我经常看上去显得麻木不仁。
我在稻镇过得并不寂寞。我养过一只小猫小白点。我在一只垃圾筒旁边看见它的时候它还不到一个月,还是个猫孩子。它的妈妈在旁边看着我抱走了它,朝我咪咪地叫了两声。我知道,它是把小白点托付给我了。但是上个月小白点不见了,我不知道它跑到哪里去了,李芳的妈妈听买东西的人说,五里外的另一个镇上压死了一只猫,很像我的小白点。还有人说镇口那家饭店经常收一些狗啊猫的,我的小白点要是落到那里,多半也就没有活路了。
小白点的失踪让我伤心了好一阵。不过我在稻镇时常收到城里朋友的来信,她们在信里肆无忌惮讲着各自最新的恋情,每次开始爱一个人的时候,她们都是亢奋的,而且越来越把跟男人同宿当成吃一顿饭一样简单,我也给她们写回信,说我在稻镇很好,很喜欢稻镇的河湾边,我是个缺不得花草的女人,我在院子里搭了架子种了丝瓜,蕃茄,结交了一个叫孔凤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