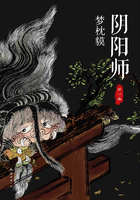我搬到稻镇九个月了,只去过孔凤兰家。
孔凤兰住在稻镇最中心的老街上,她丈夫做生意,一年只有两三个月在家,儿子在南京读书。孔凤兰家是幢两进深的宅子,门楣上写着断齑划粥。孔凤兰在县里上班,每天早出晚归,空余喜欢写写稻镇人物风土的散文。我去河湾边散步常碰到她,她看上去很高傲,肩上搭着淡灰的缕空披肩,稻镇只有孔凤兰披这种披肩,认识她的人很多,她往河湾边走不断有人招呼她,她笑一笑也不说话就走过去了。那时我刚搬到稻镇。
我到了稻镇才知道稻镇的治安不怎么好,天刚一黑,家家户户就关门闭户了。我问隔壁的寿荣,寿荣当当地敲了几十下白铁皮才爱理不理瞟我一眼道:“这有什么不好懂的?穷人家再穷,还有一条命呢。”
那是前年的事了:一个外地人借讨水喝白天闯到一户人家家里,把五十几岁的祖母和三岁的孙子杀死了。那个外地人早枪毙了,可祖孙两人的血腥气仍在稻镇的屋檐之间飘荡着。
我说我不算外地人,我外婆就是稻镇人。我跟着妈妈还来稻镇住过一夜。
“现在这个世界,还是小心点好。”寿荣说罢这句再不理睬我了。我赞他白铁打得好也没用,蜜糖和刀一样是用来杀人的。
让别人相信自己是很难的,河湾边的鸡笼山夜景很好,我也不敢上去看,天刚有些灰蒙蒙的,就往家里走了。
大约有半年我没见到过孔凤兰,说是去北京了。李芳告诉我的。李芳还在读书,她是李家兜人,很小爸爸就死了,现在的爸爸是继父。李芳的妈妈嫁到稻镇,在家里开小店,李芳放了学也要在店里照料生意。稻镇水多,蚊子也多,我买过蚊香片,一次性打火机,还有八宝粥。李芳的妈妈叫李芳多跟我学学,我问李芳以后想做什么,李芳说她没有想过。我看见柜台后面的小桌上放着几张画,李芳笑着把画拿开了,说她画着玩的。
李芳告诉我的时候孔凤兰去了四个月了。又过了两个月,她回来了,穿了条金黄的下摆很长的裙子,离我还有十来步远,满面春风地笑着招呼我说:“散步去?”
我惊讶了一下才笑着点了点头,问她,“你回来了?”
她比去之前瘦了点,晒黑了不少。我端详着她,发现她的脸还有种明显的变化,一下子却又说不上来。
我们很自然的并肩上了桥,又下了桥,往河湾边的茅草亭那儿走。孔凤兰没谈起北京,她谈的是稻镇往西六十里的琼山,琼山顶上的五梅观,五梅观的一棵大银杏树。
我们还谈到了紫薇。道观门口都有一棵紫薇,那是道家取的紫气东来的意思。我们还说紫薇怕痒,也叫痒痒树。回到大路上,我看着天黑了,想到必须穿过的弄堂,不安起来。
孔凤兰发现我在走神,问我,“怎么?你走夜路怕?”
我想说不是怕,是警惕。再一想,为什么警惕?还是怕。我问孔凤兰怕不怕,这里杀过两个人,这里的人家黄昏时分齐刷刷地关门关窗,像给子弹上膛。孔凤兰说有什么可怕,她不怕,问我想不想上鸡笼山看看。“真的?”我说,兴奋起来。
我们一块上了山。这山原是一个诸候王的墓葬封土,这一带都是平原,这封土也算一座山了,山顶有一小块空地,能望见绕镇而过的丁字形的河流,河边的树丛已经隐入了黑暗。我向天上望,青天皓月,没半点云翳。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孔凤兰。我们第一次聊就聊得很好。
从鸡笼山下来,孔凤兰问我要不要送,我坚决不要。除了我的脚步声,路上很安静,我必须要穿过的弄堂只开了两扇门,相隔二三十米,是两户人家的后门,从前供仆妇佣人走的,现在没人走了,不单上了锁,还用铁丝绞死了。
出了这阴森的弄堂我就到家了。我锁了院门,房门也锁了,坐在台灯桔黄的光圈里,心才定了,拿起桌上的水晶球,在手里转着,想着孔凤兰脸上明显的变化是什么。水晶球在灯光下晶莹剔透,我向着它的深处窥去。这种水晶球据说能预测运势变化,很多做生意的人喜欢在桌上放一个。我不做生意,拿它当镇纸用,还有就是迷茫的时候,我非常希望有个高过我的人告诉我不懂的事,——我经常这样想。我转着水晶球,突然发觉孔凤兰变得平和了。是的,她平和了。她不高傲了。
入了秋,她依旧搭着那块淡灰的缕空披肩,她的脸白了一些,不过再没有以前目空一切的神情了。她邀我去她家。我由此进了那幢灰色的写着断齑划粥的宅子。院子里种着桂花,香樟。客厅窗上挂着淡蓝色的窗帘,茶几上放着一块墨绿的石头,在灯下暗暗放着金光。孔凤兰说这不是块普通的石头,是她从崂山带回来的海底玉。接下去,她又跟我谈起五梅观里的树,从第一眼看见说到夜半时分又一次站到那棵树下,那棵树那时被月光照得斑驳发白。“道观里只有一个女道士,姓冷,大家就叫她冷师傅,在山上八年了。八年,整座山上只有她一个人。”
我似信非信。现在还有诚心修道的人吗?我去过庙里,看见过眼珠子乱转的和尚。我希望这个冷师傅年纪轻一点,老本身代表着一些东西死了,要它在一个年轻的心里死了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