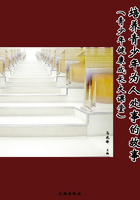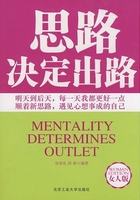墨家本是先秦时期的显学,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学派不但传承中断,而且学说也遭禁止。从西汉中期开始,一直到明清之际,将近1700年间,墨学再也没有复兴过。清初,傅山曾给《墨子·大取》篇作注,从而开启了清人治墨的先河。乾嘉年间,毕沅和汪中在诸子学兴起的背景下,又对《墨子》全书进行校勘,进一步引发了清人整理墨书的兴趣。鸦片战争以后,在西学的刺激下,《墨子》书中因包含光学、力学、几何学等内容而受到知识界更加广泛的注意,许多人都希望能在墨学中找到救国之路。辛亥革命以后,儒学独尊既成陈迹,墨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热潮,墨家这一沉埋千古的学说又一次扮演了反传统的角色。“墨学热”成为近代思想史中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一、乾嘉时期
严格地讲,乾嘉时期并不属于近代的范畴,当时对《墨子》书的整理也还不足以称之为“墨学的复兴”。汉学家们之所以花费气力校注《墨子》一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援墨注儒”、“以子证经”的需要。不过,也多亏了汉学家们的这种细致的校注工作,后来墨学的真正复兴才得以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1.诸子学的兴起
清代的学术风尚是考据学,《墨子》书的校勘、整理正是这种学术风尚的产物。从外在机缘讲,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是清朝统治者高压的结果,这使得学者们根本不敢涉入与政治相关的敏感问题,更不敢有什么经世之想,只好埋首于书斋,从事没有风险的学术考证工作。从思想的内在理路来说,汉学的兴起亦是对明代心学空疏学风的反动,也就是说学者们已经厌倦了空洞的心性之论,而希望走上一条向实求真的路子。清初的几位大儒已经预示了这种学风的转变,顾炎武首先提出“经学即理学”的主张,称“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黄宗羲也一改心学不读书的惯例,认为“学者必先穷经”、“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方以智的“藏理学于经学”和顾炎武的说法如出一辙。另外,顾炎武的《日知录》更为这种主张提供了典范性的著作,所以后来的汉学家们多沿袭顾氏的路子、尊顾氏为始祖也就不奇怪了。只不过,在顾炎武那里,“通经”的目的在于“致用”,学术的背后还怀抱着某种政治的目的,而到了后来的汉学家如乾嘉学派那里,这种致用的目的早已消亡殆尽,剩下的也就只是为考据而考据、为学术而学术了。
但是,考据也有自己的限制:考据的目的在于求真,求真就必须充分占有资料,可儒家的几部主要经书都是上古文献的遗存,内容既不连贯,错、讹、衍、脱之处亦所在多有,因此要想求得它们的真实面貌,除了对其内容进行细致的研究之外,还需要撇开学派的成见,深入到当时或稍后的诸子百家著作之中,寻求有用的资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乾嘉时期“诸子学”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汉学家们于治经之余,对各种子书多所涉猎。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详细罗列了清儒校治子学的总成绩,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诸子学”兴盛之一斑。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一开始子书主要是用来证经的,但到后来,各种子书也就差不多成为一种独立的专门之学了。
在这种背景之下,《墨子》一书也开始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汪中、毕沅、卢文弨、孙星衍、张惠言、王念孙等这些清代一流的学者均曾从事过《墨子》的校订或注解工作。在详细介绍他们的成绩之前,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另一个人的工作,正是这个人首先开启了清人治墨的先河——他就是清初著名的大儒傅山。
傅山是清初从实学的角度批判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清儒中率先开创子学研究的先行者。和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相比,傅山的特点是对中国传统的名辩学说有独到的体会。逻辑史家汪奠基曾这样评述道:“他(傅山)的子学思想,是唐代以来最能表现因明识相诸宗的影响和运用这些影响来发挥祖国名辩学说义蕴的一人。傅山能掌握这方面的认识,所以真能揭穿宋儒如何囫囵道佛以入理学的形而上学方法。”傅山用因明来解释中国传统名辩之学的作品主要便是《墨子大取篇释》和《公孙龙子坚白论释》。
《大取》是墨辩六篇中最难读的一篇,因为讹脱太甚,文义已不连贯,许多内容已无法索解。傅山选取《大取》篇作注,可算是给自己找到了一种理智和能力的挑战。他的注解多依文为训,尽量避免牵强附会之辞。如对《大取》中的“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惟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一段话,傅山的解释是:
故物之以形貌命者,必知是物为某物,则尽其辞而名之曰“焉智某”也。若其不可以形貌命者,知之不真,不能确知是物为某物也,但智某之可也,不得尽其辞曰“焉智某”也。此焉如汉碑焉焉矣。终辞也,决辞也。又“智某”与上“是之某”也义有深浅,上文多一之字,下文去之字,上文是实指之词,下文是想象之词。
在《大取》篇中,“以形貌命者”指的是具体概念,根据事物形态和面貌而命名;“不可以形貌命者”指的是抽象概念,不能够指出其具体对象或形态是什么。傅山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两种概念间的区别,他把两者分别称之为“实指之词”和“想象之词”。“实指之词”知之真,能够根据形状确知是某物。“想象之词”知之不真,不能根据形状确知是某物,但这并不妨碍其为知,只不过和“实指之词”相比,义有深浅而已。傅山还发现,《大取》篇解释“以形貌命者”所用的“焉”字是一个“终辞”、“决辞”,表达的是一种断定。这和后来墨学家们以“乃”释“焉”完全一致。
又如,对《大取》篇中“有其异也,为其同也,为其同也异”一段话,傅山解释说:“因有异也,而欲同之,其为同之也,又不能浑同,而各有其私同者又异。《楞严》因彼所异,因异立同之语,可互明此指。”这是用《楞严经》来解释《大取》的例子。《大取》中该段话的意思是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异之间是一种相互包含和相互渗透的关系。而《楞严经》“因彼所异,因异立同”,讲的同样是同异之间互为立破的关系。傅山用《楞严经》来解释《大取》,可以说基本上把握住了后期墨家同异观的内容。
傅山对《大取》篇的解释多与此类似。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就不再一一详举了。其实,从墨学史的角度看,傅山对墨学的贡献并不在于他的解释是否正确或有多大独创性,而在于他开了风气之先。由于缺乏足够的知识准备,傅山还无法理解和掌握墨辩中的逻辑学。
2.汪中与毕沅
傅山之后,对《墨子》全书进行校注和整理的是汪中和毕沅二人。汪中是乾嘉时期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出身贫寒,为人正直。做学问重视实事求是,不喜欢墨守成规。他率先对《墨子》全书进行了校订。根据其自序,汪中曾把《墨子》一书“定为内外二篇,又以其徒之所附著为杂篇,仿刘向校《晏子春秋》例,辄于篇末,述所以进退之意”;对于《墨子》书中的误字及文义昧晦处,则“以意粗为是正,阙所不知”;又“采古书之涉于墨子者,别为表微一卷”。由此推测,该书可观之处肯定不少。可惜汪氏此书不传,唯有该书的《序言》保留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述学》之内。正是从这篇序言中,我们才可以粗略地了解到汪氏的工作。至于说他究竟以什么标准定《墨子》为内外杂三篇,迄今为止仍然是一桩历史悬案。
除了校订之外,汪中大概还是清儒中第一个对墨子深表同情的人。其《墨子序》云:
儒之绌墨子者,孟氏荀氏。荀之礼论乐论,为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节葬非乐,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爱,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谓兼者,欲国家慎其封守,而无虐其邻之人民畜产也。虽昔先王,制为聘问吊恤之礼,以睦诸侯之邦交者,岂有异哉?彼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枉矣。后之君子,日习孟子之说,而未睹墨子之本书,其以耳食,无足怪也。世莫不以其诬孔子,为墨子辠。虽然,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当日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虽欲平情核实,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
在这段话中,汪中很明白地指出,儒墨两家立说的目的都是为了救衰世之敝,因此意相反而实相成。从当时的情形看,孔子和墨子地位差不多,年代亦相近,他们的不同实际上是道不同,所以不相为谋而已。因此,儒墨之争是正常的学派之争,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说墨家曾经诬蔑过孔子,那么孟子骂墨家“无父”也同样是诬蔑。从整段话的倾向来看,汪中的目的显然是想替墨家的主张辩护。他不但把孟子之批墨定为“诬”,而且公开承认儒墨相争的事实并把孔墨放在完全平等的位置来对待,这在当时真可谓石破天惊之论。唐代韩愈因为说了句“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就遭到宋儒几乎众口一词的批判,更何况在清朝文字狱最盛的乾嘉时代!汪氏秉承学术的良心,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意见,这种勇气实在让人敬佩。
其实,在当时,就已经有人开始攻击汪中为“名教之罪人”了,曾任太子洗马的翁方纲声称:
有生员汪中者,则公然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之言兼爱无父为诬墨子,此则名教之罪人,又无疑也。昔翰林蒋士铨掌教于扬州,汪中以女子之嫁往送之门是何门为问,蒋不能答,因衔之,言于学使者,欲置汪中劣等,吾尝笑蒋之不学也。今见汪中治《墨子》之言,则当时褫革其生员衣顶,固法所宜也。汪中者,昔尝与予论金石,颇该洽,犹是嗜学士也。其所撰他条尚无甚大舛戾,或今姑以此准折焉,不名之曰生员,以当褫革,第称曰“墨者汪中”,庶得其平也乎?
翁氏本为汪中的朋友,只因汪中替墨子作序,就断然称之曰“名教之罪人”、“墨者汪中”,并威胁说应当褫革其生员衣顶,这足可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孙星衍的《墨子后序》,这位翁洗马其实也是当时治墨者中的一员:“时则有仁和卢学士抱经,大兴翁洗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谋同时共为其学,皆折衷于先生(指毕沅——引者注),或此学当显?”其中的翁洗马覃谿指的正是翁方纲。这倒也并不是暗示说翁氏的道德有多么败坏,品行有什么不好,它只不过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氛围还没有为墨学提供足够的复苏条件而已。从翁氏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墨学研究尚存一种严格的限度即不能有损儒教。在这个度之内,校订也好、注释也好、批评也好,都是允许的,但若超出了这个度,如汪中一样,那就难免会沦落为“名教之罪人”,甚而有“褫革其衣顶”的危险了。
汪中的《墨子注》校本写定于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三年之后,毕沅的《墨子注》亦告竣工。和汪中相比,毕沅的做法就显得谨慎周全多了。他在《自序》中说:
非儒,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其称孔子讳及诸毁词,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称孔子,亦称仲尼,又以为孔子言亦当而不可易,是翟未尝非孔。孔子之言多见《论语》、《家语》,及他纬书传注,亦无斥墨词。
先秦之书,字少假借,后乃偏旁相益。若本书,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之溢为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镒”。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传写者乱之,非旧文。乃若贼百姓之为“杀”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亡之训,关叔之即管叔,实足以证声音文字训诂之学,好古者幸存其旧云。
称孔子无斥墨词,实为失考,墨学后起,与孔子不相值,孔子当然不会有斥墨之词。但毕氏此论,用心却很良苦。把儒墨的对立化为弟子后学所为,这自然就替墨子洗刷掉了非儒的罪名。再说,《墨子》书中的古音古字“足以证声音文字训诂之学”,这同样有益于儒家经典的考校。从这两方面考虑,为《墨子》一书作注也就不能算是替异端张目的行为了。
对墨子的一些思想,毕沅亦能采取同情的立场。墨子曾告诫弟子入国必择务而从事,毕沅评论道:“是亦通达经权,不可訾议。”对《备城门》以下诸篇,毕沅认为属古兵家言,有实用的价值。这些评论,较之翁方纲已有极大的进步。
由于汪氏之书不传,毕沅的《墨子注》成为乾嘉时期流传下来并影响后人的最重要的注《墨》著作。梁启超称“其功盖等于茂堂之注《说文》”虽然有点夸张,但其创始之功实不可没。后来孙诒让作《墨子间诂》,之所以用毕书作底本,原因就在于此。根据毕沅的自序:“先是仁和卢学士文弨、阳湖孙明经星衍,互校此书,略有端绪,沅始集其成”,可知卢文弨、孙星衍二人亦曾参与该书的校注,所以确切地说,该书实为三人合作的产物,这也许是它能够取得相当成绩的主要原因。
粗略地讲,毕氏的《墨子注》大致有两大贡献:(1)以声音训诂之学证古字古音。此点从上面的一段引文即可看出,它同时也是毕氏颇引以自豪之处。清儒治学从顾炎武开始本来就是从音韵入手以通文字训诂,就此而论,毕氏可谓能严守家法。(2)恢复《经上》篇旧本写法。墨书之中,《经》及《经说》四篇素号难读,鲁胜之后,更无人能解。毕氏根据《经上》篇的“读此书旁行”一语,在篇末别作新考,分该篇为上下两行横列,从而使这篇千古奇文得以初还旧观。后来的墨学家之所以能够在《墨经》四篇方面迭出新论,全赖毕氏的这一发端之功。不过,毕注也有许多缺点,如好以儒言附会、注文简略、鲜少发明等,这也许是发端之初在所难免的通病。
汪、毕诸人之外,当时及稍后治墨者还有张惠言、丁杰、许宗彦、王念孙等人。张、丁、许三人均专治《经》、《说》四篇,其中,丁、许之书不传,张氏的《墨子经说解》生前亦未尝刊布,直到1907年孙诒让始得校写本。据其书,张氏首先援用鲁胜“引说就经”之例,将《经》、《说》四篇逐条拆开,先列《经上》旁行为一篇,而后以《经说上》附《经上》为一篇,是为上卷;次列《经下》旁行为一篇,又以《经说下》附《经下》为一篇,是为下卷。两卷书使经文与说文互相对照,条分缕析,旁行之文,全复旧观,以致连孙诒让亦不得不赞叹说:“余前补定《经下》篇句读,颇自矜为创获,不意张先生已先我得之;其善谈名理,虽校雠未寀,不无望文生义之失;然顾有精论,足补余书之阙误者。”不过,从其序言中可以看出,张氏亦是对墨家抱有甚深成见的人,他把墨学之亡归于圣贤之功,他称孟子的“无父”、“禽兽”之骂为诛心之论并告诫后之读墨书者“览其义,则于孟子之道,犹引弦以知矩乎”。所有这些,和汪中相比,其识见就未免不可以道里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