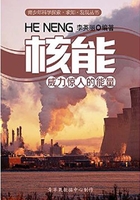个人觉得,这恐怕不仅仅是一种论证的策略,以便让汉学家们更容易接受。同样也不太像是思想混乱的结果,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玄妙的问题。最大的可能是,陈澧并没有真正从考证学传统中走出来,长期的汉学训练使他对宋儒的“义理”抱有一种习惯性的反感,这从他把“排陆王”作为《学思录》大旨之一即可看出。下节我们将会论证陈澧对“义理”的了解并没有超出考证学的传统,这是他整个主张呈现混乱色彩的症结所在。
陈澧贯彻“汉宋调和”论的第三种方式与第二种方式大同小异,只不过这次把讨论的范围缩小到了郑玄和朱熹两人。《读书记》单列两卷讨论两人的学说,可见陈澧对二人的重视程度。郑玄是汉学宗师,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以这两人作为汉、宋的代表,自然没有什么不合适。事实上,在陈氏之前,清代汉学家也有人倡导并尊郑、朱,例如吴派的惠栋就有“六经宗服郑,百行法程朱”的说法,皖派的江永也曾替朱子的《近思录》作过集注。这些人并尊郑、朱的理由虽不完全一样,但大体上都属于同一种类型,那就是既肯定郑玄在汉学上的成就,也承认朱熹在理学上的贡献。陈澧则不然,他在这两卷书中,试图说明的仍然是那个“汉儒精义理、宋学能考据”的中心论点。结果我们发现,郑玄论学的大旨,不在于“小小才艺”之事,而在于“圣人之道”,程朱义理之学早已发端于汉儒;朱熹除了知道居敬穷理之外,还重训诂、重注疏、重音读、知算学、明地理,即便与汉儒比,也不遑多让。
就朱熹而言,陈澧的解释并不算错,只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在理学家中,朱熹可能是最重视章句训诂之学的人,他一生孜孜不倦注经、解经,都是想把义理建立在可靠的文献基础之上。但理学就是理学,经解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义理的最终获得必须建立在自得的基础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熹说:“读书乃学者第二事”、“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陈澧显然无法理解这一点,当他辩驳说“第一事(穷理)必在乎第二事”、“第一义必在乎第二义”时,汉学和宋学的区别立刻暴露无遗。
和有关朱熹的解释相比,陈澧对郑玄的“发明”倒显得更有说服力一些。虽然把“圣人之道”作为郑学之宗旨并不足以说明郑学之特色(因为汉、宋的区别本不在目的,而在于方法),虽然凭有限的几句话并不足以证明郑学真的“说心性最精”,但陈澧毕竟对汉学更有体会,当他把郑氏家法概括为“有宗主,亦有不同”,并与何休之“墨守”、许慎之“异义”相互对照时,确能彰显汉儒各家之特色。从陈澧本人反对墨守和异义、特别推崇郑氏家法来看,“有宗主、有不同”似乎也是形成他的“汉宋调和”论的一个助缘。
总之,出于对汉学之弊的反省,陈澧提出了“汉宋调和”的主张。从多方面的材料看,陈澧曾经尝试把这种主张的宗旨表述为:汉、宋皆有其独特的价值。可是,他所提供的证据却是汉学和宋学互相兼有对方之长。正是这些证据本身的脆弱,使得陈澧难以自圆其说,并深受后来者的诟病。陈澧之所以陷入此种窘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仍然身处考据的传统之内,对“义理”之学并没有形成一个恰当的认识。
四、“义理”之所以为“义理”
“义理”与“考据”的关系是清代学术的一个中心问题。尽管可以把该问题的源头一直追溯到宋代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但这两对概念却是不能随便置换的。宋代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属于“义理之学”内部的事儿,双方的分歧最多只是程度的差别而已。号称最重“道问学”的朱熹仍然把读书看成“第二事”,就足以说明问题。清代则不同,“义理”与“考据”被当作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学问来对待,“义理”属于思想性的内容,“考据”则是对名物数度的训释。
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最极端的看法是:“义理”皆空谈,“考据”才是实学,因此不必耗精费神于“义理”。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对明代心学极端厌恶,并且乐意置程朱理学于不闻不问之列。第二种意见是:“义理”必须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训诂明而后义理可明”。这是最流行、影响也最大的一种说法,戴东原曾给予经典的表述,钱大昕等积极附和,焦循、阮元并且热心地去效法和实践。钱大昕对“义理”没什么兴趣,故只愿从事考证的工作;焦、阮则有“义理”的偏好,他们都试图通过训诂的方法解决经典中的义理问题。最后一种意见是:“义理”是一种自得之学,不必建立在“考据”之上。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是宋学家,考证学派中几乎找不到一个代表。晚年的戴震曾经提出“义理即考核、文章之源”、“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向这种观点的让步。
陈澧在反省汉学之弊时,曾意识到考证学把精力专注于文字名物的训释是舍本逐末,因此他批评汉学家不知道经典中还有许多不必训释的内容。这种说法与第二种意见相比已有松动,主要表现在:第一,至少承认经典中有些“义理”可以不必借“训诂”而明。第二,把“义理”放在了比“训诂”更重要的地位。但是,仅此而已,在基本精神上,陈澧的说法与第二种意见没有任何实质的区别,那就是:“义理”全部保存在经典中,任何试图超越经典文本来寻求义理的做法都是不能接受的,通常所说的“自得”只不过是师心自用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在《遗稿》中,陈澧曾这样表白自己:
余不讲理学,但欲读经而求其义理;不讲文章,但欲读经而咀其英华;不讲经济,但欲读经而知其所法戒耳。
陈澧的意思并不是说自己不愿意讲理学,而是说不必要、也不能够超出经书去讲理学。“义理”全在经书中,只要认真去读经,义理自然可以到手。他借陆清献的话批评象山、阳明说:
然《大学》条目,亦何尝不可借?如象山、阳明辈,皆是借《大学》条目,作自己宗旨。
象山、阳明之所以被批评,就是因为他们借经书讲自家宗旨。和大多数考证学者一样,陈澧相信这是导致明学“空疏”的根本原因,所以,他时时提醒说:
本朝诸儒考据训诂之学,断不可轻。若轻议之,恐后来从而废弃之,则成明儒之荒陋矣。
陈澧特别欣赏朱熹对“自得”的另一番解释:
大概读书,且因先儒之说,通其文义而玩味之,使之浃洽于心,自见意味可也。……且谓之自得,则是自然而得,岂可强求也哉!今人多是认作独自之自,故不安于他人之说,而必己出耳。
按照这种解释,“自得”不是自己而得,而是自然而得。“自己而得”以我为主,“自然而得”则由学习得来。从哪里学习?当然是从儒家经书中学习,于是陈澧总结说:
必读经乃谓之经学。以疏解注,以注解经,既解之而读之、思之,此经学也。不以疏解注,是读疏非读注也;不以注解经,是读注非读经也。嗟乎,天下岂易有经学哉!
为了纠正汉学之弊,陈澧曾搬出义理之学(宋学)的大旗。可是,出于对义理本身的极端不信任,陈澧又极力鼓吹读经,要求只从经书中“学习”义理。转了一个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原点。
戴东原曾经概括过考证学的大纲领:“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陈澧修订了第一句(古经的有些内容可以不借助“故训”而明),照搬了第二句。虽有小变,但宗旨无别。看看《自述》中的话,就会知道陈澧在汉宋之间、义理考据之间的抉择:
又以为国朝考据之学盛矣,犹有未备者,宜补苴之。
何为主、何为辅,这里说得实在清楚不过!至此,我们终于可以明白,陈澧强调义理只不过是为了“补苴”考据,提倡“宋学”主要是用来济“汉学”之穷。所谓“汉宋调和”,就陈澧的本来意愿来说,并不是简单的调停,而是有轻有重、有主有次的。换句话说,在陈澧那时,“汉”也许真的是“汉”,但“宋”却肯定不是真“宋”,最多也只是已经“汉”化的“宋”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年辈稍晚、但却同样出身于汉学传统的章太炎就显得比陈澧高明许多:
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若诸子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一切载籍,可以供我之用。
我们可以不必同意章氏的经、子之分,也不一定认可他对经学性质的断定,但却不能不承认他对“义理之学”的特征有精到的体会:“义理”之学属于主观之学,它一定要建立在自得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自得”(自己而得),“义理”将失去价值,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人云亦云而已。
并不是说讲“义理”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可以随意发挥。训诂考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典文本,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大部分“义理”上的分歧都不是由于“训诂”的原因而产生。即便是经典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我们都掌握了它的含义,也不能说就真的理解了该书的内容。文本没有呈现出的东西永远比呈现出来的多,这就是为什么在训诂学上并不复杂的《论语》和《孟子》有那么多种不同解释的原因所在。
陈澧当然知道儒家经典有多种解释,并且他建议人们要首先了解“先儒诸家”谁是谁非,然后再从中选择一种作为自己读经时的指导思想:
所谓经学者,非谓解先儒所不解也。先儒所解,我知其说;先儒诸家所解不同,我知其是非;先儒诸家各有是、各有非,我择一家为主而辅以诸家。此之谓经学。
问题是,凭什么来判定是非?凭什么去进行选择?“选择”、“判定是非”本身不就已经包含有读者自己的认识和体验吗?另外,先儒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解释?难道全是由于客观的理由?就拿陈澧最爱读的《孟子》来说,何谓性善,后儒聚讼纷纭,总不能说所有这些人都不善于读书吧!
由“读书”寻求“义理”是对的,但把“义理”全部看成是“读书”所得则有疑问。主张经书已经穷尽了所有的“义理”,则更成问题。当陈澧这样说时:
微言大义,必从读书考古而得。《学思录》说微言大义,恐启后来不读书不考据之弊,不可不慎。必须句句说微言大义,句句读书考据,勿使稍堕一偏也。
他实际上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至少,从后人对这部书的反应来看,他的“微言大义”常常被“读书考据”部分遮蔽掉了。批评他抄袭、摭拾,自然只是个别人的看法,但大多数人所重视的都是这部书在经学史方面的一些见解,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他的“微言大义”、他调和汉宋的苦衷,反而常常被忽视或者忘记。
重提一下章太炎也许会给我们一点启发。章氏早年同样受过严格的考证学训练,他后来之所以能够认识到“义理”之学必须“直观自得”,完全是由于佛教唯识学的影响。换句话说,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章太炎已经从汉学的传统中走了出来。陈澧却没有。陈澧仍然在汉学之内,这注定了他和大多数的汉学家一样,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义理”之学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