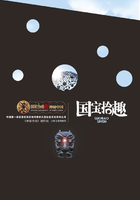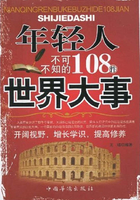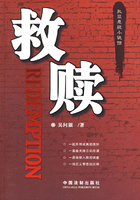《洛阳伽蓝记》序言中说洛阳:至晋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剎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垆。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稼,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这段开场白内涵丰富,情韵深厚,表明《洛阳伽蓝记》写于元魏已亡、洛阳已残破之时,作者希望借文字来缅怀追思元魏社会和佛教的兴衰。诚如范祥雍在《洛阳伽蓝记校注·序》中说是"反映一个时期,一种宗教,同时又是反映一个京师,一个王朝的历史文学"。广义上讲《洛阳伽蓝记》是怀旧文学、遗民文学。
《洛阳伽蓝记》从空间展开,以元魏鼎盛时洛阳佛寺为叙述中心、叙述焦点,因寺来叙事、写人、状物,把佛教内外之事融在一起,深情而又全面地回顾元魏的一切,展现元魏洛都的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她生动立体地再现了元魏文学景观,特别值得北朝文学研究者珍视。
有见于学界对《洛阳伽蓝记》在北朝文学史研究意义价值关注不够(似乎只有台湾学者王美秀写过一篇《论〈洛阳伽蓝记〉载存文学资料的意义》,可惜没有见到原文),故写此小文。
从文学研究视野去看《洛阳伽蓝记》,其价值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洛阳伽蓝记》自身就是北朝一部文化名著,有其自身的文学特色、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此点本文暂不论及);完整展示元魏文学的社会时代大背景;《洛阳伽蓝记》收录不少文学作品(有文人文学、民间文学);记录作家生平及其有关文学活动情况(这些文学活动涉及文学交际、创作、评论、传播等各个方面,记录了文学活动的时间、空间、场合、气氛等等,它们大多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鉴赏、文学交流、传播息息相关,是广义的文学背景史料);描绘了乐舞、绘画雕塑、杂技幻术、佛教建筑与园林艺术等与文学息息相关的姊妹艺术的情状;从接受美学看对前代诗文、文学遗迹的征引等等。
一、展示元魏文学的时代社会大背景
元魏政治社会生活大事:《洛阳伽蓝记》所记录的是元魏王朝最为昌盛、同时重大社会危机频出的特定时期,那些导致元魏急剧衰败并迅速分裂的一系列大事件发生在几十年间,必然影响到杨衒之的创作活动,全书始终流露着浓浓的"麦秀之感,黍离之悲",悲怆感怀的情韵十足,这既是全书所有文士、文学活动的无形背景,又是元魏文学的背景,这是理解北朝文学最应该重视的。
作者在正文一开始即卷一就写永宁寺,从全书来看,永宁寺可谓是元魏国寺,等级最高、寺庙建筑最完整、规范、装饰最奢华、富丽,她不光是象征佛事的隆盛,也暗示着元魏王朝的兴盛,一寺兼有佛、俗两方面象征,所以作者写得详尽,融入了自己的兴则喜、败则哀的情意。作者还巧妙安排结构,依寺写事、人、物,把发生在永宁寺的王朝大事汇聚于此,把佛事与尘俗之事融合在一起,而自己的情意感慨却深深潜藏在娓娓叙述中,这是十分高明的写法。
写佛寺最盛时: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剎,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剎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剎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铃,其十二门二十四扇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五躯,玉像二躯。作功奇巧,冠于当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琐绮疏,难得而言。栝柏松椿,扶疏簷霤,丛竹香草,布护阶墀。是以常景碑云:"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也。"
外国所献经像,皆在此寺。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阁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列钱青琐,赫奕华丽。拱门有四力士,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庄严焕炳,世所未闻。东西两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唯楼二重。北门一道,上不施屋,似乌头门。其四门外,皆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断飞尘,不由渰云之润;清风送凉,岂藉合欢之发?...... 装饰毕功,明帝与太后共登之。视宫内如掌中,临京师若家庭,以其目见宫中,禁人不听升之。
衒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物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至孝昌二年中,大风发屋拔树,剎上宝瓶,随风而落,入地丈余。复命工匠,更铸新瓶。写佛寺毁灭时: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帝登凌云台望火,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长孙稚将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泪而去。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
其年五月中,有人从东莱郡来云:"见浮图于海中,光明照耀,俨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见之。俄然雾起,浮图遂隐。"至七月中,平阳王为侍中斛斯椿所挟,奔于长安。十月而京师迁邺。诚所谓寺兴国兴,国亡寺亡。在永宁寺兴亡之间,叙述了元魏一系列重大事件:
"建义元年,太原王尔朱荣总士马于此寺。"于是有了"十二日荣军于芒山之北,河阴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驾,至者尽诛之。王公卿士及诸朝臣死者二千余人。......于时新经大兵,人物歼尽,流迸之徒,惊骇未出。......起家为公卿牧守者,不可胜数。二十日洛中草草,犹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怀异虑。贵室豪家,并宅竞窜;贫夫贱士,襁负争逃"、"逆刃加于君亲,锋镝肆于卿宰。元氏少长,殆欲无遗"。
"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颢复入洛,在此寺聚兵。"于是有了元颢引梁军赴洛夺权之事,魏庄帝逃跑流亡,结果是"所将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列。颢为社民斩其首,传送京师"。
"永安三年,逆贼尔朱兆囚庄帝于寺。"结果是"庄帝手刃荣......尔朱兆举兵向京师,......囚庄帝于寺"。后来庄帝死于非命。
这种把佛寺与世俗之事交融、兴盛与衰败结合的写法还有很多,佛寺与王朝并兴的如永明寺:"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庑连亘,一千余间,庭列修竹,簷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民间号为王子坊。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及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
借佛寺衰败写王朝之衰败的如平等寺,"寺门外有金像一躯,高二丈八尺,相好端严,常有神验,国之吉凶,先炳祥异。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两目垂泪,遍体皆湿,时人号曰佛汗。京师士女空市里往而观之。有一比丘,以净绵拭其泪,须臾之间,绵湿都尽。更换以它绵,俄然复湿。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尔朱荣入洛阳,诛戮百官,死亡涂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复汗,京邑士庶复往观之。五月,北海王入洛,庄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败,所将江淮子弟五千,尽被俘虏,无一得还。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经神验,朝野惶惧,禁人不听观之。至十二月,尔朱兆入洛阳,擒庄帝,帝崩于晋阳。
在京宫殿空虚,百日无主,唯尚书令司州牧乐平王尔朱世隆镇京师。商旅四通,盗贼不作。......其日,寺门外有石象,无故自动,低头复举,竟日乃止。帝躬来礼拜,怪其诡异。中书舍人卢景宣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还宫。七月中,帝为侍中斛斯椿所挟,奔于长安。至十月终,而京师迁邺焉"。"经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寿丘里闾,列剎相望,祗洹郁起,宝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师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廊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入其后园,见沟渎蹇产,石磴嶕峣,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咸皆唧唧,虽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同样,《魏书·释老志》亦载:"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
一座座寺庙牵连王朝的衰败、时局的动荡、人心的飘摇,这一切定然是当时人(包括文人学者、士大夫)所看到听到的,也一定会在其心里激起大的波澜。而这一切均构成元魏洛都时期乃至东西魏、北齐北周时期文学创作的大背景和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