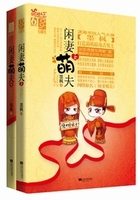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紧急的话,我情愿这时候老天赶紧的打个大炸雷下来劈死我吧,这个人太可恨了,不是女的却装作女的,不是聋哑人又装作聋哑人。
但我后知后觉地想起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女的,当初我最先叫他姑娘时,他脸上的表情应该是可以吃下我的凶狠吧,当时他为什么没杀我,是因为我露出的女相,是个好值钱的金人吧。
而且他也从来没对我说过他不会说话或是听不见这些什么的,当初我试他时,以他那么高的功夫,我的那些蹑手蹑脚,在几里外他都是能够知道的了,那里那么静。
好可笑,好可笑,我居然给她起个什么阿笑的名字,暗地里他的肠子都快笑断了吧,我还傻乎乎地给他留了一半的银两呢?简直是傻毙了,我完全的应该买块豆腐一头撞死在这里了。
羞恼过去后,心里油然而生的自然是愤怒,听得他声音清朗,却带着股迫人的寒气,我咬牙,这生意做了,我又有什么损失,反正在他的手下,我就是跑也跑不掉,飞也飞不了的了。
细算下来,救若兰的相公,简直可说是他是白救了,不答应我还真是傻了。
我点头答应,他从怀里掏了一包药扔在地上,我赶紧的抓到手上,“外敷还是内服?”立即问。
“外敷。”冷淡的回说,我原本想给若兰的,但见她手抖抖的样子,我索性挤开她,自己小心地给地上的那具男性的身躯上药,还没上得完呢,他一下子挤开我,木着一张脸说:“给我。”
怎么着他现在回想过来反悔了,我赶紧地把药藏身后,也不管是不是就此的藏得住,我说:“你想干什么?”“你这么笨手笨脚的,让开,我来帮他上。”
他会有这么的好心,一个杀人如草芥的人?
我也只有将信将疑地交出药去,他熟练地三两下就上好了药,“走吧。”
我告别汪若兰,只有随他走了,“我应该叫你什么,现在叫阿笑又不对,我不想喂来喂去的。”
我不认为他会回答我,毕竟我与他的相处,都是我说,他听,后发制人,他是最高明的实践者,看,这么多次,他都是不说话,只是酷酷的装深沉,就玩得我云里雾里的,讲手段,我还够得学。
我现在能落入这么凄惨的境地,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不够聪明,其实被捉我并不生气,这应该是迟早的事吧,但自己居然当了这么久的傻瓜,就太不能让我原谅他了。
是自已的忿怒在发酵吧,我自己也有点这样的自觉,人在恼羞成怒的时候,就象处于发作期的精神病患,看到什么都想扑上去咬一口才能泄愤似的,现在又不聪明了居然问他名字,就是告诉我又有什么用?
但他居然很给我面子的回答说:“刘义道,道义的义,道义的道。”很讲道义的黑社会杀手?我扑喇一声笑出来,他不解地看了看我。
原来那些人叫他刘一刀,是喊成了他名字的谐音吧,不过也许是恭维他杀人手法高明,只用一刀吧,我不知道我的猜测有几分触摸到了事实,不过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与他现在的关系是他显然是诓我到这里来的,然后方便交货吧,悲哀,我秦婧玉居然真的成了一件货物了,聊以**的是总算是很值钱,心思有够无聊的。
不过愤怒就不无聊了吗?同样的无聊,强权就是真理,这家伙武功这么高,我现在算是真理的小尾巴也抓不上了,乖乖地等着吧,忍气吞声地等着,看离了这家伙后,能不能找一条生路。
他的功夫太可怕了,而我的求生欲望也太强了。
从陡峭的山崖下山,真是刺激,当身边有一个武功高强到天下少有的高手的时候。以前在二十一世纪出外旅游上山下山我总是能跑到前头,毕竟练了这么年的跆拳道,要没跑到前头,那跆拳道不是白练了。
现在……
怎一个快字了得,刘义道扯我一边的手臂,拉扯着我好一阵的疾奔,我只知道身旁的一切飞速地后退,上升,居然不走山道,逢山跳山,逢崖渡崖,这人会飞吔。
最初的惊诧过后,后知后觉地感到我的手臂好一阵的痛感传来,一处高岩,他落下,“啊”,手臂猛烈地拉扯了一下,这一下仿佛要让我的手臂同自己的身体分离开去一般。
“怎么了?”他回头察看,“没什么。”我绝不呼痛,高仰着我的头,斜挑着我的眉,上翘着我的嘴角,我傲气十足,在他面前我已经闹了这么多的笑话,出了这么多的糗事后,我此刻一定得保持住自己的尊严,尽管它在他的面前应该早就支离破碎。
这是我的坚持,或许愚蠢,但坚持就是坚持,我秦婧玉就是这样的人。
下得一处较平坦地,他放开我,在我的前面微蹲下身子:“上来,我背你。”
“背我,你要背我?”我的下腭快掉下去了吧,“上不上来,随便你,不过你的手臂要是废了,我想不会有人同情你的。”他说话虽冷,但确是实情,有舒服的途径我为何不选择,我又不是傻的。
不过他又是为什么呢?是想保持货物的完好性吧。
我应该恨他的,毕竟是他将要把我送到国师的虎口中去,不过我想不出我有多少地方应该恨他,刘义道,他就象茫茫雪原上觅食的一匹野狼,咬住了一头小羊,人人都指责狼,唾骂他的凶残,但谁又能真正了解狼的孤独,狼的哀伤,狼的饥寒,羊要活命就理所当然,狼也要活命啊,有多少人替狼想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