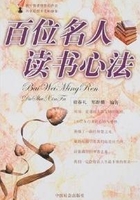经过这一翻的折腾,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街上来往的人已经很多,人们为自己的生活来来往往,谁也不知道就在先前不久,我们经历了一场血战,此刻也不知道赵擎天他们是否平安,不过以他的身手再加上我这个祸患已经离去,我想他们之间应该不会缠斗太久的。
但心里总是有些些的忐忑。
大槐国之所以叫大槐国,是因为国内的大槐树是国树,作为国家的首都,一人合抱不拢来的大槐树在街道上是随处可见,撑开一片片绿荫护住祥和的景象。
他们领我到一处距皇城极近的民宅后稍稍交代了两句就走了。
这处宅院不太,也就如老北京的四合院,四周的房屋围拢过来中间有个几十个平方的天井,天井里对角放着两口极大的石水缸,接无根水用的,里面的水可以用来预防火灾。
房子很有些旧了,屋檐上的灰砖和柱子上的黑漆都有些剥落了,而爬山虎则勃勃地爬满了院墙,带来了好一片的绿意和生机,爬山虎下有整齐的六月雪,此时正开得繁盛,星星点点的白色小点,连绵一片,当真如雪花沾染上了绿叶,很漂亮。
但我看到这个院子时,最喜欢的还是院中那一棵大大的老槐树,它撑起的绿荫覆盖住了整个小院,在这炎热的夏季带来好大一片的阴凉,在这一片阴凉中有一张石桌和几张石鼓凳。
我挑了北厢住下来了,屋子里床、椅、柜,什么的日常的家俱倒是很齐备的,都结实而实用。
这院子,王公子并没安排着人保护或监视我,这是我最满意的一点。只有一对聋哑的老夫妇,以酿酒为业,住在这院子外前面的一处小房子里,这院子的东西两边屋子里满是酒坛子酒罐子酒缸子,不过在我住进来这段时间里他们都没有来搬运过。
已经走了的那两位转告我王公子的话意,主要的就是在这里我是完全自由的,想走就可以走,想留就留下。
我与这聋哑的老夫妇之间也没什么联系,日常生活要用什么东西,只需写一张条子放在东厢里的一口酒缸子下,第二天这些东西就会出现在院子里的,我搬进去自己使就是了,然后东西用没有了再写字条再要。
这就有些象聚宝盆的意思了。
我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力求正常和规律,早晨天未亮就起床练拳,功夫是保命的法门不可轻忽,我想学内功和轻功可惜没有老师可以请教,下午看书练字,知识是力量,早就认识到了的,晚上天一黑就熄灯睡觉,保持良好的作息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规律得不能再规律,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一下子仿佛所有凡尘的事情红尘的喧嚣全都离得我很远很远很远了,我看不到也听不着它们了,再也用不着去回避去感受了。
这就是所谓的大隐隐于市吗?多么旷达多么高远。
但我只是个俗人,那心不是说能定下来就能定得下来的,这样的日子足过了有小半个月,世上的人们似乎已经将我遗忘,不管是仇还是爱。
心漾漾的有些不甘,未必非要有人记得我,自己都有些好笑。
这天是上弦月,月亮挂在树梢头,象一艘小小的明亮的帆船一样,静谐地停着空中。
任它的清辉洒遍了它脚下所有的大地,我站在院子里仰望明月,明月千里照流黄,这个样子的它也映照着我的二十一世纪的家吗?
一片静谐中有人叩响了我的院门,我透过门缝看到了王公子领着两个从人,拎着食盒提着灯笼站在门前。
主人现身了,他还真不过份讲究礼貌,距我住进来都十多天了,他这才来见我。
我开门接过食盒迎他们进门,“还习惯吗?”清朗的声音问,王公子的脸上带着如月亮清辉一样的笑,这有一个月来没见着他了,他好象又清减了些,这个人一天到晚的在愁些什么呢?
我以前认为他是富贵的闲人,但现下看来又不太象,是天生的多愁善感吗?也不太象,这一次,他能这样迅速地就知道了我的行踪还派会易容的人来接我,还安排下这样不好找的地方安置我,我就知道这个人也不会象我先前所想的那么简单。
他是谁?他真的是什么王公子吗?他对我到底有没有恶意?一连串的问号升腾起来,但我决定不动声色,反正他现在也没表现出恶意来,慢慢观察着看吧,反正我很享受他的笑。
“很好,我很习惯,谢谢王公子关心了,不过我还想问一下就在我来这里的那一天,京城里没出什么大的事吧?”我回答后提问。
没听到赵擎天平安的消息我的心始终是难安的,有那么多的挂牵,不是因为此时回想到他的好,后知后觉地爱上他了,而是毕竟他是为了我才卷入这一趟的混水的,太过忘恩负义我做不到。
不过我也不好明问,天知道赵擎天同志来这里有没有通过大槐国官面上接洽,我与他住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没看着有什么大槐国官面上的人来拜候,估摸着应该算是偷渡来的偷渡客吧。
“能有什么事呢?不过当日,城里流氓斗殴死了几十人,烧了几间房,别的可没听着有什么重要的人物没了。”王公子已经说得很明了,我的心放了下来。
与聪明人说话也很好,大家都是一点就透了,不用说得太白。
“今天月色不错,我们要不要在院子里喝两杯?”我问,听得赵擎天无事,我的心里自然是有些舒爽的,夏天这样的热,将宵夜摆在院子里吃喝兼赏月既凉爽又风雅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