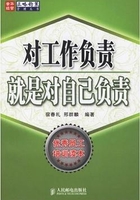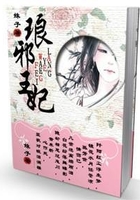“这叫借寿年吗?这能叫借吗?这叫抢,这叫偷,如果是借,请问二位你们准备怎么还我,还有我再请问一下阁下,你这样做有几份把握,杀了我,你的妻子就一定能得到健康得到寿年了吗?请问你是太上老君吗?请问你是仙人张三丰吗?”那个女子的眼睛里闪出了惶惑,慢慢汇成了泪水的小溪滴落,然后听得她对丈夫说:“元靖,还是算了吧,一切都听天由命吧,放她走吧。”她抓住他的手臂摇晃,“不,这么难得在预定的时间内找到跟你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生的人,况且她还这么健康,我算过她的寿年,足可活到九十二,怎么可能放她走呢?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的,原来我还不知道我为什么从小要学道,现在我才知道我应该学道要不然我们怎么继续在一起呢。”“可是,这个方子,没有人试过的,怎么就知道管用呢,别害了她,又救不了我。”她低下头嘤嘤的洒泪。“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把握我都不会放过的,你放心好了,师祖这个方法一定可行。”“但是她怎么办呢?”“有些人生来就是为了替别人死的,你不用放在心上,就象我们吃鸡、鸭、鱼、肉这些一样。”
什么,当我不是人吗?我的心气得快爆炸了,看样子他们已经决定了,我驯服或不驯服结局都不会变了,因此我破口大骂:“混蛋,混蛋,王八蛋,凭什么就得你们生我死,生死有命,凭什么你们就为了这万分之一的希望让人丧生,你们是不是人呀……唔唔”还有好多的话想骂却骂不出来了,那男人拿了一团布絮塞进了我的嘴,他显然的怕我的言语动摇了她妻子的信心,我尽力地瞪着两人,现在也只能用眼睛了,我的手指只能悄悄地用力地去撕扯那已经有些磨损的绳索,这才是我脱困的希望,最后的希望,他们是不可能放了我的,我的心下十分的明白,人没有不自私的,那个女人既想活下去又想与自己的丈夫呆在一起,她的内疚也只会是鳄鱼的眼泪了,看现在她在听了自己丈夫假惺惺的解释后也就缩在一角不开口也不望向我了。
男人在用心布置着,用不知什么粉末在大厅里画上了七个大小不一的太极八卦图形,然后小心地把那个女子抱来放在了一个点上,然后就是我了,我被放在与那女子相隔一臂之遥的另一个点上,我继续努力地拉扯着绳索,动作却不敢太大。
“时辰到了。”男人忙完休憩一阵后目注妻子说,“好,时辰到了就好。”她扯着一抺淡淡的笑意说,我看得出其实两人都在力持镇定,毕竟借寿这法子不一定可行,也许他两人也有危险,我对这些邪魔外道的东西门道都不懂,但我知道凡是逆天行事的人都会受到天谴,但祈求天谴来惩罚他们只是没有能力的人做的,我秦婧玉不是个只会坐等的人。
那男人开始喃喃地念着咒语,几个太极图形在我的眼里好象开始旋转了起来,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象一口口深井仿佛要将身周的一切都吸入井底,男人用一根尖锐的银针来刺我额头的鲜血,好痛,但就是这股痛的刺激让我一下子挣脱了手上最后的束缚,我猛力地挥拳,打上了他的左眼,地上的女人一惊,伸手过来拉扯我的头发,男人在最初的惊愕后也扑上来按住我,这时太极图案旋得更快了,我们三个人都被扯进了深井里,旋转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眼晕头晕耳鸣心里一阵阵的烦闷涌上来,想吐又吐不出来,难受难受,难受到极致人就晕过去了!
好象有几道哭声从远而近,一下子低一下子高呜呜地在耳边响着,还有人在一边低低地数说着什么一边抽泣,那哭声说话声一忽儿引来两三人的共鸣一忽儿又被人斥骂,这是什么地方呀,怎么这么吵。我使劲地想左右偏偏着脑袋想摆脱那烦死人的声波,却怎么着也动作不了,又一波的头痛,脖颈痛,胸口痛……全身上下无处不痛,那痛就象有一辆大卡车缓慢地从我身上碾过一分一寸地都不放过一般,又怎么着除了有人又我借寿现在又有人把我丢出去撞车了吗?
疑惑,急于想求证这疑惑,但头痛蜿蜒而下至全身各处,口干咽喉处更仿佛被人用钝刀子割了一刀似的,涩涩地干痛无可缓和,想翻身,却连动一下小手指都不行,想说话,让那恼人的哭声停一停,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难道自己是已经死了吗?死亡后的灵魂怎能感觉到如此的清晰痛楚,生平并没做过什么坏事,就是死后不能上天堂,估计也下不了十八层地狱呀。
现在我到底是身处何方,为何会有如此的疼痛,我赶紧的想弄个明白,我的寿年我的健康是否当真被人借走?
于是我卯足了全身的力气睁眼,那平日里只是上下耷拉的眼皮此时足有千斤重,全凭一股想一探究竟的信念支持,无边的黑暗终于才不甘心地退却,我看到了一点的光亮,当真是一点的光亮,即使我使劲睁大了眼睛,当此情形的我平躺在一张木床上,身上有被身下有褥但却感觉不到十分的温暖,这可是炎热的夏天呀,难道这一晕去就晕了好几个月了?也太不可能了吧。
有一种奇诡的气氛环绕在四周围,什么都不是太对,由于暂时也说不出话来询问,所以我虽然看到了周围围绕着七八个人,一时我也顾不上打量这些人了,我惊讶地看到四周能发出光亮的东西,那是一盏菜油灯,绝计不会错,空气中弥散着一股燃烧油脂的味道,由于有风吹的原因,它的小小的火焰还明灭不定,屋里一些家什的影子都在这光亮下投射得极长极长,又不住地变幻……